2021-02-06《花边文学》: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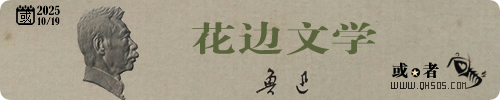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
——《做文章》
推倒旧东西,是为了建设新生活,在推倒和建设之间,是有一种叫做过渡的存在,过渡便是发展,而且是有机的发展,但是当推倒旧东西太过用力,则变成了“做”,太“做”的东西便成了“生涩”,成了“格格不吐”,既不能建设新生活,连旧有的味道也一概抹除了,甚至比起古人圆熟的东西也还要坏——这便有一个如何保留和如何加工的问题,而保留和加工则指向如何做文章的终极问题。
“朔尔”在《做文章》中引用了沈括《梦溪笔谈》里的一则文章,“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同一个事件被两个人同一时间看见,于是两人都做文章,一个是说马踏死了黄犬,一个则是犬死于奔马之下,两种作文,是叙述同一个事件,但是一个的重点在马,一个的重点在犬,不但主旨不一,而且都有些拙劣,还不如沈括在文章说得明白稳当:“有奔马,践死一犬。”两个人作为是要比较谁工谁拙,而这和当时的文体改革有关,““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他们是为了打破对偶成文的传统,而以“平文”或“古文”的方式作文,但是在拙涩的文章中,这“古文”倒也变成了太“做”的东西,变成了生涩甚至“格格不入”的文章。
“时文体新变”,就是要推倒旧东西,“朔尔”举例其实是为了指出当今的“生涩”风格,有一派是胡适为代表的,他认为古代是“言文不分”的,“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也就是在他看来,战国以前的文体和语体是合一的,这种“言文不分”在现在看来,白话文也就是“古文”,而鲁迅当时是否定这种看法的,“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而在胡适之外,林语堂也有一个观点,那就是“白话的文言”,他在《一张字条的写法》中说,以“语录体”为“白话的文言”,是“天然的写法”,能够“达意”,这便是他所谓的“做文章”的方法,也是现代“古文”的方向。一个认为古者言文不分,“白话文”就是问题新变的“古文”,一个推崇“白话的文言”,用这种天然的写法“达意”——而在“朔尔”看来,似乎都变得拙涩,似乎都是一种太着力的做法,而真正要推倒旧东西,完成从白话文到“大众语”的发展,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建设,他引用了高尔基的说法,“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从大众语变成文学,这不仅是一个推倒旧东西的过程,更在于解答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新与旧,毛坯与加工,生涩和圆熟,需要处理好的是这几个关系,但是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这似乎还是一个国民性问题。以笔名“倪朔尔”发表的《运命》讽刺的是中国人的“穷人哲学”,电影《姊妹花》汇总穷老太婆对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这便是宗汉所说的“穷人哲学”,这一种穷人哲学是对于运命的一种无奈,但是却变成了工具,“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也是电影,是外国电影,先是有洋侠客的勇敢,又有了野蛮人的陋劣,接着是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这还不够,有了几条腿之后又有了“一大从”,又有了“赤条条”,这就变成了“裸体运动大写真”,是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但是又把小童挡在了外面,因为他们不配看这些“美”——中国社会是“爸爸类”社会,在戏里只有“妈妈”献身“儿子”受谤,而到了紧要关头,便是“木兰从军”,推出“女人与小人”来搪塞,“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而“韦士繇”更是以“洋服的没落”来抨击中国的“恢复古制”思想:因为中国人的人体是最能顺其自然的,“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所以违反了自然的洋服,便要没落,“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人体顺其自然导致洋服没落,这其实就衍生出两种向度:对外和对内。向内的要恢复古制,要顺身体之自然,要适合砍头、下跪、打屁股,要有“穷人哲学”,要用“女人与小人”来搪塞,于是有了对“此生或彼生”省力的赞叹,“学习文言固较寻常语言稍难,……而应用上之省力,则阅者作者以及印工皆较经济,若用耳不用目,固无须文言。若须用目则文言尚矣。因文言为语体之缩写,语言注重音义,而文言音义之外,尚有形可察。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这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汪懋祖的说法,发对新文化运动鼓吹文言,是因为文言省力,但是“此生或彼生”是不是也可以解释为“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或者是“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文言字是少了,但意思模糊了,“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还有那些学者,比如梁启超、胡适,对于清代的学术眉飞色舞,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发达,不论是解经的打坐,还是小学、史论、考据,都达到了一个顶峰,而这种思想在“莫朕”看来,是完全可以算账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这些人的思想其实是固化的尊孔崇儒,到了新朝,不是革新,而是“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确,有些人的心是被征服了,“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民族的心被征服,而且彻底征服,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等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蚁民”黄维新还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呈请国民党广东政治研究会采用:禁止男女同车;禁止酒楼茶肆男女同食;禁止旅客男女同住;禁止军民人等男女同行;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乐场所……“白道”在《奇怪》一文中说:“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
甚而至于,防止男女同吸空气男女背着防毒面具更为妥当,既可以避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例子还有,比如东三省沦亡的时候处处在卖《推背图》,华北华南危急的时候上海出现了“碟仙”,所谓的科学在中国便证明了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当每一种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都像落入了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于是“公汗”在《偶感》中说:“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中国不可救药,是因为把外面传来的新东西“中国化”了,这种中国化不是吸收,不是融合,而是排斥,而是拒绝——向内而拒外,便也是洋服没落而让身体顺其自然的愚民社会表现之一。
但是如何向外呢?对梅兰芳的不同观点似乎也提供了这两种向度,张沛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中说,“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将梅兰芳从俗众中提出,又罩上了玻璃罩,坐起紫檀架子,还教他多数人听不懂的话,“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梅兰芳游日游美,就是拿着玻璃罩搬出去搬回来,从前没有士大夫帮忙做的戏,虽然俗,甚至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但是等待化为“天女”,虽然高贵了,但是“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这便是士大夫把他变成了皇家的供奉,成了不死不活的象征。但是梅兰芳却要访苏了,而且《大晚报》上刊载文章说,“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梅兰芳既是发扬国光,也是采用象征主义的必然,“常庚”在《谁在没落?》中的质问是: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是不是只是一种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而梅兰芳的京剧艺术也是象征主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于是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一种“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梅兰芳被士大夫放在玻璃罩里,是让中国艺术变得“死板板”了,而去苏联发扬国光,又是一种“艺术的消亡”,那么,向内和向外,何以不死板不消亡?其实从梅兰芳事件中引出了更多的问题,施蛰存在《现代》杂志上说,“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杜衡则说:“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一种是不平的大叫,一种是转变的提议,但是张沛却说,梅兰芳倒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也是“第三种人”;而且还以他“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来批评那些学会了“化名新法”的文人——“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比如《中国文艺年鉴》的“鸟瞰”中,既说苏汶“文艺自由论”行,也说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而实际上苏汶就是杜衡,不仅他人被抹杀了,而且还假冒文章吹捧自己,苏汶甚至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似乎就指向了用不同化名的鲁迅,因为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就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
不仅化名被抨击,连鲁迅写作的“花边文学”也难逃被攻击的命运。“花边文学”是“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青年战友廖沫沙的“立意”,一方面那些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周围饰以花边,二是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用不同的笔名,还托了人去投稿,并用花边装饰,鲁迅说,“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但是当化名为“公汗”的鲁迅发表了《倒提》便引来了林默的批评,“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而且林默还认为“花边体”的流传和拥护,对于建设“大众语”文学是不利的,“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林默认为“花边文学”将有不能流传下去的一天,是因为不被大众所接受,是违背大众需求的,而大众所需要的无非是“大众语”文学——所以林默否定“花边文学”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花边文学”实在是代西洋人“辩护说教”。
公汗的《倒提》一文,是指出了在租界因为西洋的慈善家“怕看虐待动物”,所以凡是倒提着鸡鸭经过就要法办,“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公汗当然是反对几位华人的做法,在他看来,“倒提”并非是虐待华人,因为,“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反而是有些仁人义士,“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甚至还比不上鸡鸭,“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于是林默在《论“花边文学”》中倒过来讽刺公汗,“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由此把“花边文学”也看成是为了“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的买办文学,和中国大众需要的“大众语文学”格格不入。
关于大众语、大众语文学,当时的确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怎样防止白话文变质,如何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这是白话文运动以后出现的新问题,这不仅仅是涉及文体改革的问题,而是关涉理念,而这种理念就变成了“时文体新变”向内还是向外的问题。鲁迅当然反对回到文言的老路上,但是在欧化过程中,如何把握好一个吸收和兼容的度。在刘半农病故的时候,“康伯度”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一文,他认为刘半农当时是《新青年》的同人,是文学革命的战士,但是在对于白话文欧化上,却是一个古人,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刘半农在《中国文法通论》中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太老式了,不好!”,所以要欧化,或者是,“‘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好!”或者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这都是欧化好的例子,但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当然刘半农是不赞成欧化了,因为欧化还可能将“子曰”变成“曰子”。但是康伯度认为“成了古人”的刘半农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一样,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便冷笑,康伯度的观点是:“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
正是这种欧化的必要性,马上引来的反驳,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中说,欧式文化的风行是因为“必要”,那么中国话是不是要取消了?“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康伯度为此答文公直说,中国语法里加一点欧化,不是取消中国话,当然也不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指使,“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因为中国人要前进不能照老例,他说,文公直文中的“对于”、“欧化”、“取消”等词都不是中国话,都是欧化的词,“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除了回应文公直之外,康伯度也针对另一支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林语堂进行了回应,林语堂讨伐的不是白话难懂,而是白话“鲁里鲁苏”,他认为返璞归真就需要“语录式”达意的“白话的文言”,康伯度嘲讽了一番林语堂的“幽默”论,“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在“中国没有幽默”中,白话的文言就如那被打的屁股一样,“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
如何欧化,“仲度”在《汉字和拉丁化》中更是提出了“书法拉丁化”是“大众语”革新的最后一条路,比起提倡白话文,提倡大众语对于读书人其实更有难度,因为必须接受另一种文体,甚至于书写和读音的变化,“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从字母、拼法到横行、作文,“书法拉丁化”甚至是一次让文人“牺牲”的做法,但是这牺牲却是必然的,“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为汉字牺牲我们,是一种守旧,甚至于还是拜蛇迎神的“物”崇拜,而为我们牺牲汉字,则是对于工具的革新,对于文体的创造,对于带病遗产的疗救——“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620]
顾后:傍晚的一百万亿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