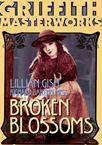2024-02-06《残花泪》:最后的微笑留给世界

英文片名:Broken Blossoms or The Yellow Man and the Girl,《残花泪》只是“or”之前的部分,它表达着一种美丽被毁灭的悲剧性,指向的是个体命运;而“or”的后半部分则是另一种指称,“黄种人”是电影中的男主角陈桓,“女孩”则是被称为“默片时代伟大而脆弱的尖叫者之一”的丽莲·吉许扮演的露西,但是大卫·格里菲斯在这里都没有强调个体性,只有画面拍摄到陈桓在伦敦的店名时才有英文的“陈桓”,而露西也叫过他的名字“陈基”,默片的所有字幕中提及的都是“黄种人”,“黄种人”作为“中国人”而出现,和“女孩”一样,它们都是类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卫·格里菲斯讲述的并不是单纯个体的故事,而是从人类、人性的普遍性角度来表达“残花泪”的悲剧性意义。
这从电影最开始的一段字幕中可以解读出来:“这是一个寺院钟声的故事,这是一个爱情与恋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泪水湿襟的故事……”这是这个故事具有的三个维度,爱情、恋人以及泪水湿襟指向的是陈桓和露西之间的跨过之恋,更是对弱者命运的一种关切,而这种对弱者命运的关切也超出了个体,成为对“黄种人”和“女孩”类的叙事,这种“残花泪”的叙事需要的则是“寺院钟声”的升华,为什么寺院钟声是对“残花泪”的一种救赎?在电影中,寺院钟声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陈桓在中国的时候去参拜僧人,僧人对他谆谆善诱,然后敲击了寺院的钟,“钟声在夕阳西斜的佛像前鸣响”,正是在这个场景中,陈桓心中有了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远渡重洋进行佛教教理的传授,在他看来,他有职责和使命将和平信息带给“蒙昧、无秩序和好战的孩子们——央格鲁·撒克逊人。”这就很明显,陈桓作为佛教教理的传道者,是要将仁慈、和平带给蒙昧、无秩序和好战的英国人,这就是所谓的跨国拯救,它体现的就是人类的救赎。
在这里,陈桓所代表的“黄种人”绝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存在,蒙昧、无秩序和好战也并非是央格鲁·撒克逊人的一种劣根性,大卫·格里菲斯在这里也只是一种类的表达,陈桓去往英国之后,在伦敦开了一家店,但是他并没有实施他的拯救计划,反而在鸦片的腐蚀中迷失了自己,所以拯救者也可能是迷途者,而他在店门口也遇到了一个英国人,他说自己将要去中国传教,他递给陈桓一本成小册子,小册子上写着“地狱”。陈桓带着佛教的仁慈之心来英国,英国人带着基督教的救赎思想去中国,宗教在交流,并不是为了突出地域、种族的差异,所以在这里,大卫·格里菲斯被人诟病的种族主义也并不存在,虽然在电影中陈桓总是眯着眼睛,总是佝偻着身子,这是对“黄种人”的刻板印象,还有那个对露西的美色垂涎的中国人,他在电影中被称为“邪恶之眼”,但是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只是为了突出他们的性格,并非是人种意义上的歧视——这和大卫·格里菲斯称央格鲁·撒克逊民族是蒙昧、好战和无秩序的民族一样,和陈桓在街上遇到自由打斗的外国水兵一样,不具有人种和民族的特指性。
| 导演: 大卫·格里菲斯 |
这也就回到了大卫·格里菲斯电影中的主题,“我们或许相信没有巴特林·布鲁斯这种用残忍地鞭子抽打无助者的人,但是我们没有使用过刻薄言行的鞭子吗?这么说,巴特林有可能甚或传递着一种警示信息。”鞭子在露西的“父亲”巴特林的手上,巴特林狠狠抽在露西身上,这就是露西命运的写照,也是走向“残花泪”悲剧的原因,就是在巴特林的鞭子之下,露西最后惨死。但是格里菲斯给了“巴特林的鞭子”一种隐喻,它和蒙昧、无秩序和好战一样,是人类的恶劣品性,它代表着一种滥用的权力,最后它夺走了生命,在这里的警示意义就是对人类之恶的表达和批判,那么,在以拳击为生、手拿鞭子的巴特林代表权力和暴力的同时,露西代表的则是无助者,这个被人用布包着塞给巴特林,被这个“父亲”养大也遭受欺凌的女子就是弱者,所以当陈桓收留她并最后在“一分钟营救”中用枪杀死了巴特林,就是一种对弱者的拯救,不仅露西是弱者,远渡重洋迷失了自己的陈桓也是弱者,用枪对抗鞭子和斧子,以暴制暴虽然和陈桓当初的仁义式拯救不同,但也是对邪恶的一种对抗,也是对罪恶的一次消除,当然也是回到了“寺院钟声”这一意象之中。
第一次的寺院钟声是陈桓内心伟大梦想的表达,他像一个救世主一样踏上了他国之路,开始了对迷失的人类的救赎;第二次出现寺院钟声则是在陈桓来到伦敦迷上了鸦片,一蹶不振的他回想起了那寺院的钟声,这钟声便成了对他迷失的警钟。也在这个时候,露西出现他店门口,陈桓被这个美丽的女子所吸引,从这个意义上讲,露西的美丽和纯正就是“寺院钟声”,它反而变成了对陈桓的拯救。露西是弱者,陈桓也是弱者,他们的拯救是弱者对弱者的相互取暖,在罪恶的权力和暴力之下,两个人再次相遇,露西因为不堪忍受“爸爸”巴特林的殴打,离家出走,最后倒在了陈桓的店门口,陈桓将她扶到了楼上的创伤,给她擦去了伤痕,照顾她,给她穿上中国的旗袍,还吹奏笛子给她听好听的歌曲,送给她一个娃娃,在这里便是陈桓的拯救,“她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彬彬有礼”,而他梦想着露西小鸟依人的样子、纯真的本性都属于他,所以他叫她“白色花朵”,“他的爱里有一种神圣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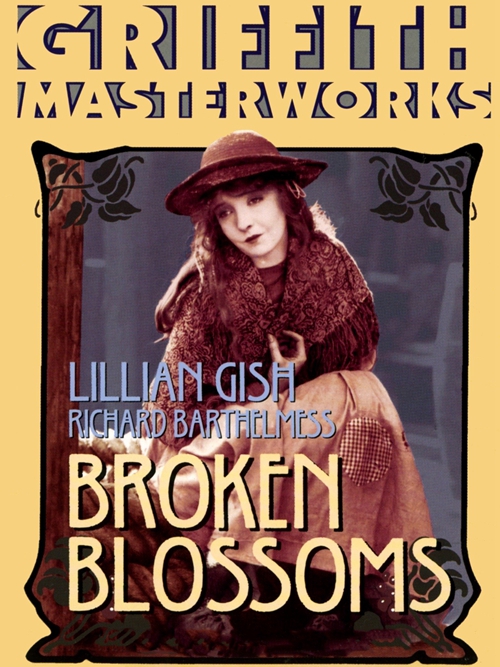
《残花泪》电影海报
他们相互依靠,他们相互拯救,“黄种人”和“女孩”在这里便呈现为人类最美好、最神圣的存在,它是爱情,它是仁慈,它是和平,它是美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甚至比宗教的拯救更具普遍性,这就是格里菲斯在电影中所强调的美。但是邪恶势力还是存在,当巴特林知道露西藏在陈桓的店里,他无法容忍这个“中国佬”,并骂他是“肮脏的中国佬”,在陈桓出去换零钱的时候,巴特林砸掉了陈桓房间里的东西,带走了露西,回到家之后,巴特林用斧头砸开了露西躲藏的房间的门,并用鞭子残忍地打死了露西,露西在死之前做出的最后动作就是把手放在嘴角,然后让嘴角扬起,这就是“微笑”的表情,所以,“微笑”成为露西所渴望的表情,“微笑”是她对世界最后的期待,“微笑”也是人生之美的最后表达。
陈桓拿着枪赶来,最后一分钟营救没有留住露西的生命,但是在巴特林拿起斧子的那一刻,陈桓的枪响了,作恶多端的巴特林终于倒下。杀死邪恶,是陈桓对世界最后的拯救,而当他把露西的尸体抱回家,放在那张给了露西温暖的床上,然后披上美丽的中国旗袍,此时的陈桓向佛像进行了祭拜,自己敲响了“寺院钟声”,这也是对于仁慈之心的最后一次表达,“他对白色花朵微笑着说别离时,一生所有的泪水涌过他的心田……”露西用最后的微笑向世界告别,陈桓也以最后的微笑保留了世界的美好,而当“残花泪”成为两个人的悲剧,最后再次出现了夕阳西下时的寺院钟声,它成为了格里菲斯对整个人类命运拯救的最后表达。
从中国到伦敦,从“黄种人”到“女孩”,格里菲斯的跨国之恋不局限于个体的爱和悲剧,而是上升到人类普遍性问题,这里有拳击代表的暴力,有鞭子代表的权力,有自由打斗代表的游戏心态,有“邪恶之眼”代表的欲望,更有1919年拍摄这部电影指向的战争,在巴特林北枪杀之后,更有伦敦警察说的“这一周好过上周,只有4万人死亡”的麻木,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之恶,而在这种恶面前,是仁慈,是和平,是美丽,是爱,是最后的微笑,它们构成了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存在,而且,美好没有最后战胜邪恶,露西死了,陈桓最后也自杀了,但是在“残花泪”中,他们留下了最后一抹微笑,这微笑也成为格里菲斯对世界的警示,它和寺院钟声一起构成了新的希望。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