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16《最后的把戏》:在场之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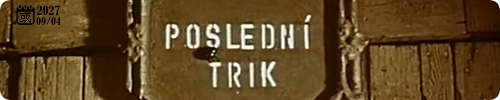
11分钟的短片,1964年的电影,当打开,当观影,距离屏幕几十厘米,作为一个2022年的观众,是无论如何无法以一种“进入”的方式成为杨·史云梅耶第一部影片的“在场者”,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隔离呈现出一种非在场的纯粹观影体验,但是当影片中“最后的把戏”里有舞台,有观众,有观众的掌声,他们是不是就具有了在场性?
“最后的把戏”,史云梅耶无疑将焦点对准在舞台上的两位魔术师,施瓦斯韦德和埃格就是最后把戏的表演者,当他们被赋予表演者的身份,舞台上的一切都可以看做是“最后的把戏”的组成部分。最后的把戏里有精彩的魔术:埃格首先从凳子上站起来,然后拿下帽子取出一条表面如岩画的鱼,然后打开脑袋,将整条鱼都放了进去,接着上紧发条,脑袋里的齿轮开始转动,最后再打开脑袋的盖子,于是整条鱼只剩下了鱼骨;这是埃格的“第一个把戏”,接着施瓦斯韦德站起来,开始表演属于他的第一个把戏:他用钥匙打开脑袋,拿出里面的小提琴,在演奏的同时,一匹马在绳子上舞蹈,不断的组合产生不断的运动;接着埃格开始了第二个把戏的表演,他打开了身体,里面是两把小提琴,埃格用四只手演奏,演奏的曲目是“我的灵魂之歌”:“你既迷人又美丽,不要让我承受怒火……”在小提琴演奏之后,埃格更是一个人演奏了大锣、小号,一个人俨然是一支乐队;轮到施瓦斯韦德表演第二个把戏,他变出三个头,然后如积木一半堆砌在上面,随着动作起舞,三个头也舞蹈起来;之后是埃格的第三个把戏,他从耳朵里掏出了指挥棒,在指挥棒的作用下,椅子开始翩翩起舞,不仅自己的椅子,施瓦斯韦德的椅子也在起舞……
埃格表演了三个把戏,施瓦斯韦德则表演了两个把戏,三个和两个呈现出的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暗示着两个人矛盾的不可调和:从魔术节目来说,两个人各有精彩之处,但是很明显,埃格更多是在和施瓦斯韦德较劲,因为施瓦斯韦德表演的第一个把戏就是音乐的演奏,埃格之后的两个把戏也都是和音乐有关,更大的场面,更丰富的内容,更精彩的表演,就是一种无声的压制。而在节目本身之外,两个人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处处体现了矛盾:一开始两个人端正地坐着,在谁先开始表演的选择中,他们都采取了谦让的方式,伸出手邀请对方,便是一种共同表演的礼节。但是这种谦让的礼节,本质则是一种暗斗:在施瓦斯韦德表演第一个把戏的时候,埃格就是用棉花将自己的耳朵堵上了,小提琴演奏带来的美妙声音始终被他拒绝;在埃格表演完毕的时候,施瓦斯韦德也在鼓掌,但是那完全变成了一种形式。
| 导演: 杨·史云梅耶 |
表面是尊重,是谦让,是礼貌,实质上却是暗斗,是矛盾,所以这是一个展现他们虚伪本质的舞台,而在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时候,他们更是采取了毁灭性的暴力行为:各自表演完把戏,对方伸出手“友好地握手”,却是极其用力制造对方的痛苦,而当埃格表演完第三个把戏,施瓦斯韦德上前和他握手时,竟然用了大力气,硬是将埃格的一只手臂扯了下来;于是矛盾升级,于是冲突白热化,他们不停地扯下对方的肢体,从手到脚,一件件跌落,最后两个人只剩下一条胳膊——这是一次解体过程,当他们的头、身体和四肢不断被肢解,也意味着魔术走向了解体。从两个人的虚伪,到不断升级的冲突,最后的把戏变成了暴力的游戏——无处不在的小甲虫,似乎就是这种恶的象征,它存在与魔术师打开的世界里,在魔术表演时爬行着,最后在魔术师两败俱伤中死去,从出现到死亡,小甲虫伴随着这场暴力的表演,它是见证者,也是恶的符号。
如果仅仅把魔术师从和谐走向矛盾,解读为人性的一种恶,似乎显得单一,即使将1964年的动画电影映射为对当时冷战的讽刺,也显得表象化。实际上,史云梅耶命名为“最后的把戏”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把戏发生在舞台上,把戏就是魔术本身,无论是埃格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把戏,还是施瓦斯韦德的第一、第二个把戏,无论是他们在虚伪中的谦让、握手和鼓掌,还是他们发生矛盾乃至最后升级为暴力式的肢解,都可以视为把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最后的把戏”所包含的是舞台上的一切,是魔术,也是暴力,它们是舞台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最后,当两个人只剩下一条胳膊的时候,从矛盾和暴力又走向了和解:他们的手从斗争状态恢复到友好状态,于是再次握手,于是表演走向结束。

《最后的把戏》电影海报
这是一层含义的“最后的把戏”,当然在这个把戏里,史云梅耶的命名本身就包含着讽刺成分,因为魔术变成了“把戏”,里面就是一种阴谋论的运用。但是这并不是史云梅耶讽刺的全部,在舞台之上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舞台之外的世界,而这正是史云梅耶真正想要揭露的把戏。在两位魔术师分别表演魔术的时候,传来的是观众的掌声;当魔术师从矛盾升级为暴力的时候,掌声依然;当身体被肢解,掌声还是在最后响起——这是观众在场的充分体现,正因为观众的在场,魔术师要为他们表演精彩的魔术,因为观众的在场,魔术师的矛盾和暴力也被看成是表演,因为观众的在场,魔术师不惜以牺牲自己的方式赢得掌声。而对于观众来说,正是他们用掌声来表达对节目的喜欢,才使得矛盾升级,才使得暴力发生,才使得死亡出现,观众的在场就是让暴力具有了合理性,就是让暴力也变成了表演变成了把戏。
所以这实际上是史云梅耶在批判观众之恶、在场之恶、旁观之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后的把戏”不仅仅是舞台上的演出,更是将舞台之上和舞台之下结合在一起,成为人类之恶的表演。而在开场的时候,字幕打出来的是“这是我的鞋子”“这是一个模型”“这是一堵墙”,对应的是魔术师的鞋子,是魔术师的面具,是魔术师陈列道具的墙,这更是暗示了表演舞台的普遍化,在这个无处不在的舞台上,魔术师表演了最后的把戏,观众也在参与。这种参与性还有另一个很隐蔽的线索:展示鞋子之后,要套上模型的时候,出现的是一个真人的脸,这部11分钟的短片是一部动画片,是木偶戏,但是真人的脸一闪而过分明是在暗示:这不是舞台上的表演,这是现实中的把戏,当舞台延伸到现实,当把戏成为一种现实,它就是真实的恶。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