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17《林中之死》:我们也能孕育出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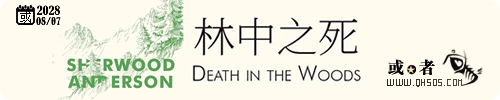
我脑中蹦出了“煞白”这个词,因为我小时候曾在一本侦探故事中看到过这个词,而最近我一直在与侦探打交道。
——《她在那儿——她在洗澡》
煞白,一个词语,一种状态,以及一个虚构,它是猝不及防之后的表现,它是真相暴露之后的表情,用在妻子身上,是因为她面对的是一个得到了秘密的我,是一个知道了不忠故事的我,甚至是一个撞见了和妻子在一起的男人的我——当然,最主要的,是面对一个雇佣了侦探把整件事情弄得水落石出的我。
之前不知道“煞白”这个词的意思,现在突然从脑子里蹦出这个词,并将其用在妻子身上,是找到了这个词最恰当的位置,这一切就源于将侦探小说的情节变成了现实,“最近我一直在与侦探打交道”:我不仅去见了一名侦探,我又雇了一名侦探,我还假装自己是妻子的情人,然后回家向妻子摊牌,告诉她我的疑虑,观察她的脸色,看看她的脸色是否会变成煞白。一切都进入到我设计的情节之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不是一个侦探故事,而是一部活生生取材于现实的“侦探小说”——侦探故事和侦探小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小说是人为设计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小说充满了虚构,故事则在讲述后对他人具有启迪意义。
首先一定是一个现实的故事。十年前我的生意黄了,我的资产归于妻子名下,文件让妻子签字之后事情就算处理好了。但是十七天前,我发现了一张便条,便条是写给妻子的,署名是比尔,“这周三等那只老山羊离开之后,你到公园来。在我之前遇见你的动物笼边上的长凳那里等我。”便条里当然是一个秘密,晚上在办公室里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之后,我回家,走到家门时大声问妻子在干什么,妻子回答说:“我在洗澡。”问答都没有什么疑问,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是在我看来一切都在发生,“她一直假装爱我”,这是我下的判断,“妻子对丈夫不忠。她开心地出了门,说不定还挽着一个潇洒的小伙子的手臂。那人是谁?他会跳舞。他会抽烟。他和那些同类人在一起时会大笑起来。”或者不一定是比尔,可能是和妻子一起坐在公寓里假装兜售地毯清扫器的人,可能是门廊前辈我撞见掏了掏口袋的人。
总之,妻子假装爱我,妻子对我不忠。这是现实的故事?当十年前将资产归于妻子名下开始,似乎隐隐地就开始了对妻子的怀疑,而十七天前的便条无疑加上了砝码,但是这个故事在妻子是否出现“煞白”之前就已经慢慢变成了小说,我雇了侦探,我假装妻子的情人,我完全在侦探小说中使用“煞白”,就是一种虚构的开始,而妻子也成为了我小说的人物。从现实的故事到虚构的小说,这其中的转变就在于把作为词语的“煞白”、作为想象的“煞白”变成了具体可见的表情,但是小说之存在,已经越过了现实的故事,在自己的轨道上成为了独立却虚无的文本——安德森·舍伍德的小说《消失的小说》似乎就是对于“小说”的某种反讽。
“我指的是,他在脑中写这部小说。将要写成的这本书自动写成,随后又毁掉了。”出生在英国某个农村的贫苦家庭,他一开始就想要写东西,写东西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改变故事里的现实:他把他的女人变成了某种异教徒,他在她闯入了正在写小说的房间里打了她,他当然也去看过她还给她寄了钱……实际上,她的女人就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因为小说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支配。他把女人当成了小说中人物,他自己在完成一部小说,这是小说的双重建构,在苦苦琢磨最后动笔完成之后,一部优秀的小说终于完成了,他把小说放在了桌子上,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但是,他知道小说其实从未真正写出,“当然,桌子上只有空空如也的一叠白纸。”写出了小说,又毁掉了小说?毋宁说,小说一直是头脑中的虚构,一直无法成为现实的注解,或者说,小说就是现实的注解,优秀的小说完成了,而其实是一部被毁掉的小说。
小说是虚构的小说,是设计的小说,是支配他人的小说,当然,小说是消失的小说。《消失的小说》是舍伍德对作家状态的一种讽刺,那么讽刺之后必将从小说回到故事,那么在这个《她在那儿——她在洗澡》的故事里,从“煞白”开始的小说如何重新变成和现实相关的故事?那就是从支配他人的命运被被支配的生活中挣脱出来,让故事成为现实的真相并启迪现实,“不过,哼,既然我要把这个故事说给你们听,那就开始吧。”讲故事的是我,我要将这个故事讲出来是为了让“你们”听见,我和你们之间构筑了讲故事的主体和客体,那么,从故事中获得启迪的“你们”又是谁?“我来告诉你们吧,你们这些牵着狗散步的人,或许你们没有理由去怀疑你们的妻子,但你们的境遇和我一样。”那么很明显,“你们”就是和我一样境遇的人:你们也喜欢支配别人,也喜欢雇佣侦探,也喜欢使用“煞白”这个词语。
我就是你们,你们就是我,故事主客体合一便是舍伍德·安德森构建的故事叙事,它以最大可能将小说变成消失的存在,从而回到不受支配的故事应有的层面。《林中之死》可以看做关于“故事”最本质的叙事,“这么些年过去后,我此刻突然想起了她和那些事儿。那是一段往事。”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不知不觉间,林中那个场景就构成了我现在试图讲述的这则真实故事的基础。你们懂了吧,故事的碎片是很久之后一点点拼凑起来的。”我之所以讲故事,之所以把碎片拼凑起来,因为故事中有启示他人的意义;“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们明白,为何我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是在讲故事,我还是一个参与故事的人,所以关于老妇人的故事,也变成了我亲历的故事。
老妇人的故事呈现的是一种碎片的人生,她起先在一个德国人的农庄里,被农场主强奸,之后又被杰克抢了过去,生了一个儿子和女儿,后来女儿死了,丈夫和儿子名声不好,他们是无赖,偷马、喝酒、赌博,“马,奶牛,猪,狗,人。”这就是老妇人之后的人生。后来她去了树林里,一群狗围着她,然后一条狗开始撕咬老妇人背上的袋子,“如果这群狗真的曾经是狼,那么这条狗就是狼群中的狼王。”当然在寒冷的林子里,老妇人死了。这便是关于老妇人的故事,而我曾经见过这个踽踽独行的老妇人,在“林中之死”发生之后也见到了死去的她,“在此之前,我俩谁都没有看到过女人的身体。或许是覆在冻僵肉体上的雪,才让它看上去如此白皙、动人,如此像大理石。”林中之死的问题是:老妇人是不是被谋杀的?我拼凑出这个故事,我还原这个故事,我参与这个故事,对于是否是谋杀最重要的一点不是案件本身,而是谋杀所指向的就是如小说一样被支配的命运——既是老妇人是自杀,她也是在被命运推向了生命的深渊。
| 编号:C54·2220919·1874 |
故事不是小说,人生不应该是一种被支配的文本,《林中之死》就是回归故事、挣脱被支配命运的一种努力,我讲述故事就是为了“让你们明白”:“我当时以及自那以后为何会感到不满……”仿佛是要拨开那神秘而幽暗的林中世界,让踽踽独行又顾影自怜的老妇人能给人一个关于生命的启迪:活着是为了什么?舍伍德·安德森小说集中的几部小说都可以看做是《林中之死》的延续:从幽暗的树林中走出,从孤立的命运中走出,从被支配的小说中走出。《山里人》也是一个故事,也是我亲历的一个故事,“我曾在弗吉尼亚西南的山里住过一段时间,北方人在我到北方时曾向我问起很多有关山里人的事儿。”山里人构筑了一种在“林中”的境遇:“山里的男男女女都是那个样。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都是穷苦的白人。这么说当然意味着他们既是白人,也是穷人。他们也是山里人。”在那个叫“山谷”的村子里,我因为钓鲑鱼而迷路,后来见到了一个老人,老人说起自己的妻子死了,他独自一人住在这里——但是,我分明听到了楼上女人的声音。老人说,那女人不是自己的女人,她的老爹死了,所以她收留了她,“你知道吧,她是个巫婆。你无法满足她。她必须给自己找个男人。”
这多么像《林中之死》中老妇人的命运,甚至我认为是老头将她关在那里,她急需要从这里逃走,在临走时我偷偷塞给她钱,但是女人拒绝了,甚至变成了愤怒,“你给我滚,滚了就别再回来。”我还是把钱放在了那里,从此之后我也再没有去过那个山谷。《山里人》是我亲历而讲述的故事,很明显,老头和女人都变成了我讲述故事中的人物,他是不是真收留了女人,她是不是真的是个巫婆,其实我并不知道真相,我放下的钱,我想制造她逃跑的机会,反而变成了一种小说的设置:他们都在我的故事中变成了被支配的人物,但是,“尽管鳟鱼肥美,但我再也没去那个山谷钓过。”至少是我开始远离小说设置的一种努力。而在《感伤之旅》中,故事开始向着它固有的方式发展:乔一直想到外面去看看,甚至试图从山里逃出去,后来他去了矿上,认识了意大利人,但是当外面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他反而不适应了,这便是被自己的想象支配的生活,所以乔最后回到了山里,三天三夜的跋涉,从迷路到找到路,一趟“感伤之旅”结束,乔又回到了山里,“他之所以会毅然决然地从矿村回到自己的山区,那是因为他担心他的妻子身处山里的小屋里,柴火会不够用,但他这么说时却笑了起来。”
山里有妻子,有小屋,有柴火,当然也有生活——乔和《山里人》种的我所设想中的女人形成了一种相悖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乔是真正活在启迪人的故事里的人物。同样在《一次南方的聚会》上,那个跛子说的那句“我应该带他去见见萨莉姨妈”,其实就揭开了土生土长中西部人的萨利姨妈的真实生活,“在她精神状况好,她想要见人的时候,她比谁都要热情。”她经营着一个庭院,那面坍塌的墙已经修缮一新,旁边还种上了植物,关键是萨利姨妈这个人,六十五岁的她会聊起过去的时光,聊起密西西比河的生活,聊起新奥尔良受法国人的影响,她是一个热情的人,一个慈母般的人,一个称得上是贵族的人,“也许我确实有点儿了解他们。我自己就是中西部人,看来我们也能孕育出我们的贵族。”
《山里人》里的老头和女人,《感伤之旅》中回归的乔,《一次南方的聚会》里中西部贵族的萨利姨妈,他们都是“林中”的一种存在,但是他们并没有像那个死去的老妇人一样,活在被支配的命运中,他们拥有的是自尊,是对爱的呵护,是对生活的热情,这一切构成了“林中之死”的反面,而由这些故事延伸开来,还有《回乡》故事中的浓浓回忆:在剧院里看到了曼斯菲尔德扮演的布鲁特斯、和舅妈一起乘坐夜船沿河而上到了奥尔巴尼、船上两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还有萨姆森河拐弯处的丽舍之角,和父亲的远足垂钓经历,当然对于约翰来说,最重要的则是那个叫莉莉安的女人,即使她的故事里是结婚、离婚、再结婚的曲折,但是当十八年后再回来,约翰的故事依然充满了快乐,“我要把她约出来,天啊!这会很有趣!我要把她约出来。”而在《宛若女王》里,故事变成了对于美的一次探讨:当崩溃的男人去欧扎克山脉散心时看见了从脏兮兮的孩子和邋遢的女人中走出来的年轻姑娘,他发现了“非凡之美”;另一个男人在孩子时曾遇到过贩马人,贩马人中的女人朝他看了一眼,她成了“他这一生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还有我眼中的爱丽丝,一个失声的歌手,一个有着豪宅的女人,一个拥有情人的女人,当她垂垂老矣讲起那些故事,“她走在我前面,穿过空地,那一刻我发现了美。”那是一种沧桑之美,和非凡之美、回眸之美一起构成了关于美的叙事,“爱丽丝只是在试图抹去一段无果的爱情的记忆。”抹去就是对支配生活的否定,就是对小说虚构的拒绝,当然,就是回到故事本身。
从《林中之死》开篇,舍伍德·安德森就是将死亡赤裸裸呈现出来,而最后归于《兄弟之死》的死亡,则完全超越了命运。十四岁的玛丽和十一岁的泰德是姐弟,他们地主格雷的孩子,在外面玩耍,他们从来不在乎什么禁忌——泰德因为患过白喉病,他的心脏不能经历剧烈运动,“医生说他随时可能会死去,会突然跌倒就再也醒不过来。”但是在雨天玛丽带着她疯狂奔跑,“玛丽觉得她和泰德似乎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家庭。农场、农舍和谷仓里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富饶。他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由。”这种自由起先也在格雷另一个孩子唐的身上,十八岁的唐拒绝父亲砍掉那两棵树,“如果你打算这样做,父亲……我要离开这个农场,再也不回来了。”唐威胁父亲,当然,父亲还是叫人砍了树,唐也离开了这里。似乎这也是和玛丽、泰德一样在追寻一种属于自己的自由:“所有权赋予人们奇怪的权力和支配地位——父亲对孩子的支配,男人和女人对土地、房屋、城里的工厂和田地的支配。”只有舍弃所谓的支配权才能得到自由。但是唐还是回来了,父亲和他见面之后将指挥权交给了他,而他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也接受了,“你体内的某些东西必须先死去,你才能拥有和控制它。”
唐的过去死了,唐的现在是拥有和支配,其实离开根本没有改变什么,但是泰德死了,死在自己的床上,而在他死之前,和玛丽一起,“他们继续做着禁止做的事,但没有人提出抗议。”《兄弟之死》是泰德之死,但是死亡的背后却是自由,“他从来没有像他哥哥那样妥协——以确保获得财产、成功,以及他发号施令的时刻——也永远不会面临将落在他哥哥身上的那种更微妙、更可怕的死亡。”唐只不过是小说的一部分,泰德和玛丽活在自己的故事里,于是他们得到了自由,他们不被支配,他们没有“煞白”的经历,当然,“我们也能孕育出贵族”。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39]
顾后:“莫”愁前路无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