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17《保罗·利科六访马赛尔》:向他者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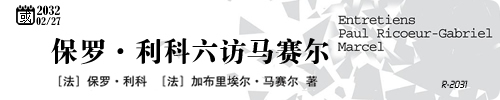
吉妮:没错,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在你现在所过的生活当中,是否能够显现出来呢?
克里斯蒂安:(不情愿地)不,那不是我的灵魂,那只不过是描摹灵魂形象的一格讽刺漫画罢了。虚伪的仁慈只能启发谎言。或许是虚伪的爱吧……(沉默)现在好像突然有一道光线照到了我身上,我一时之间看不清楚。
——《破碎的世界·第四幕》
上编是《保罗·利科六访马赛尔》,下编是《破碎的世界》剧本,当下编不再是上编的“附录”,上和下构成的是一种平等的结构,这种平等的结构所反映的就是解读马赛尔思想所具有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哲学,另一个则是戏剧。《破碎的世界》曾出现在马赛尔1933年发表的《存有奥秘之立场与具体进路》中,也在《保罗·利科六访马赛尔》的对话中,哲学和戏剧的内在关系通过这一文本得以展现——而在保罗·利科第三次访问时,马塞尔就具体阐述了他的哲学和戏剧之间的双进路关系。
保罗·利科直接提出的问题是:“今天您如何看您的戏剧呢?您如何了解您的戏剧和您的哲学之间的关系呢?”马赛尔首先做了概括性的回答:“我的戏剧与我的哲学,二者之间有最密切的关联。”对于这种密切的关联,马赛尔用了一个比喻,他把自己的作品整体看成是希腊,与欧洲大陆连接的那部分就是他的哲学作品,而岛屿就是他的戏剧,如果要去岛屿则必须渡海,所以要接近剧作就必须离开海岸,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更具内在性:“早在我知道或揣测一种哲学之前,我就已在戏剧内运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哲学戏剧化的一个表现,在马赛尔看来,哲学是不是具有存在性格,就必须通过戏剧性来检验,或者说,戏剧之存在,就是通过戏剧性来诠释哲学的存在性格。
存在和戏剧性之间的同一性,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形式意义上,马赛尔认为存在的主体要有效地被我们思考就必须给他说话的机会,也就是说主体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主体通过说话被确知,而戏剧就是制造说话的机会,就是关于对话的文本;另一方面,这种所谓的说话和对话所凸显的主体性,又并非是封闭的主体,他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互为主体性”,也就是主体间性,“由于我们不是绝缘体,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对自己所做而产生的所有的对别人的影响,都须负责。”在马赛尔看来,每个人都是自己观点的囚犯,只有把主体的我提升到一个“可以包含众人的层面”,才能让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位置,才能使得每个人为自己辩解,这就是互为主体性:既是主体之我的存在标志,也是为他人负责的态度。而拥有了互为主体性性,那么“问题”就会变成一种“奥秘”,分析的反省之外就会有意识得到提升的“第二反省”,“奥秘”的价值和“第二反省”都通过戏剧的角色加以落实,从而完成了从自我封闭走向自律和对向他者开放的目的。
这就是马赛尔关于存有奥秘与具体进路的阐释,而在剧本《破碎的世界》里,这种互为主体性通过戏剧化的情节构建出来。这出四幕戏剧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女主角克里斯蒂安·谢奈是一位多才多艺、美丽聪颖而极富魅力的少妇,她身边围绕着许多男女,他们都渴望引起她的注意并争取她的爱情:年轻的吉尔勃特仰慕克里斯蒂安,他和她合作以书信的方式共同创作一部角色对调的小说;克里斯蒂安的好友亨利则与她合作编排一出芭蕾舞剧,他也希望争取克里斯蒂安的感情。所以克里斯蒂安虽然已经嫁给了罗伦,但是她每天都在社交圈里,除了所谓创作的合作之外,喝酒、跳舞、旅行等社交活动占据了她的大部分经历。但是这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克里斯蒂安却陷在自我的封闭世界里,她对丹妮说:“我根本就不爱任何人。”继而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她将这个破碎的世界比喻为一只停摆不走的表,外面看起来完好如初,但是里面的零件都不再走动,“要知道,世界,或者这个我们叫作世界的东西,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以前曾经有过一颗心。可是现在那颗心似乎已经停止搏动了……”
之所以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就在于人与人之间“只是偶然碰在一起”,生活没有重心,也没有生命,这就是马赛尔所说的自我成为囚犯的世界,克里斯蒂娜成为“戴着一张大众情人的面具”在过日子的人,看起来丰富多彩的生活就是一出戏。但是寄送来的一封信揭开了克里斯蒂安内心隐藏的秘密,也打破了自我囚禁的破碎世界,她在和罗伦结婚之前,和一个名叫克劳的人陷入了恋爱之中,克里斯蒂安后来对克劳的姐姐吉妮讲出了自己的这个秘密,“没错,我对他的爱情是一种美妙的体验,这样一份美丽的爱情,就跟你猜到的一样……完全征服了我……”克劳也许是她真正爱过的唯一一个人,但是克劳后来成为了本笃会的修士莫里斯神父,这封信就是莫里斯在死之前写给克里斯蒂安的。
| 编号:E39·2240905·2175 |
一封信和一种死亡,再次揭开了克里斯蒂安埋藏已久的秘密,吉妮告诉她的是,克劳一直背负着对克里斯蒂安的爱,“就像背负着他自己的十字架一样”,也就是说,虽然他已将自己奉献给上帝,但是也为爱情留下了位置,这种爱情显然已经超越了肉体,“他觉察出自己对你负有一种神秘的责任……对,一种灵性的父爱。”他每天在为克里斯蒂安祈祷,希望她能够蒙受光照,那么克劳的祈祷之光能否拯救这个破碎的世界?能否在克里斯蒂安的灵魂之处显现出来?当克里斯蒂安听说克劳之死后,她认为曾经他们矮的刻骨铭心,但是当两个人分开之后,她的灵魂也早已经变成了“描摹灵魂形象的一格讽刺漫画”,但是当吉妮说完之后,在内心的体验中,克里斯蒂安似乎看见了什么,那就是一道照在她身上的灵性之光,按照吉妮的说法,克里斯蒂安之所以感受到了那道光,就在于克劳已经化身为她的守护圣者了,克里斯蒂安终于得到了解救,她把带来这一信息的吉妮也称为“真理的精神”,终于她回到了罗伦的怀抱,“我发誓,从今以后,我完全属于你,只属于你一个人。我现在已经是被解救了的人……就像终于从一个好长的噩梦中醒来。现在,一切的关键都在你,都看你了……”
虽然四幕剧最后的转变显得有些突兀,但是克里斯蒂安从戴着面具生活到被一道光照亮,从自我的囚徒到发现真理的精神,就很好地阐述了一种“奥秘”的价值和“第二反省”的精神,正如罗洛所说,“就好像你从死里复活,回到我的身边来……”克里斯蒂安的复活是爱,是祈祷,是灵魂发现,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了守护圣者,这并非单纯从宗教角度的再生,而是马赛尔所说的爱与忠信,而这就构成了从“存有”到存在的进路。关于存有,虽然六次访谈中都有所提及,但是访谈本身具有的对话性往往意味着一种破碎,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取决于两人讨论的现场状态,一个议题没有被深入而透彻地阐述,又转向了另一个议题——毕竟,保罗·利科是在学生时代三十年后重访自己的老师马赛尔,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更多是叙旧,而不再是曾经年轻时在马赛尔家的“哲学星期五”中的切磋。但是在陆达诚的《导读》里,关于马赛尔提出的存有观点和互为主体性有一些介绍:存有是和存在相关的概念——马赛尔的著作《是与有》就阐述了存有和存在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存有?“我的身体”就是一个我拥有的事物,它和我共同拥有我所有的“有”,所以“我”就是一个取体存有,“我的身体”和“我”的一元关系就是“有”参与“是”的特例,马赛尔认为这个一元关系不是“问题”而是一种奥秘,这种奥秘就构成了马赛尔的存在哲学:“有”牵涉渴望占有和害怕失落;“是”引发的是同在、互为主体性、临在和爱的正面经验。
从“有”参与而成为“是”,参与的过程就是互为主体性的发现,因为马赛尔就是保留了“存有”无法被知识论入侵的空间,它所保留的是他者的位置,“人的现象的客观性不能通过一个知识论式的还原过程,而是通过具体的互为主体的成为可能。”那么这个和存有建立主体间性的他者到底是什么?在第一次访谈中,保罗·利科确定的主题是“探索”,在马赛尔谈到“用辩证来摆脱辩证”的方法论之外,他说到了存在,在他看来,“存在绝无可能化约成任何别的东西,或对它产生怀疑。”这就是“是”的先决性,存在是任何一个思想的先决条件,我们不能再存在外边看到客体。在第二次访谈中,保罗·利科则提出了存有的问题:当我们谈论‘存有’时,我们究竟意愿说什么,我们的意图和目标是什么?”马赛尔的著作对存有有过阐释,在《形上日记》中他说:“存有不会欺骗人。当我们的期待得到满足时,‘存有’就有了。”存有就是一个人人都参与的期待,“‘不必有所期待。只有不期待什么的人,才不会被欺骗。’我相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询问存有的问题。”在《是与有》中,“‘存在’常是‘存有’的一种特定方式。我们应当考察这是否是唯一的方式。可能有一种只是‘有’而不存在的东西。”
按照保罗·利科的理解,存有指向的是“本体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不再只是谈及存在的无可怀疑之物,“而是指一个被遗忘的生命底层的复苏。”甚至保罗·利科将本体存有和完全主体性的“我思”置于势不两立的关系之中,马赛尔再次强调存在是任何事物的先决条件,他同时认为存有必须和经验结合起来,这里他提出了“第二反省”,如果说第一反省意指批判和解构,那么“第二反省”则是一种“再生的反省”,“我要再生,用一种聪明及可理解的方法,而不是用一种纯主观的直觉。”马赛尔所说的“再生”和保罗·利科所说的“复苏”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如何实现“再生的反省”?如何让被遗忘的生命实现复苏?这里就涉及到马赛尔所说的“期待”,他从自己从无神论者到成皈依天主教谈到了转变问题,“我觉得在基督信仰中有十分深沉的东西,而我身为哲学研究者,有责任要找到使它可以表达为被人理解的概念。这是加诸我一个有关可理解性的问题。”这既是马赛尔从基督教中寻找期待的一种实践,也是他站在信仰与学说之间成为边缘者的努力,边缘者就是在信者和不信者之间建立对话,“我一面背靠着基督教,更确切地说天主教,但为了可以与非基督徒对话,使他了解我所讲的,或许这样可以使他们得益。”
构建对话的可能,马赛尔将自己的信仰变成了哲学的阐述,这里就从期待进入到了另一个存有的维度里,那就是忠信,他相信存有是一个神圣的实体,而忠信就是一种“人内的人性品质”——他谈到了德雷福斯事件对自己的影响,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参战,谈到了科技本身的无辜性,核心则是马赛尔所说的正义,“正义的问题有优位,我们应当采取一个柏拉图所取的立场,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把正义放在最高位置,难免不退步堕落。”而正义问题其实是一种人性的关怀,“我试着要完成的任务是:重建位格和位格的尊严的传统诠释……”在最后一次访谈中,马赛尔直接指出了互为主体性的真正目标,那就是:向他者开放。可能在这种开放中,自我会成为最大的阻碍,如果自我堵塞了这种开放,那么他就变成了自己的囚犯,对他者开放的意义就是爱德,就是博爱,就是对自己的“体认”,“对我而言,人之为人,或许在于最后体认自己的缺失,及自己的错误。”
自称是“新苏格拉底主义者”的马赛尔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把人导向一个远方,一个彼界,而是回到苏格拉底精神的核心,那就是谦逊,就是平等,“在我们之所是,我们身为平等的存有,我们是主体这方面,我们必须体认有一种暧昧性格。”所以要向他者开放,要穿过自我的迷宫,要通过经验的体认找到希望之光,“我在你内为我们希望。”这就是从存有通往存在的征途,它是冒险,是忍耐,是祈祷,是《破碎的世界》中的“真理的精神”,更是马赛尔笔下的《旅途之人》:“变形的精神。当我们试图清除使我们与另一王国分隔的边境阴霾时,请您指导我们新手的行动!待规定的时间一到,请您唤醒旅人身体内的生气,使我们肩负背包,精神抖擞地起步,那时,晨曦在因蒸气而显朦胧的窗后悠悠地升现!”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