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08《迷宫案》:身后只有一个空字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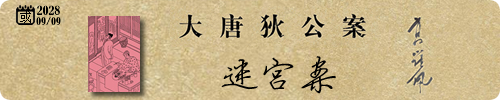
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浓缩在倪守谦所写的关于地蚓与天龙的对子中。
——《后记》
对子来自一本禅宗的佛经,是神秘的鹤衣隐士留给狄公的,“长生门前两条路,地蚓掘土天龙飞”,地龙掘土和飞龙升天指向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一条在地,一条在天,所对应的则是鹤衣隐士的选择和狄公的抱负,或者更直接一点,分别代表道教思想和儒家价值——“狄公作为正统的儒家学者与官员,对于儒家教义尊崇备至,极其重视公平、正义、仁慈、责任等公认的道德价值。鹤衣先生却恰恰相反,坚持道家准则,认为所有现实价值都具有相对性,提倡超越善恶之上的无为人生,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当高罗佩在结尾处再次引出这个对子,在人生不同选择中,狄公似乎获得了某种启悟:当破解了“迷宫案”,关于丁护国之死,关于倪守谦之谜,都已大白于天下,而狄公也有了辞官归因之心,“自己刚过不惑之年,回到家乡购置一座小田庄,重新开始恬淡生活,倒也为时不晚。”但是当他再次寻访鹤衣隐士的时候,他早已不见了踪影,狄公只是遇见了山上的樵夫,樵夫对他说的是:“如他那般之人,根本不会像你我这样寻常死去!他们自始便不是世间人,临到头来,也会如天龙一般飞升而去,身后不留一丝痕迹,只有一个空字而已!”隐士不在人世间,他早已化作飞龙飞升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身后只留一个空字,似乎就是对狄公的某种暗示,或者这个透解了隐士人生信条的樵夫也是“飞龙”的化身。狄公有所悟,在兰坊经历了这一切,狄公看到了恬淡之意义;当狄公还是无法跟随隐士而去,他最后笑着说:“不错,不错,我既身为世间人,还是仍旧埋头掘土去也!”
道家代表鹤衣隐士如飞龙远去,身后留下的是耐人琢磨的空字,狄公有所悟,但终归还是回到了儒家之途中,甘心做一个掘土的地蚓也许也是他的使命所在。儒家与道家短暂地有所交集,高罗佩引入鹤衣隐士这个神秘人物,一方面和倪守谦留下的“迷宫”联系起来,正是在迷宫的入口处,写着几句诗“歧路回环,可逾千里;直指人心,不过毫厘。”被青苔遮住的落款就是“鹤衣隐士”,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诗是实指,迷宫是“歧路回环”的结构,也是虚指,人生之路何尝不是充满了歧路?另一方面当然提供了人生的另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又和对疑案的破解联系在一起,当狄公希冀从他那里获得迷宫的线索时,隐士对他说的是:“问一事,接着便要问二事三事。试想那些丢下网罟缘木求鱼之徒,你与他们有何两样!又好似先在船底凿一大洞,却指望此船能涉江渡河一般!心中如有疑问,若是找对了方向,或许有朝一日,你自会寻到最终的答案。后会有期!”
不做机械般的缘木求鱼之徒,要学会从问题出发找到对的方向,这就是面对迷宫的态度,狄公或许就是从这句话得到了破解迷宫的办法,最终揭露了真相,而在这个意义上,狄公从“歧路回环”中找到了“直指人心”的办法,最终解答出了心中的疑问,鹤衣隐士的确帮助了他,但是狄公最终还是没有辞官归隐,还是无法成为像鹤衣隐士那样的人,他承认自己是世间之人,是掘土的地蚓,也就意味着他依然还要恪守儒家的思想,还是要在家的公平、正义、仁慈、责任的道德框架中前行——这或者可以称作是感悟式回归,在更加透彻理解人性之外,也可以更好地为百姓服务,两种观念之结合,使得狄公在高罗佩笔下越来越接近儒家为国为民的完美形象。
但是,在《迷宫案》中狄公又遭受了何种迷宫的困扰,又如何看清身后的空字?《迷宫案》的整体结构和其他几部狄公小说并无二致,“笔者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借用了三个故事,重新组织后写成了一部情节连贯的小说”,高罗佩将案件三合一的处理,在这里似乎并不仅仅在于简单的三个疑案,他在《后记》中说到了三个案件的出处:密室杀人案取材于明代奸臣严世蕃的一则轶事,“据说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毛笔,靠近烛火后会射出致命的暗器。”秘密遗嘱案取材于中国古代的故事,在《棠阴比事》、《龙图公案》和《今古奇观》中均有记载;无头女尸案在公安案小说中较为常见,只是高罗佩在这里将其演化为“同性之爱”的故事;除了这三个案件之外,最主要的则是迷宫故事,高罗佩认为迷宫在中国公案小说中并不是常见题材,他是从中国的香炉盖子中获得启示,“中国人习惯将一片刻出纹样的镂空薄铜板盖在装满香粉的容器上,当香粉从一端燃着之后,会像导火线一般沿着图样缓缓烧下去。”这是一种像极了歧路回环的结构,所以高罗佩从香炉的图案获得灵感,在小说中将迷宫的线路变成了一张《虚空楼阁》的绘画,“虚空楼阁”这几个篆字正好形成了迷宫的路线。
除了三个案子结合在一起形成破案的故事,高罗佩在楔子中也是按照以前的惯例,设置了“当下”的一个场景,“值此大明永乐年间,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四方无旱无涝,万民富足乐业。凡此种种,全赖当今圣上仁德。”时空倒错,社会秩序异样,第一人称的“鄙人”又是一个喜欢钻研前朝断案故事的人,所以自然引出他心目中的断案英雄狄仁杰,那天他出门经过莲池,看到了男人和女人,之后他们又消失不见,后来遇到了一个老者,一起喝酒时老者说起自己就是山西人,当然也知道身为太原人的狄仁杰,“想当年,这位受人尊崇的狄家先祖曾经担任过兰坊县令。兰坊地处偏僻,远在大唐西北边陲,饶是当日情势非常,狄公仍然设法破获了三桩惊世大案,老夫这便与你细细讲来。”于是被老者讲述的故事便成为了“我”的素材,当酒过三巡睡去醒来,老者已不见踪影,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如梦中所见一样:西北边陲并无兰坊这一地方,老者也转身不见,和莲池一样像是想象之物,但是从老者那里听来的“三桩惊世大案”却还记得,于是我提笔写下了这奇异故事,“如今我斗胆将这段故事向诸君道来,至于莲池边的一段奇遇究竟是梦是真,不如也留给目光如炬的各位看官去自行定夺。”
| 编号:C38·2221004·1882 |
引入大明盛世,引入喜欢断案故事的读者,引入路遇的老者,最终都是为了引入惊世大案,是真是假,是虚是实,其实都不重要了。高罗佩的这种引入方式在其他几部小说中已屡试不爽,这次的引入除了恍惚的梦境之外,哲思性的意义似乎被减弱了不少,甚至变成了为引入而引入,和狄公故事的展开也并无多少过渡的意义。但是显然我对奇遇之真实性的怀疑契合了狄公在整个故事中对“歧路回环”的疑问和破解,那么在兰坊发生的三个甚至更多的案件如何形成密谜案的复杂线索?新任兰坊县令,狄公在赴任过程中先是在路上遭遇险情,之后发现城内冷冷清清,商户都关门闭户,整个兰坊显出几分异样,后来得知是一个名叫钱茂的人一手遮天,“兰坊一半田地和超过两成的店铺房产都归他所有,不但包揽了全县的政事、讼事与军务,还定期给州府官员们赠送贿银,派人骑马前去,五日便可到达,声称如果不是有他坐镇,胡人早已越过疆界攻占了兰坊,那些人听了,也都信以为真。”甚至四年前的潘县令想要调查钱茂也被割喉遇害。
于是狄公着手要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立兰坊的秩序,在他势如破竹的整饬过程中,钱茂被轻易打掉,但是钱茂本人手上,当狄公问他:“究竟是谁杀害了潘县令?”两眼喷火瞪的钱茂只是口唇翕动一下,然后使尽全身力气,含混吐出了一个字便又声息全无。钱茂以气绝身亡的方式断绝了线索,但是他最后说出的“你”后来变成了最重要的破案线索。钱茂虽死,但是他能够一手遮天并非靠武力,内中必然牵涉到他的后台,而根据调查还有一个神秘谋士,“区区一名兰坊乡民,哪能晓得如何应付刺史,又如何与朝廷大员们周旋呢?总是在那神秘人物来过之后,他便会使出不少高明的手段来,从而避免了刺史插手兰坊本地事务。”这个裹着僧袍、黑巾缠头、深夜徒步而来的神秘人士谁也没有见过他的真实面容。
钱茂背后的恶势力以及神秘谋士,自然是另一个故事的线索。而狄公在基本处理了钱茂恶霸之后,遇到了另两件案子,一件是“倪氏兄弟案”,此案是由倪守谦身后的遗产分配而引发。曾任节度使的倪守谦已于九年前过世,根据案卷所述,倪守谦下葬之后,大儿子倪继便立即将继母幼弟倪善逐出家门,“声称其父临终前的遗言分明暗示出倪善并非倪家骨血,梅氏既然不守妇道,自己也就无须照拂她母子二人。”另一个案件则是丁护国被害案,而其实在丁护国被害之前,他的儿子丁毅就前来找狄公,说有人要害父亲,而这个嫌疑人就是吴峰,按照丁毅的说法,““家父在京师的一班故旧好友已然寻出了当年诬告的证据,那姓吴的得到风声,为了救自己一条狗命,于是派遣其子前来谋害家父。”
倪公模棱两可的临终遗言、有人预先昭告丁将军会被谋害,这两件案子却让狄公深感兴味,而事件的走向似乎并无意外:丁护国被人杀害在自己的书房,“骨瘦如柴的喉头处插着窄窄一片薄刃,仅有一寸来长,厚度不及半指,露在外面的原木刀柄样式奇特,只比刀刃略厚,长短仅有半寸。”丁护国的死带来了两个疑问:丁毅为什么会有预言?丁护国又如何被人闯入密室杀死?吴峰当然是应该调查的人,狄公在深入对丁毅口中的嫌犯吴峰的调查中,发现喜欢绘制佛像的他,其实笔下的女菩萨却有一个女人的影子,“女菩萨通常都画得平和安详,不带一些烟火气,但是此画却更像是一幅活生生的凡间女子肖像!”由此判断他深爱着一个女子,而方班头的女儿白兰也在那时失踪,狄公让白兰的妹妹玄兰深入丁家打探消息,玄兰在丁毅的抽屉里发现了很多诗文书信,无疑也是写给女人的——丁毅和吴峰是不是爱着同一个女人,所以才会变成仇人?
狄公从吴峰的口中得知,当年丁护国来到兰坊正是为了躲避当年犯下的罪,“那老贼当年为了自已脱困,送了整整一营官军的性命,致使八百名大好男儿全被胡人残杀。当时军中已多有怨声,若非虑及军心不稳,丁护国定会被依律斩首。朝廷欲将这一丑事遮掩过去,因此勒令他休致还家。”实际上丁护国的这一举动让他树敌过多。在丁护国被害案展开的同时,倪公那份模棱两可的遗言也正在调查中,狄公看出的端倪是:“我深信这份遗嘱是由倪继伪造而成。”倪夫人提供的那幅名为《虚空楼阁》的图在狄公看来藏有重要的线索,“据我想来,倪公在这幅画中藏入了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书,为的是引着倪继误人歧途。正如我曾经所言,倪公若将真正重要之物藏在此处的话,手法未免过于粗糙。除去这一障眼法之外,此画中必是以更加巧妙的方式藏有真正的线索。”
两起案件的线索似乎在各自的轨道上发展,但是当狄公终于从丁护国被害中找到装有有毒梅子的盒子,发现里面有吴峰的朱红印记,被证实吴峰画中的女子便是白兰,两条线索终于汇集在一处:杀人的武器是一支笔管,笔管中刻有“恭贺自省斋主人六十华诞,静庐拜祝”字样,也就是说,杀人者是九年前死去的倪守谦,“制作此笔之人将藤丝塞入笔管中,并尽力压到最底处,再用一根中空的管子将熔化的漆树树脂倒人,一直等到树脂完全于凝,方才拿掉管子,并换上此物。”这是何等严密的一个杀人现场,倪守谦在生前布置的机关终于在丁护国动到厄兰笔管时触发了机关——倪守谦为何要杀害丁护国?““朝廷出于大局考虑,不便对令尊公开定罪,倪节度便决意亲手将他处决,以示天理昭彰、罪有应得。倪节度英勇无畏,若不是为自己家人考虑,不想他们受到牵连的话,大可公然取了令尊性命,于是决心等到自己不受律法约束时再行此事。”
丁护国之死和当年的案件有关,“罪有应得”的背后是对于秩序的维护,而另一起案件中的主角则是倪继,他正是钱茂的谋士,也是四年前杀害潘县令的凶手,而现在更大的阴谋则是:和回纥蓝部的乌尔金王子勾结准备攻下兰坊自立为王——钱茂死之前说出的“你”其实是“倪”。当然,狄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倪守谦当初建造的那座迷宫才是最终解开谜案的关键,而那张《虚空楼阁》才是迷宫的线路图。狄公根据线路图走进迷宫,最终发现了倪公留下的真正遗嘱,揭开了倪继的阴谋,同事也发现了一具女尸,而那具女尸正是被害的白兰——由白兰之死引出了劫持少女的邪恶之女李女士。
除了白兰之死纯粹是一种私欲引发的惨案,丁护国被害案和倪公迷宫中的遗嘱,都指向了官场的秩序问题,而狄公破解此案也化解了兰坊异族部落攻城的野心,在这个意义上狄公看到了道统的失序状态,所以他才会从鹤衣隐士那里受到启发,想要离开官场这个是非之地,如隐士一般做飞龙在天的自由生活。但是狄公还是回到了地蚓的世界,一面是妥协,毕竟身后的空字不是每个人都能书写的,另一方面则是回归自己的职责,身为世间人也无法躲开这些现实问题,重要的是维护秩序,身上的补子图样便是身份的象征,权力的象征,追求正义的象征,“须知举国上下,每时每刻,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身穿有此纹样的公服,都在为天下万民主持公道。”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