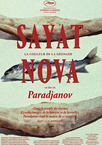2023-10-06《石榴的颜色》:让我回归大地吧

“石榴的颜色”是石榴汁呈现的颜色,它是满目的红,是流动的红,是鲜艳的红,红是火焰的燃烧,是激情的象征,是血液的颜色,当“石榴的颜色”以火焰、激情和血液而书写,它是诗歌,是爱情,是故乡,是死亡,是信仰,而所有一切最终变成土地的赞歌:就像石榴,从土地里出生和生长,最后流淌、渗入而回归于土地中,“你赐予的面包很美好,但土壤更加美好,让我回归大地吧,我很疲倦,很疲倦了……”在身上被覆盖了石榴的红色之后,诗人终于从肉身消失中死去,变成永恒大地的一部分。
从出生到死亡,从肉身的沉寂到大地的回归,从苦难的人生到永恒的信仰,这便是帕拉杰诺夫所构筑的诗人一生。《石榴的颜色》原名《莎耶特·诺瓦》,莎耶特·诺瓦是十八世纪亚美尼亚著名的吟游诗人,年轻时受到格鲁吉亚国王的赏识,被召入宫成为宫廷诗人,晚年则笃信宗教成为僧侣,避世于修道院。从《莎耶特·诺瓦》到《石榴的颜色》,片名的变化似乎是帕拉杰诺夫从纪实到写意的一种改变,电影取材于诺瓦的故事,但是在这部完全是诗意影像化呈现的电影里,诗人、诗歌完全化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苦难和追寻,“本片并非试图讲述一位世人的人生,而是通过他灵魂的不安、激情和磨难,尽力展现诗人的内心世界,并运用大量象征及讽喻,描绘中世纪亚美尼亚吟咏诗人的传统……”
诗人是一种象征,诗歌也是一种隐喻,它传达的便是这段字幕之后的一句话:“我是一个身心皆充满痛苦的人……”展开的画面中,是流淌在白布上的石榴汁,是一把沾着红色液体的刀,是双脚踩着的葡萄,是鱼和骨头,是白色的花,是荆棘……每一件物品都具有象征意义,而在“石榴的颜色”第一次呈现中,它就混杂着生与死,快意与苦难,在静态的画面中,它们组成了关于诗人人生的不同序列。“原始之初,上帝创造了天与地,第六天上帝说现在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意愿……”在雷电、石碑和暴雨的呈现中,上帝造人所书写的“创世纪”缓缓打开,这是“生”的启示,它是生命之生,是诗人之生,是诗歌之生,当母亲为孩子盖上被子,字幕写下的是“我”出生的意义:“许多人先我而来,却对这个世界鲜有了解,故他们先我而消亡……”
出生和消亡,对于从世界面前匆匆走过的人来说,生和死形成的闭合系统只是肉身的一次抵达,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了解这个世界,不了解世界也就不了解自己的内心,所以诗人出生的意义就是摆脱肉身,摆脱物质,了解世界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出生就必然指向诗人的出生,指向精神意义的出生,内在精神的诗人便是亚美尼亚的“传统”,抒情诗人VALEIR BRIOUSSOV曾说过:“中世纪亚美尼亚的诗是雕刻在宇宙历史中人类精神最辉煌的胜利。”童年时期的诗人,拥有的是象征灵魂和生命的书,它们被翻开,被晾晒,被阅读;拥有的是丰富的颜色,它们染上了那些织物上,组成了生活丰富多彩的意象;他们拥有信仰带来的光辉,“圣乔治,我们恳求你,将你的才思撒向我们的家族,我们的人民……”
| 导演: 谢尔盖·帕拉杰诺夫 |
所以对于本就以诗人之精神出生为象征的序曲里,诗人最终拥有的是一把七弦琴,“从这个世界的色彩和芬芳中,我用童年制作了一把诗人的七弦琴。”诗人的七弦琴奏出美妙的音乐,这便是流动的美,而这也对应于“石榴的颜色”具有的流动性,而对于诗人来说,他的出生就意味着一次征途,“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寻找自我……”这自我从何处寻找?在每一个人身上就是对个体的逃离,就是对世界的介入,自我在经书上,在镜子里,在食物中,也在对世界不断地了解中,而这种了解混合着太多的苦难。“健康而美好的生活之中,我一直承受着煎熬——何以至此?”不断的成长,就意味着不断对世界发出质疑,不断在苦难中寻找答案。从童年到成年,他看见了战争,公主在裹尸布上写下的祭文:“你弃我们而去,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讲你包裹在金缕衣中,以便来世化为一双蝴蝶。”从童年到成年,他看到了爱情的脆弱,“我该如何保护用蜡做成的爱之城堡,免于被你炙热的火焰?”诗人用尽全力,终究无法挽回被怒火摧毁的爱情;从童年到成年,他更是看见了死亡,“我们在寻找一处爱的避难所,但相反,那时一条通往死亡的路。”
白色的裹尸布上,那血红的颜色仿佛是“石榴的颜色”的再一次呈现,只是不是童年时如七弦琴的流动之美,而是燃烧着的火红,“你是火,你身穿火焰,你是火,你身穿漆黑。两种火焰,我能承受哪一种呢?”火焰之火和灰烬之火,红色之火和黑色之火,那爱的城堡仿佛也在这火之红色中坍塌。“石榴的颜色”在两次呈现中变成了两种意象,具有双重含义。而在火焰的红带来的燃烧甚至毁灭中,诗人开始了寻找,“去寻找你无私的爱的避难所,我会一个接一个地寻遍所有的修道院……”修道院是接近上帝、表达信仰的场所,他在祈祷,在忏悔,在求得原谅,在获得救赎,就像孩子的受洗一样,在礼仪中接近上帝。但是修道院也呈现出人世的苦难,“作为一群天真的受害者,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给你作为献祭……”大教长在埃奇米阿津主教堂去世,死亡带来的是混乱,那一大群羊围在逝者身边,诗人必须穿越过去为大教长盖上,并下跪祈祷,“我想要一块裹尸布来包裹尸体,他们活生生的脸上,却露出扭曲的表情,我在何处才能找到无私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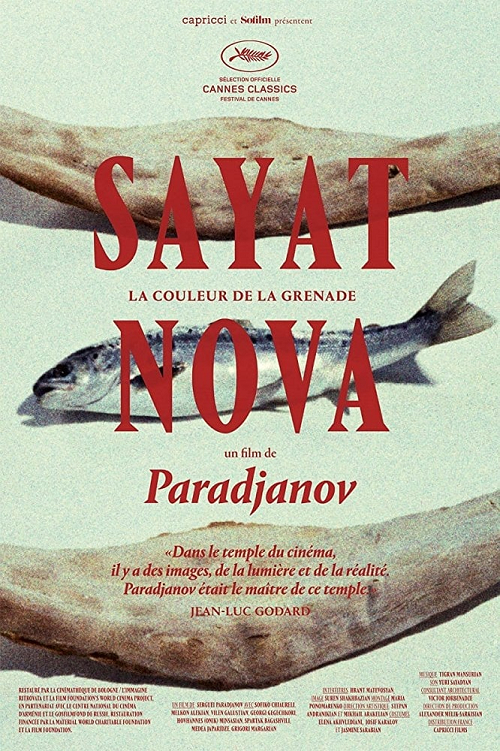
《石榴的颜色》电影海报
质问只为了另一种寻找,梦境展开,诗人看到了童年之光,“在遥远的阳光谷场住着我的乡愁,我的爱,我的童年。”一只手遮挡住了他的眼睛,“你是火,你身穿一片漆黑……”女人在他面前不断重复,那种童年的流动之美又被火焰吞噬成了一片漆黑,于是过去的一幕幕再现,它们是唱歌的女人,是吹鼓的仪式,是献祭的公鸡,是父母,是战争,是爱情,也是那经历的苦难,“我看到了一切,都清晰且怪异,然后我明白生命已将我抛弃。”当生命被抛弃,肉身意义的死亡降临,他等待着不想改变的结局,“世界是一扇窗,透过它看的人被烧得透焦,而我厌倦了这灼烧,昨天好过今天,而我厌倦了明天。人不可能总千篇一律,但我已厌倦任何改变。”内心满的是悲伤,当厌倦了明天,还有什么可以重建希望?
从童年到成年再到老年,诗人的一生被昨天、今天和明天构建,当“昨天好过今天”,他需要的是回归,这种回归是死亡之后的开始,是精神的重生,“我依稀听见归还希望的呼唤,但我已经疲倦,是谁在这苍老而疲惫的大地上散布所有的悲伤?”支撑着诗人一生的是爱,爱情之爱,上帝之爱,诗歌之爱,以及“石榴的颜色”之爱,而最后在死亡降临的时候就是将爱变成了一首大地之歌,“我的生命属于你,我的爱人,只要我活着,重新拿起七弦琴。”回乡之旅就是大地的回归之旅,上面不满了十字架,也流淌出了最初生命诞生的流水之美。
“我的苦难已经满溢。”这何尝不是流动之美?所以“石榴的颜色”最后具有了大地的象征,从童年七弦琴里的“流水之美”,到成年变成火焰而燃烧的漆黑,“石榴的颜色”经历了双重的转变,最后又回归到大地,从水到火再到土,这是生命生成的过程,这是精神追寻的结果,这是信仰完成的标志,而帕拉杰诺夫也以语言的诗化、色彩的明艳、构图的奇特均衡、内容上的仪式感,完成了一次心灵之旅,以多重隐喻的《石榴的颜色》完成了最后的回归。而诗人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帕拉杰诺夫的苦难写照,被逮捕,被劳改,被禁拍电影,当他被允许拍摄电影时,在苦难的折磨下,帕拉杰诺夫已经看见了漆黑之火,被生活摧残了身体的他最终在1990年去世,但是影像不朽,死亡是他新生的呼喊,“让我回归大地吧……”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272]
顾后:《美国大兵》:死比爱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