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10《伦理学》:最高的善是对神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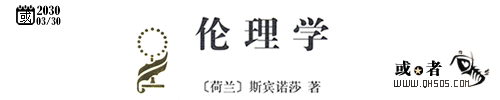
成见:自然万物,与人一样,都是为着达到某种目的而行动这一点。并且他相信神作育万物皆导向一定的目的。
——《第一部分 论神》
万物之存在,当然有它存在的意义,当然由它必然的价值,但是存在所表现的意义和价值就是目的本身?或者说,当万物产生,它自身是不是就带有目的性?肯定的说法在斯宾诺莎那里就成为了成见,而对于成见他必须进行驳斥——斯宾诺莎的驳斥首先就在于万物的有用论:自然万物,的确很多对人是有利的,但是还有很多是有害的,比如风霜雷电,比如暴雨地震,比如疾病灾害,当它们成为有害的存在,它的目的性在哪里?其次,当万物是为了人用这一目的,那必定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甚至有害的,必定区别了价值和无价值,必定会被重视和忽视,当人们以价值来解释自然万物,便有了善恶、冷热、美丑等观念,再加上人也有自由或不自由的目的,便产生了褒贬、功罪等观念,既然人的目的是衡量的标准,那么自然万物为什么会产生会被创造?或者说,无用的、有害的东西为什么会存在?
其实,这种成见在斯宾诺莎看来,并不是在人这一维度上成为了成见,而是神创造万物变成了一种目的论,如果神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为了达到神的某种目的,那么最先的东西就是为了最后的东西而存在,而最后的东西在目的论中就必然超出了一切,那么最先的东西产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直接可以说,神创造最后有用的东西就可以了。再者,神如果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动作,那么神就是在寻求它所缺乏的东西,而神怎么可能有所欠缺的,有所欠缺就是一种不圆满,这样也就否认了神的圆满性。斯宾诺莎对于这一成见的驳斥,不管是基于人的有用性还是神的目的论,其实度为了指出成见本身就是一种观念,而这些观念“不过是些想象的产品罢了”,因为它们只是想象事物的存在,而不能揭示事物的本性,“所以我只好称它们为想象的存在,而非理性的存在。”
第一部分的“附录”部分,斯宾诺莎对成见的驳斥,就是将其看做是想象的“观念”,从而指出了它是“非理性”的存在,这也就表明,斯宾诺莎对于神的创造、神的圆满,以及对于万物之存在的认识,必然要在理性之下。但是这只是斯宾诺莎理性主义的一个序曲,他首先要做的是界定神本身,第一部分“论神”就是关于神的“知识”。作为十七世纪的伟大哲学家,斯宾诺莎其实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者,但是他知道否认神是造物主就不会得到教会的宽容——这部花费了十三年功夫的著作,斯宾诺莎并没有在生前发表,而且在他逝世后出版也被当局视为“亵渎的、无神论的学说”。为什么斯宾诺莎将神放在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存在位置,还会被当局视为无神论,还会被教会所迫害?原因只有一个,斯宾诺莎的神不是神学意义上的神,更不是宗教维度的神,而是实体的神,自然界的神——这就是斯宾诺莎超越神学的伟大之处。
而要认识这样的神,就必须从“论神”中展开。斯宾诺莎的阐述最重要的就是在“界说”中确立了概念:他提出了“自因”,“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即包含存在,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自因意味着本质包含了存在,正是这一学说,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第一次摆脱了中世纪以来神学的羁绊,扔开了第一推动力的信仰主义;他提出了“实体”的概念,“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也就是说,实体无需借助他物而被自身认识;而属性则是“由知性看来是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样式是实体的分殊,是在他物内通过他物而被认识的东西;在这里,斯宾诺莎提出了神的概念,他认为神是一种“绝对无限的存在”,是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每一属性都表示永恒无限的本质,这个关于神的概念很明显是一种实体说,而且是绝对无限的存在,也否定了神是“自类无限”,自类无限是“为同性质的另一事物所限制的东西”,显然神不是自类无限的,因为神的无限包含了一切表示本质的东西,它不包含自类无限的否定;接着,斯宾诺莎又界说了“自由”:“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界说了“永恒”:“我理解为存在的自身,就存在被理解为只能从永恒事物的界说中必然推出而言。”
第一部分的八条界说确定了斯宾诺莎最重要的概念,“公则”部分则提出了事物认识的公理:一切事物不是在自身内,就必定是在他物内;一切事物,如果不能通过他物而被认识,就必定通过自身而被认识;如果有确定原因,则必定有结果相随,反之,如果无确定的原因,则决无结果相随;认识结果有赖于认识原因,并且也包含了认识原因;凡两物间无相互共同之点,则这物不能借那物而被理解,换言之,这物的概念不包含那物的概念;真观念必定符合它的对象;凡是可以设想为不存在的东西,则它的本质不包含存在。而之后提出的命题,则首先从实体的概念出发,实体的本性先于分殊,实体的属性不同只是分殊各异,实体的本性决定相同属性的实体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实体是唯一的实体,由此斯宾诺莎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一个实体不能为另一个实体所产生;每一个实体必然是无限的;实体的每一个属性必然是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
提出实体的命题,斯宾诺莎其实就是为了引向神,在“命题十一”中他第一次将神和实体并置在一起:“神,或实体,具有无限多的属性,而它的每一个属性各表示其永恒无限的本质,必然存在。”对于这个命题,他首先证明:神不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神必然存在”;他又提出了“别证”:不存在一定有不存在的原因,如果没有原因否定其存在,那必然存在,因为神没有不存在的原因,所以神必然存在,“这是自明的道理”;另一个“别证”是:不能够存在就是无力,能够存在就是有力,神是绝对无限的东西,所以必然存在;斯宾诺莎又进行了“附释”,从后天方面可以证明神的存在,同样从先天方面也可以证明神的存在,由此斯宾诺莎进一步确证了这一命题:“所以我们所最深信不疑的存在,除了绝对无限、绝对圆满的存在,即神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这一深化的意义就在于指出神包含着绝对圆满性,所以神就是最高的确定性。
| 编号:B35·2231113·2027 |
从这里开始,斯宾诺莎真正开始了“论神”:除了神之外,不能有任何实体,也不能设想任何实体;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于神之内,没有神就不能有任何东西存在,也不能有任何东西被认识;神是无限理智对象的制动因,神凭借自身的原因而不是凭借偶然的原因,神是绝对的第一原因;神是万物的内因,而不是万物的外因;神的一切属性都是永恒的;神的存在与神的本质是同一的;神的力量就是神的本质本身……“论神”就是在把神界定为唯一的实体中解说了神的本性和特质:
神必然存在;神是唯一的;神只是由它的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和动作;神是万物的自由因,以及神在什么方式下是万物的自由因;万物都在神之内,都依靠神,因而没有神就既不能存在,也不能被理解:最后,我又说明了,万物都预先为神所决定——并不是为神的自由意志或绝对任性所决定,而是为神的绝对本性或无限力量所决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才得以展开,因为神和理性之间可以建立关系。第二部分是“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在斯宾诺莎看来,从神或永恒无限存在的本质必然而出的那些东西就能揭开心灵的性质,因为心灵就是人的心灵,人就是神或永恒无限存在的本质必然而出的那些东西。同样,他界说了物体的概念,“我理解为在某种一定的方式下表示神的本质的样式”;界说了“观念”,“我理解为心灵所形成的概念,因为心灵是能思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斯宾诺莎提出了“实在性和圆满性是同一”的重要观点,这也为之后“伦理学部分”的解说奠定了基础。在“公则”部分,斯宾诺莎对人提出了公理:人的本质不包含必然的存在;人有思想;思想的不同样式依赖于观念;身体和思想的样式是感觉或知觉的个别事物,除此之外任何个体事物并不能被感觉或知觉。接下去斯宾诺莎的命题部分,则从人的心灵和身体提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实体的存在不属于人的本质,也就是说,实体不构成人的形成,从这里得出的“绎理”是:“人的本质是由神的属性的某些分殊构成”,所以在“命题十一”中,斯宾诺莎说:“构成人的心灵的现实存在的最初成分不外是一个现实存在着的个别事物的观念……”观念是构成人的心灵的存在的最初成分,而且观念的对象产生变化也必定为心灵所察觉;人的身体则更多为外物所刺激,也通过别的物体所保存;心灵通过人的身体因感触而起的情状产生观念,但是“对于人身以及人身的存在无所知觉”,所以,“人心只有通过知觉身体的情状的观念,才能认识其自身。”
通过观念而认识,认识而成为知识,与人心对自身的认识产生的“正确知识”不同,对于其他事物的观念而产生的知识却有不同,斯宾诺莎在这里区别了四种知识:第一种是通过感官片段地、混淆地和不依理智的秩序而呈现给我们的观念,这样的知识是“从泛泛经验而来的知识”;第二种是从记号得来的观念,它通过词语激起回忆并形成观念从而产生知识,这是一种意见或想象;第三种则是从对于事物的特质具有共同概念和正确观念而得来的观念,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就是理性,斯宾诺莎还指出了直观知识,在他看来,想象的只是会产生错误,只有理性知识和直观知识才是真知识。从这里开始,斯宾诺莎将观念的阐述印象了对理性的阐述:理性的本性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所以理性是在某种永恒的形式下来考察事物,而这也和神建立了关系:“神的无限的本质及其永恒性乃是人人所共知的。而且万物既在神内并通过神而被认识,由此可见,我们可以从关于神的知识推论出许多正确的知识”,这些正确的知识就是理性的知识。
考察神和心灵之后,斯宾诺莎开始考察情感的性质和力量,在这里他的考察方法已经变成了理性的“几何学”,“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理性就是为了证明,所哟情感的产生都有其原因,通过原因的分析就可以了解他们,就可以加以认识:“通过原因可以清楚明晰认知其结果,则这个原因便称为正确原因,反之,仅仅通过原因不能理解其结果,则这个原因便称为不正确的或部分的原因。”正确的原因就是一种主动,不正确的原因就是一种被动,而神构成任何人心中正确的观念,只有正确观念愈多,心灵便越主动也越自主,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提出了包括欲望、快乐、痛苦、惊异、轻蔑等在内各种情绪的界说,之后他总结认为,“情绪,所谓心灵的被动,乃是一个混淆的观念,通过这种观念心灵肯定其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具有比前此较大或较小的存在力量,而且由于有了这种混淆的观念,心灵便被决定而更多地思想此物,而不思想他物。”心灵的本质在于肯定身体的实际存在,而圆满性就是一物的本质,所以,“当心灵能肯定于其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分的某种东西具有比从前较大或较小的实在性时,那么心灵便是过渡到一个较大或较小的圆满性。”因为实在性就是圆满性。
实在性之多大和小,对应于圆满性之多和少,这其中就是正确的原因和不正确的原因、主动和被动、自主和奴役的区别,所以对于命运的善恶来说,就是奴役和自由的问题:斯宾诺莎对“恶”的界说是“我们确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恶则反之,那么在奴役和自由、善与恶之间,实在性和圆满性如何达到最大,那就需要理性,理性的本质就是“每个人都爱他自己”,“寻求对自己真正有利益的东西,并且人人都力求一切足以引导人达到较大圆满性的东西。”在这里斯宾诺莎提出了“德性”,德性是一种对本性的遵守,它所抵达的目标是幸福,“德性的基础即在于保持自我存在的努力,而一个人的幸福即在于他能够保持他自己的存在。”理性指导则寻求自己的利益,而他们追求的东西也是他们为别人而追求的东西,所以他们是公正、忠诚和高尚的,所以德性和理性的关系是:“绝对遵循德性而行,在我们看来,不是别的,即是在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而不管是德性还是理性,也都是神的一种呼应,“心灵的最高的善是对神的知识,心灵的最高的德性是认识神。”
这便是斯宾诺莎所建立的“伦理学”:善是对本性的符合,是遵循理性的执导,而最高的善是“人人共同的”,而且是人人皆可同等享有的,“每一个遵循德性的人为自己所追求的善,他也愿为他人而去追求。而且他具有对于神的知识愈多,则他为他人而追求此善的愿望将愈大。”但是善不是伦理学的最高目标,自由才是,“假如人们生来就是自由的,只要他们是自由的,则他们将不会形成善与恶的观念。”从善上升到自由,则是理智的力量,理智正是在理性的力量中克制感情,达到知性完善,“只要我们不为违反我们本性的情感所侵扰,我们便有力量依照理智的秩序以整理或联系身体的感触。”对于自我本性情感的遵从,就是一种自由,而这种自由“也必定爱神”,“他愈了解他自己和他的感情,那么他便愈爱神。”更关键的一点是,爱神并不要期望神来回爱自己,因为期望神回爱他,那么只能证明他要求的神不是神,不是圆满的身,只有不回爱的神才是永恒的神,而我们也将走向永恒,“所以我们的心灵只要能在永恒的形式下去认识它自己及它的身体,就必然具有对于神的知识,并且知道它是在神之内,通过神而被认识。”
从神到心灵到情感到最后的自由,斯宾诺莎给实体冠上了“神”的名义,提出了自因说,阐述了思维是物质的属性,将理性的知识看做是最可靠的知识,作为理性主义的先驱,斯宾诺莎也陷在现实造成的不自由中,但是如同发现了神性之光一样,理性也成为斯宾诺莎思想中的一道光,“但是一切高贵的事物,其难得正如它们的稀少一样。”最后必然是真知识,必然通向自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