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06《流动的盛宴》:回忆是一种饥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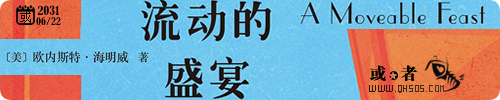
可是巴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没有简单的事情,甚至连贫困、意外发了笔小财、月光、是与非,还有在月光下躺在你身边那人的呼与吸,这一切都不简单哪。
——《一个虚假的春天》
巴黎的羊倌从乳房鼓胀的黑奶羊里挤下奶给了捧着罐子的女人,然后赶着牧羊犬离去;巴黎的男人一早在护墙广场拐角处笛卡尔路上买一份报纸,然后爬上楼梯回家;或者得到昂吉安会有一场赛马比赛的消息,即使那里扒手扎堆,但圈外人还是觉得那里适合自己……海明威就是看见羊倌把牛奶挤进罐子里,听着赶羊人远去的风笛声,然后在笛卡尔路买了一份赛马报,作为圈外人他也会在赛马的时候赌上一注——这就是海明威的巴黎生活。
那是他称之为“一个虚假的春天”,因为写作,因为赚钱,虚假的春天让海明威感到了生计的压力,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春天,一个可以大口吸进清新空气的春天,一个可以跟着羊群继续往前的春天,一个在压力的生活中寻找愉快心情的春天,“春天来临时,即使仅仅是虚假的春天,除了找寻个去处能使人过得最快乐,就再没别的问题了。”而这也许就是巴黎真正的魅力所在,贫困或者富有,虚假或者真实,是与非,呼与吸,都不简单,也都是属于春天的巴黎,“给愉快心情制造障碍的永远是人,除非是极少数像春天本身一样美好的人。”在海明威看来,巴黎是古老的城市,但是那些制造愉快心情、在虚假的春天里把一切过得不简单的人是永远年轻的,所以年轻就会有快乐,年轻就会在巴黎发现“流动的盛宴”。
那时海明威的妻子哈德莉对海明威说的一句话是:“饥饿的种类很多。春天的时候就更多了。不过春天都已经过去了。回忆,这也算是一种饥饿吧。”当巴黎那个虚假的春天过去了好多年,甚至那段时光也也和巴黎一样古老,但是在饥饿的回忆中,它依然散发着魅力,它依然是“流动的盛宴”——流动的盛宴,就在于解决饥饿的问题。“假如你有幸能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巴黎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盛宴。”1950年,海明威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流动的盛宴之所以成为巴黎的独特景观,就在于那里有过年轻时的记忆,就在于从虚假的春天里感受了最纯粹的味道,而记忆一旦成了回忆,就永远是年轻的幸福。
这种年轻的幸福是巴黎的人和事所具有的亮丽色彩。海明威的孙女玛丽·海明威介绍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1958年夏季,海明威在古巴开始撰写这本书,从冬季的爱达荷州凯彻姆到第二年春天的西班牙,海明威一直在写作,直到1960年全部竣稿,之后海明威对全书做了修改,《流动的盛宴》最后成型。这是海明威对1921年至1926年在巴黎岁月的回忆,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海明威在《序》中说书中有些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有些则不便公开,但不管如何,它们都成为了巴黎的一部分,成为了二十年代记忆中巴黎的一部分,成为了在饥饿中得到了“流动的盛宴”的一部分,而对于本书的风格,海明威认为如果有人将它看做一本小说也“未尝不可”,里面很多回忆中的细节,尤其是一大段一大段的对话,就是一种小说的写法,毕竟过去了近30年,海明威不可能将这些东西都还原为真实。但是海明威之所以爱回忆中加入了虚构的东西,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巴黎这一“流动的盛宴”里需要更亮丽的东西,“即使作为一部虚构作品,它也总有可能使作为实事来写的事情显得稍稍清晰亮丽一些。”
让人和物变得更为亮丽,无疑海明威想让三十年前巴黎的生活在回忆中变得更为温暖和浪漫,一切的平凡显得更为“不简单”。的确,这一段时光对于海明威来说即使不是刻骨铭心至少也是尤为特殊的。在海明威的笔下,巴黎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虽然自己为了生计忙于写作,小说的发表又总是碰壁,但是在巴黎发生的故事似乎都充满了温情:他会选择和肮脏、吵闹的“票友咖啡馆”完全不一样的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在温暖、洁净、气氛友好中点上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写作,或者还能看见美丽的姑娘从身边经过,“我见到你了,美丽的姑娘,你现在属于我,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你,我想。你属于我,整个巴黎都属于我,而我则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或者到西尔维娅·比奇开设在奥德翁路12号上的莎士比亚公司借书部,取下两卷本的《猎人笔记》或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在冬天的那只大火炉旁边看看书,还有漂亮的西尔维娅,“西尔维娅有一张生气勃勃、棱角分明的脸,一双褐色眼睛像小动物般灵活,像少女般欢欣。”如果不在咖啡馆或书店,可以沿着塞纳河行走,在那里发现码头上的旧书摊,或者结识几个钓鱼人,和他们聊聊天,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自己买到的那些旧书;即使一个人在房间里,海明威也会在快写完小说或者天快黑时,喝上一杯从山区带来的樱桃酒,当做完一天的工作,会把笔记本放进抽屉,然后把吃剩的橘子放进衣兜,如果写作时感到难以下笔,“我便往火焰边缘挤捏橘子皮,观察汁水怎样使火焰毕剥作响,蹿出蓝幽幽的焰花。”
| 编号:C55·2240504·2113 |
当然,巴黎对于海明威来说,更重要的是遇见一些人,发生一些事,因为只有人才可能给虚假的春天制造某种愉快。和妻子一起去拜访斯泰因小姐,斯泰因和海明威则说起写作的事,她说不喜欢单调乏味的修改文字的苦差事,她喜欢舍伍德·安德森并不是因为他是作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男人,“兴致勃勃地说他那双大眼睛长得漂亮、温暖,像是意大利人的,又说他和蔼可亲,很有魅力。”她憎恨将她的椅子整个儿坐得散架的埃兹拉·庞德……有一天下去,斯泰因竟教导海明威性方面的知识,她认为海明威在这方面所受的教育过于肤浅,尤其是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斯泰因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主要的问题是男同性恋者干的事儿太下流,令人作呕,完事后他们连自己都觉得恶心。于是便酗酒,吸毒,以缓解恶劣的心情,但是他们厌恶这样的行为,所以不断地更换伴侣,却无法真正快乐起来。”当然,在海明威从加拿大回来住在乡村圣母院路的时候,斯泰因说起了“迷惘的一代”这个话题,“你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你们喝酒喝到送命……”斯泰因显然不是讨厌这个名字和写作的态度,而是,“你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你们喝酒喝到送命……”
对于“迷惘的一代”,海明威从斯泰因的苛责中也受到了启发,夜晚走近丁香园咖啡馆的时候,他看到了灯光打在了拿破仑时代内伊元帅的铜像上,“他的军刀刺向前方,铜像上树影斑驳,他孤身一人,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而回想那段历史,“滑铁卢一役他败得多么惨呀”,当拿破仑带着科兰古乘坐马车仓皇逃窜时,内伊却率领后卫部队且战且退,这是不是属于内伊的“迷惘”?遭遇滑铁卢的他们是不是也是“迷惘的一代”?“我想到历来的一代代人都是被什么弄得迷失与迷惘的,过去如此,今后亦将如此”——但是这所谓的“迷惘的一代”并不应该是自我的消沉,就像斯泰因小姐所说,“喝酒喝到送命”,所以在回家之后,海明威见到了妻子、而子和那只叫“F.噗斯”的小猫,看到他们坐在生着火的壁炉前,他心里骂着,斯泰因那套关于“迷惘的一代”的说法和轻易贴上的标签“全部见鬼去吧”,迷惘不是迷失,而是一种苦战的态度。
海明威在丁香园咖啡馆的诗人聚会时,遇到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这个“活像只会走路、穿着讲究、上下倒置的大啤酒桶”,说因为海明威是个有前途的青年作家才和他喝酒,“实际上是把你视为一个同行。”画家朱尔·帕散也经常在咖啡馆喝酒,两位年轻的模特陪着他,在海明威看来,帕散就像百老汇的滑稽演员,他在咖啡馆故意寻醉,而在1930年举办第一个个展前夕,帕散突然自缢身亡,回想起来,海明威说:“对于那些玩世不恭的人来说,他们的种子上却覆盖着更加优质的土壤和更富营养的肥料。”美国诗人和记者埃文·希普曼1924年到巴黎,和海明威相识,也是在丁香园咖啡馆,海明威问起这个指甲很脏但脸上泛出笑容的诗人,“我一直在琢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儿,一个人文笔如此拙劣,拙劣得令人难以置信,怎么又能这样深深打动读者呢?”埃文的回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混蛋,他写混蛋和圣徒最最出色。他笔下的圣徒特别了不起。是我们自己水平低,无法重读他的作品。”海明威对埃兹·庞德充满敬意,说他是一个对朋友永远忠诚的人,而且与人为善具有基督教精神,甚至如圣徒一般的存在,“他自己的作品,在路子对头的时候,是那么的完美,犯错误时也是那么的真诚,对自己的谬误是那么的执着,对人又是那么的和善,以至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位圣徒般的人物。”海明威在埃兹拉的倡议下,为当时面临银行琐务的艾略特捐款,这是一个名为“才智之士”的组织,是庞德和富裕的美国女子纳塔莉·巴尼小姐共同创办的,后来,艾路特的《荒原》出版了,获得了《日晷》杂志的诗歌奖,还创办了《标准》刊物,“于是埃兹拉和我便再也无须为他操心了。”
在海明威对当时巴黎作家的回忆中,篇幅最长的是对司各特·菲兹杰拉德的回忆,他一开始就对菲兹杰拉德做了总体的评价:
他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正如蝴蝶翅膀上由彩色粉末构成的图案是浑然天成的一样。有一段时间他与蝴蝶一样对此毫无所知,也不清楚翅膀是何时遭到污损与涂抹的。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的受损以及它们的构成,他学会了思考,但是却再也飞不起来了,因为对于飞的爱好已不复存在,他只能回忆当初曾是如何轻松飞翔的了。
初次见面菲兹杰拉德就开始演讲,海明威和邓克·查普林等人一起喝酒、听他演讲,菲兹杰拉德不会奉承人,他认为海明威还不是了不起的作家,当时只有海明威的妻子和少数朋友持有这样的共识,但是菲兹杰拉德单刀直入,这并没有让海明威生气,“我很高兴司各特也得出了同样的让人愉快的结论”。后来他们成为了朋友,在巴黎一起交流、喝酒,也在那里创作。海明威回忆的一件事是他们离开巴黎去往里昂的一次旅行,在中途的时候去了一家旅馆,菲兹杰拉德说自己健康不佳,他担心的不是自己会得肺充血死掉,而是妻子姗尔达和女儿谁来照顾,甚至托付海明威以后让姗尔达少喝酒,为女儿找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那时躺在床上的菲兹杰拉德真的想要死了,“司各特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出气吸气,再配上他蜡白的脸色与完美俊俏的面容,简直就是一具十字军少年骑士的遗体了。”这种死亡的威胁也让海明威看清了人生的意义,“此时我开始厌烦起文学生涯来了,如果说此刻在过的就是文学生涯的话,而且我已经不惦念写作了,每当生命中的一天又给白白浪费掉,在这天行将结束时我总会感到死一般的寂寞。”菲兹杰拉德强烈要求海明威买温度计和阿司匹林,买来之后量体温服药,菲兹杰拉德却起奇迹般恢复了。
两个人算是“生死之交”了,但海明威对菲兹杰拉德的敬意全在于他的真实,“他有许多很好、很好的朋友,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所能拥有的还要多。可是我自愿参加进这个行列,不管我是否能对他有所帮助。”另外一件事则是菲兹杰拉德对妻子的爱恋,这在姗尔达那里是一种妒忌之心,“姗尔达妒忌司各特的创作活动,随着我们对他们进一步熟悉,我们便能看出,这种妒忌成了一种常规。”而菲兹杰拉德对姗尔达的爱则充满了醋意,他偷偷告诉海明威姗尔达如何爱上那个法国军官的,还说起她和女子结交,语气中透露着妒忌,甚至,“在蒙马特尔的那些酒会上,他生怕自己会喝醉,也担心她会喝得晕过去。他们一直把喝晕过去当作是自我防卫的一个高招。”后来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创作完成,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卖给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菲兹杰拉德一家的生活开始变得井然有序,而有一次姗尔达悄悄和海明威分享了一个秘密,“欧内斯特,你不认为埃尔·乔生比耶稣更加伟大吗?”埃尔·乔生是一位俄裔美国歌星,常抹黑了脸唱黑人歌曲,品位不高,但是姗尔达将他看做是比耶稣更伟大的人,海明威也许到死都不会将这个秘密告诉菲兹杰拉德,“这只不过是姗尔达让我共享的一个秘密,就像一头兀鹰会与一个人共享什么东西那样。但鹰类是不愿分食的。司各特再也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一直到他明白姗尔达的确是疯了。”
最有趣的还是关于“一个尺码大小的问题”,在姗尔达后来精神不佳甚至“崩溃”的时候,菲兹杰拉德邀请海明威去米肖餐厅共进午餐,他很郑重其事地说有一个“比世界上任何事情的意义都要重大”的问题要问海明威,而且要海明威“如实回答”,菲兹杰拉德喝了葡萄酒,他对海明威说:“你知道的,除了跟姗尔达,我从未跟任何别的女人睡过。”海明威如实回答:“不,我不知道。”菲兹杰拉德继续说:“珊尔达说,单凭我的身材,就不能让任何一个女人感到快乐,这就是让她心烦的根本原因。她说这是一个尺码大小的问题。自从她说了这样的话,我的感觉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必须弄弄清楚。”当时的海明威“如实回答”说:“你完全正常,你没有问题。你一点儿毛病都没有。”而且海明威还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说:“你从上面往下看自己,自然就像是缩短了。那么就去卢浮宫看看人体雕像,回来再对着镜子从侧面瞧瞧自己。”但是菲兹杰拉德还是不放心,他们甚至后来真的去看了雕像,看了之后菲兹杰拉德对于尺码大小还是耿耿于怀,于是海明威劝解说:“姗尔达疯了。你一点毛病也没有。对自己要有信心,做那个姑娘希望要做的事好了。姗尔达是存心想毁掉你。”
这更像是一个段子,但是无论发生在菲兹杰拉德身上还是和海明威的回忆有关,都显得真实,真实的背后也是他们友情的见证,更是巴黎那段时光的“亮丽”色彩。但是,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巴黎永远与你同在》中,亮丽还是变得有些黯淡。海明威回忆了当时从加拿大去往巴黎的冬季之旅,那时儿子邦比出生之后,整个家庭变成了三口之家,生存的压力更大了。他们在奥地利的施伦斯进行了停留,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海明威不断创作和修改自己的《太阳照常升起》,在此期间,他和镇上的人打门球,目睹了一场雪崩,自己蓄起了胡子……后来终于离开了施伦斯,海明威去纽约安排了出版社,然后回到了巴黎,看见了在火车站迎接自己的妻子哈德莉和胖嘟嘟的邦比,这是一种原本幸福的相聚,在海明威的笔下,哈德莉依旧那么美,“她在微笑,阳光照在她那被雪与阳光晒黑的脸上,体态很美,她的头发在阳光下变成金红色,一个冬天使她的头发长了不少,不怎么整齐,但是很好看”,而海明威对她的爱也没有改变,“我爱她,我不爱任何别的人,我们单独度过了一段美好又奇妙的时光。”
在巴黎的岁月中,哈德莉一直是海明威坚强的后盾,他们一起去见朋友,一起在塞纳河畔散步,一起讨论写作,甚至很多时候哈德莉为海明威誊写著作,但是施伦斯之行却改变了这一切,海明威说他“不爱任何别的人”,但是,“等到暮春时节我们离开山区回到巴黎,另外的那段情缘重又开始了。”出现在海明威生活中的是“未婚的年轻女子”,“那就是说,有个未婚的年轻女子,以另一位已婚年轻女子新近结交的闺蜜的身份,搬过来与这对夫妻一起居住,接着便人不知鬼不觉地、天真无邪地,却是毫不留情地思谋着把别人的丈夫夺走。”他不仅把自己对婚姻的背叛说成是这个年轻女子的一个阴谋,而且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倒霉”,“这位丈夫忙完工作有两位迷人的女子围在身边。其中之一是新鲜、奇异的,倘若他命中注定活该倒霉,他便会两个都爱。”离开巴黎又回到巴黎,另一段情缘开始了:1927年1月,海明威与哈德莉离婚,四个月后他与这位年轻女子,即时尚杂志女编辑波琳·法伊弗结婚。
海明威的第一次离婚和第二段婚姻,对于海明威来说也是人生的一个插曲,但是这依然是有着“流动的盛宴”的巴黎,依然是充满了亮丽色泽的巴黎,即使犯了错,依然构筑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巴黎永远不会有结束,每一个在此生活过的人都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记忆。”记忆中是橘子汁水在火炉中蹿出蓝幽幽的焰花,是清晨的羊倌将新鲜的羊奶挤进罐子,是虚假的春天那一瞬间的感动,记忆中更是斯泰因小姐谈起的性知识,西尔维娅推荐可以告别饥饿的饭店,菲兹杰拉德关于尺码的担心,以及“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的美丽姑娘,“这里所写的,仅仅是早年间我们非常贫穷又是极其快乐的那个阶段巴黎的样子。”即使有着一丝的黯淡,也是人生中“流动的盛宴”,而海明威之所以在1960年完成撰写和出版,也许他想以这最亮丽的回忆虚构青春和力量,“虽然巴黎永远是巴黎,当巴黎在起变化的时候,你自己也在变。”——一年之后,海明威把猎枪朝向了自己,结束了62岁的生命。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