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28《吕美特谈吕美特》:用电影与世界对话

南希·博斯基对西德尼·吕美特进行“一次永不停息的采访”发生在2008年,在吕美特面对镜头讲述自己和电影的故事三年后,即2011年83岁的吕美特辞世,而这部纪录片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次亮相则是2015年。从2008年拍摄到2015年首映,期间经历的七年时间里,吕美特的逝世夹在中间,而当纪录片变成完成并公映的电影,当吕美特以活着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影像就像是对生命的另一次激活?是不是记忆被保留之后可以永远延长?
这或者也是吕美特走上电影之路最积极的意义。南希·博斯基的纪录片并不出彩,甚至中规中矩到只让吕美特坐在固定位置,甚至保持固定姿势谈着和自己有关的一切,只是在吕美特谈到某一次经历、某一个观点、某一种感悟的时候,插入了吕美特电影的片段,这些经典片段也成为了吕美特的一部分。所以,“吕美特谈吕美特”就是和自我的对话,而自我对话在回顾性讲述的同时,也通过人生观的改变深入到了电影的创作观,阐释了作品核心的精神和伦理教训,但是南希·博斯基捕捉到吕美特特殊的一点,就是吕美特在遇见了一次暴力事件后,整个对世界的看法似乎就被颠覆了,吕美特通过电影创作质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面对世界,我能做什么?
吕美特在纪录片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曾经在加尔各答火车站看到的一幕:一个女孩在月台上,火车车厢外经过了一群美国兵,他们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女子进行了侵犯:把她拖进了车厢,“一个接着一个”强奸了她,然后扔给她一些钱,“我当时非常震惊”,震惊首先是对社会道德沦丧现实的一种无奈,它成为了之后吕美特电影关注的一个主题,“我不是在做道德教化,我只是拍那件事和那群人……”而在电影最后,吕美特再次说到了这个让人震惊的事件,美国士兵做完之后将她放回到了月台,仿佛也没有发生过,但是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吕美特开始反思,“他们如此残忍,但当时我什么也做不了,俄狄浦斯王剜出自己眼球那一幕,我真希望自己就在旁边,那才叫绝望……”在他看来,什么也做不了是最大的无力感,他只能在和内心进行对话之后陷入“自我憎恨”之中,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在吕美特看来,所谓惩恶扬善的英雄只存在于“热天午后”这样的电影中,也就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要成为英雄,“你得做好牺牲的准备,但是我没有……”当现实中的自己不能出手相救成为英雄,吕美特转向了艺术化的电影,但是电影对他来说绝不是一种虚饰的产物,而是和世界进行对话的另一种可能,“我的电影总有一个基础性的思考:什么是公平?”
| 导演: 南希·博斯基 |
实际上,纪录片中后面的吕美特回答了前面的吕美特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公平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个下意识的选择,没有刻意为之。”电影中的道德观就是这样,它就是对现实最真实的投影,也是用电影和世界对话的永恒主题。道德不是刻意为之的选择,电影对于吕美特来说也一样。吕美特的父亲巴鲁克·吕美特就是一个演员,也是他将吕美特带到了百老汇,让他走向了舞台,从舞台演出到电视剧导演,再到电影导演,吕美特就这样沿着“没有刻意为之”的路前进,所以他对于家庭有着特殊的感情,“自发的戏剧元素就是家庭,经久不衰的戏剧就是家庭。”《长夜漫漫路迢迢》《丹尼尔》《不设限通缉》《在魔鬼知道你死之前》等电影都呈现出父与子独特和复杂的关系,这里既有对话也有隔阂,既有矛盾也有爱。但是家庭作为吕美特演艺生涯的起点,自己电影阐释的主题,并不应该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甚至吕美特拒绝将家庭关系变成自己作品的专有特征,之所以这样,吕美特认为恰恰就在于家庭故事只是自发性的戏剧动力源泉。
很明显,家庭是起点也是吕美特需要突破的场域,于是从家庭走向了城市,他有着独特的“纽约情结”,“纽约能够承载你想创造的任何清晰或戏剧化表达,所以我离开纽约总会流鼻血……”《新绿野仙踪》中的一个场景就是在纽约世贸大厦拍摄的,这也是吕美特“纽约情结”的一次展示,但是当9·11恐怖事件发生,世贸大厦成为废墟,无辜者死去,“我的心都碎了,总觉得那时我的地盘。”但是,纽约并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纽约情结也并非只在生理上、精神上和吕美特息息相关,吕美特对于纽约有着自己特殊的解读,“我不怕封闭的物理区域,反而寻找这种场景来拍摄,纽约看起来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但其实是封闭世界。”他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十二怒汉》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演绎,而很多关于犯罪题材的电影也局限在法庭这一封闭世界,为什么封闭世界对吕美特来说是具有诱惑力?他用了一个比喻,“我不认为当人面对高山时比面对墙壁时表情会更有趣味,人的脸本身就是有趣的,而山始终保持不变。”高山看起来是开放的,其实它的不变性恰恰表明它是封闭的,而即使面对墙壁,只要人的表情是有趣的或者无奈的,那么就代表着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开放。封闭即开放,吕美特的这个美学观其实深刻地阐述了戏剧性,只有人脸表现出的丰富性才是戏剧性的真正表现,而封闭空间更能在压抑、冲突和突围中制造不同的表情,从而创造更多的戏剧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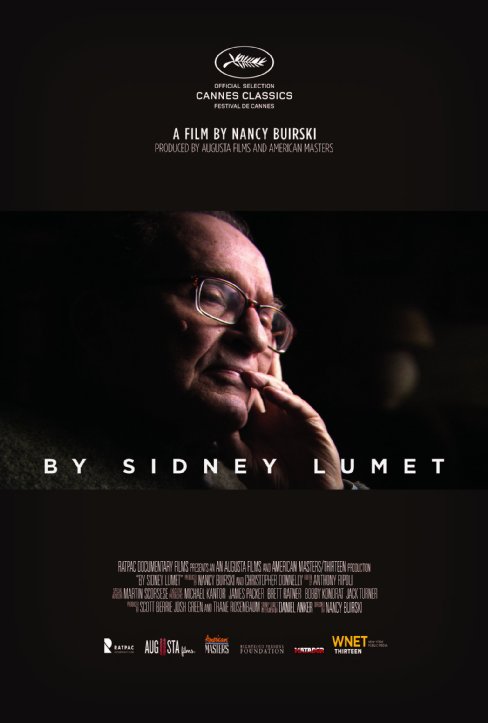
《吕美特谈吕美特》电影海报
从家到城市,从高山到人脸的表情,这其实就是吕美特对于戏剧化表达的转变思想,而他的电影就是在阐述人与本质作斗争的社会困境,他说《典当商》表现的是人必须经历痛苦才能“起死回生”的主题,《丹尼尔》是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部电影,“它是一种对不公的本能反应,时至今日仍是我的一部分。”《电视台风云》中所有人都没有了创造性,只有唯一的一个“疯子”,而《山丘战魂》所表达的主题是:“不仅仅是军队,世上一切都在合谋,摧毁人的个性。”当然他的经典电影《十二怒汉》,第一个说出“无罪”的陪审团成员就是扭转从众心理的一个叛逆者,“所以我喜欢反叛人物,我被质疑者所吸引。”吕美特认为,只有不屈服于潜规则,才是人类进步和戏剧效果的根本来源,或者说,潜规则就是那个封闭的世界,只有面对潜规则而敢于质疑、反抗和斗争的时候,那个人才会涌现出丰富的表情,才能进入到真正的戏剧世界中。
但是吕美特的反叛和质疑并不是彻底的解构,而是要归于那次震惊的经历所带来的转变,也就是归于那个基础性的问题:什么是公平?公平是道德观,是司法制度,最终一定是人生的终极追求,在吕美特的电影中,关于公平、关于正义的题材比比皆是,但是他认为,真正的电影并不是要对此寻找一个确切的答案,“当作品足够出色,道德观自然显现。”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不刻意追求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吕美特有些幽默地说:“《十二怒汉》改写了律法,但我是为了改写律法而拍的这部电影吗?不,我拍这部电影只是为了得到下一份工作。”其实自然而然的拍电影就是工作,就是生活,“我到最后发现,我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但我不是什么天之骄子,我只是个幸运的人,有我喜欢的工作,并有幸投身其中。”这就是吕美特真正和世界对话的方式,从一开始的无能为力到自我憎恨,再到后来对于公平的追问,最后却是把一切的发生都当做生活本身。或者,在50年间拍摄了44部电影的吕美特,面对46次奥斯卡提名、6次奥斯卡金像奖的荣耀却从未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现实,他也许也没有感到不公平,因为电影永在,影像永存,在镜头前的吕美特也永远活着,当南希·博斯基在纪录片的最后插入了《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火车鸣笛启程的镜头,也是对吕美特和他电影的一次致敬:后来者会沿着这条路再次出发。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