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28《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回忆与逸事》:时间已经穿帮

“五至七时”是1962年电影里的时间,从下午5点至6点半在物理时间里发生;“五至七时”是2018年观影的时间,从下午5点观看,76分钟之后关机,到第二天继续,也在物理时间里发生——在电影叙事和观影行为无限趋向于“同一时间”的时候,阿涅斯·瓦尔达的“时间影像”实验也完成了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的同一,但是,当2005年以“回忆与逸事”的方式再次走进“五至七时”的时候,电影叙事时间是不是还是开放的?进入和退出是不是还会呈现同一性?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一部1962年上映的电影,在返回现实的过程中,当然指向了另一种时间。1961年6月21日电影正是开机,这是地球上白天最长的一天,阿涅斯·瓦尔达选择在这一天开机并不是一种时间仪式,或者并不是对那个日子的纪念,仅仅是因为资金问题。原本电影在1961年春开机,资金问题搁置了电影的拍摄计划,在一个季节之后的6月21日,一切终于到位。但是6月21日原本是星期三,阿涅斯·瓦尔达为了符合剧情需要,将这一天设置成了“星期四”。这似乎是对现实时间的修改,而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说,电影制造的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同一性也只是一个影像上的游戏,现实是现实,电影是电影,而阿涅斯·瓦尔达显然也人为地区别了这种看似同一的时间标签:占卜时的塔罗牌是彩色的,而整部电影的其余部分都是黑白的——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当时拍草地时用了绿色滤镜,看上去草坪就具有了柔和虚幻的视觉效果,而“五至七时”本身的叙事时间也并非是电影中的两个小时,它只有一个半小时。
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本身就存在着某种隔阂,阿涅斯·瓦尔达从巴尔·格里恩描绘骷髅嘲弄美人的画作《死亡与少女》中得到灵感,“尤其像由巴尔东·格里恩画制的漂亮女人,死神耳语着她不想听到的事情,或是扯头发。这是画家作品的常见主题,对我来说是个灵感,我讲述的另一个展现这个故事的方式。”巴尔东·格里恩的绘画中,死神带走了少女,这并不为了带走她的生命,而是为了让她成为他永远的伴侣。而阿涅斯·瓦尔达的讲述则是在主观的恐惧中,走向与他人生命暗合的客观化存在。首先需要的是凸显客观时间,在拍摄电影时,为了和物理时间相吻合,剧组做了大量的工作,先是通过地图考察拍摄的地点,经过计算控制在“五至七时”的电影时间里,而且在拍摄现场,时间也被明显标记出来:街上的钟,房间里的钟,克莱奥身边的钟。客观时间在电影的叙事中,它就是现实一种,而主观时间,据阿涅斯·瓦尔达回忆,“45分钟的时候有了重要的转折”,那就是克莱奥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之后,开始了改变,这种改变是通过对别人的观察来定义自己,帽子店、咖啡店、绘画室,都是她观察别人从而做出改变的场所,而这便让她从恐惧走向了自信,主观时间得以完成便是最后遇见了士兵,“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也成为了最后对主观和客观之间隔阂的消除。
这是阿涅斯·瓦尔达在1961年设置的时间线索,而当四十年过去,当阿涅斯·瓦尔达和剧组人员再次造访拍摄地,再次进入“回忆与逸事”的时间段落,一切也并非留存在1961年。孟苏利公园的观星台已经拆掉,只留下了小山坡,克莱奥去过的帽子店也早已经不在了,而意大利广场的那些泡桐有的当然已经长大,而更多的则被砍掉了,每年都有新栽种的泡桐。这是一种物的变化,而40年前的那些人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发生了改变:人当然已经变老了,主角科琳娜·马尔尚和安托万·布尔塞耶从以前的风华正茂变成了人生迟暮,甚至在说起之后参加戛纳电影节,安托万已经找不到去过的记忆,科琳娜拿出当时的照片,安托万才发现自己失忆了,照片中科琳娜和安托万站在中央,旁边站着的是阿涅斯·瓦尔达——照片刻写着那时的时间,只有在照片这种定格的存在里,时间才不会老去。
| 导演: 阿涅斯·瓦尔达 |
“剧组就像一艘暴风雨中的船,大家等待风平浪静,各自上岸后约定保持联系。”安托万这样说,但其实在拍完电影之后,直到现在故地重游,安托万和科琳娜在漫长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时间的另一种暗示: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当记忆开始模糊,还能不能找到“五至七时”这个时间的意义。他们进入到回忆之中,回忆克莱奥的那串项链是瓦尔达的,回忆为了需要买下了那枚别致的蟾蜍戒指,回忆桃乐茜拍摄当天才拿到驾照,回忆科琳娜一周减肥掉了7斤,回忆多萝特走在艺术街的楼梯上……所有的回忆当然构筑了电影拍摄的客观时间,它们就是时间本身。但是这个时间只存在于四十年前,当这个客观时间过去,一切似乎都变成了时间的另一种游戏,而这也成为在“回忆与逸事”中最丰满、最哲学的注解。
阿涅斯·瓦尔达回忆说,在1962年电影上映之后,她收到了著名影评家乔治·萨杜尔的一封信,乔治告诉她看了电影之后整整哭了七天,因为电影里表达的对死亡的不安和悲伤就是他现实中的写照:1938年6月,他的妻子在萨勒贝特里埃医院去世,那时的妻子和电影中的克莱奥同岁,而且他也是在那里等待医生时等来了这个噩耗,“对我而言,那个花园就是死亡的标志,悲剧的最高点。”1961年的电影和1938年的现实不谋而合,这是不是死亡本身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是不是在时间中变成了一种重现?当阿涅斯·瓦尔达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重演了“悲剧最高点”的那一幕,“回忆与逸事”变得沉重,“在没有认识到之前,我虚拟了一个强大到足以毁灭其他人生活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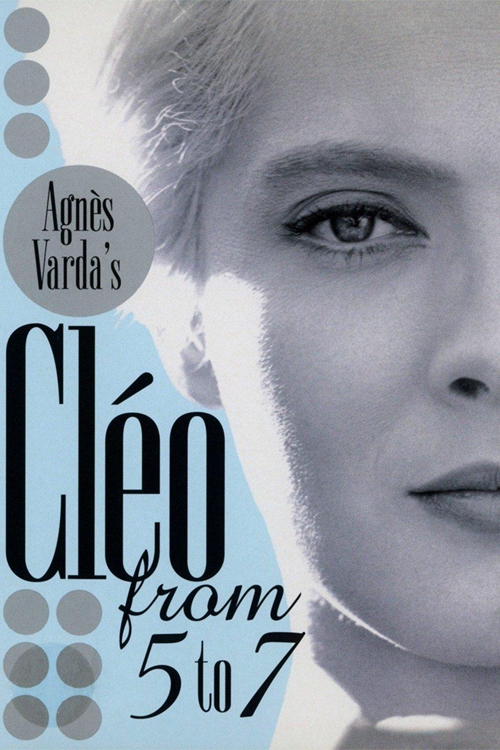
《易迪莎,熊及其他》电影海报
虚拟的场景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看似是时间的一种魔术,实际上是制造了时间的唯一性,因为一切都在发生,一切都无法停止,这种不可复制的时间存在在这部电影最后一个场景的拍摄中更得到了诠释。克莱奥和相遇的士兵一起在路上行走,第一遍完成之后,阿涅斯·瓦尔达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些模糊和黑暗的东西存在,原来这是为拍摄准备的轨道,于是她要求重新拍摄,但是,“两次或者三次都行,对我而言,没用。”因为“他们不在那里”,最初的感觉,演员的情绪,以及镜头的构图,似乎都无法在重拍中再现,于是阿涅斯·瓦尔达只好将第一次那个穿帮的镜头剪进了电影中,而这也成为了阿涅斯·瓦尔达一个永远的遗憾,“我不应该告诉你们这个故事,但那教会了我一些事情,一个真正的教训。”电影需要的是捕捉神奇的瞬间,于是在四十年后,她依旧在感叹:“重建和重塑是很难的。”
无法重塑,无法重拍,无法重建,这便是关于时间唯一性的注解,1961年的电影不是1938年的现实,1961年的电影也无法在四十年后重现,“五至七时”的时间同一性更像是一个影像的实验,它无法完整地回来,它只在封闭的叙事中,即使“回忆与逸事”想要进入其中,也可能是一些碎片,宛如模糊和黑暗的轨道,它最后变成了一种“穿帮”的时间。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