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15《亲和力》:一种关系优于另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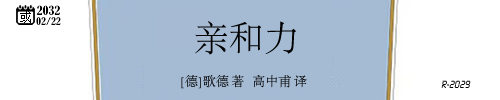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拉开,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推回去。出现了精彩和有价值的,可彼此却可怜地连在一起。任何地方都可以看作是开头,任何地方也可以当作是结束。
——《第二部·第九章》
奥狄莉的日记,当一个在寄宿学校忧郁的女孩回到庄园,当她在庄园里遇见了爱德华发现了爱情的力量,当已婚的爱德华选择了离开,对于奥狄莉来说,这是一种因为爱人不在身边而“没有爱情的生活”,她将其比喻为 "Comedie a tiroir”,一种“恶劣的抽屉剧”,生活就像那个被拉出来又推进去的抽屉一样,没有真正的归宿感,她也只有在完全属于自己的日记中倾吐心声,发出感慨。
奥狄莉这样的生活无疑就是歌德所说的“匮乏”,“匮乏”可以看作是小说情绪走向另一个拐点的标志,他在《年志》中透露了这种想法,“《潘多拉》和《亲和力》一样,表达了匮乏的痛苦之情。”这种匮乏就是“一种没有爱情的生活,一种爱人不在身边的生活”,它带给奥狄莉的就是痛苦之情,“没有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会看不到一道深深的激情的伤口,这伤口害怕愈合,这颗心畏惧康复。”面对这样的匮乏和痛苦,歌德无疑让“日记”成为奥狄莉疗伤的庇护所,他在小说中甚至以全能的视角独立于故事,引出了奥狄莉写日记的的习惯,“因此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透露一些奥狄莉记在她的日记里的事情吧。”并且指出了日记对奥狄莉来说的意义,“日记中的见解、观察,选择的格言及其他言辞,完全是写日记者特有的,并且对她是有意义的。”歌德还给了奥狄莉日记一个“比喻”,那就是“红线”,“在奥狄莉的日记中贯穿着一条爱慕和忠诚的红线,它联结着一切,标志出整体。”
日记对奥狄莉的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对歌德阐述匮乏带来的痛苦之情也具有关键意义,但是,日记里的这句话除了奥狄莉感慨生活的无助之外,更在于指出了一种关系学:爱情是她和爱德华之间的爱情,它本是一种拥有,但是当世俗社会的人们像抽屉剧一样对待两个人的爱情,即使精彩和有价值的东西,也以“可怜地连在一起”的方式发生,开始是结束,结束可能也是开始。爱情发生是两个人关系发生的开始,爱情匮乏是两个人关系的结束,却是抽屉剧里关系的开始,关系带来了拥有,也带来了匮乏,关系是幸福的,也是可怜的,而正是从奥狄莉关于关系的日记中,歌德阐述了“亲和力”的真正主题:当世界的人和自然科学一样发生了关系,形成了“亲和力”,它到底是制造了幸福和快乐,还是变成了匮乏和痛苦?它可以用描写爱慕和忠诚的日记得到安慰,还是像抽屉剧一样走向可怜?
歌德在小说第一部第四章里就非常全面地阐述了“亲和力”,但是在“亲和力”被引入之前,故事所表现的关系学就已经发生了:爱德华和夏洛蒂是两个相爱的人,但是由于家庭对于财富贪得无厌,爱德华和一个有钱女人结婚,而夏洛蒂也嫁给了一个富裕的男人,可以说他们的爱情就在被财富“劫持”中走向了解体,他们的婚姻取代了爱情,这就是一种匮乏。后来爱德华的妻子死去,留给了爱德华一笔巨大的财产,而夏洛蒂也恢复了自由,于是他们又在一起了,起初爱德华想要和夏洛蒂结婚,夏洛蒂是犹豫的,她认为自己作为妻子老了一些,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于是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又走在了一起,而且进入到了婚姻之中。从前一种婚姻对于爱情的破坏导致的匮乏,到后一种婚姻让他们重新走在一起结束了匮乏,不同的婚姻注解了不同的意义,而关键并不是婚姻本身治愈了匮乏带来的痛苦,而是两个人存在的爱情。
爱情经历了从关系的解体到关系的复合,对于他们来说显得更为珍贵,“我照管内务,你负责外部和全局。我的布置处处是迎合你的,也仅是为你一个人而生活;至少有一段时间让我们试试看,按这种方式生活,我们能持续多久。”住在乡间的庄园里,他们不被打扰,他们享受着平静,也由此获得了幸福。但是这种生活的乐趣随着爱德华最要好的朋友上尉奥托的到来而发生变化,于是对于“亲和力”的讨论开始了,这也意味着歌德要将这个故事带入关于匮乏、痛苦和断舍的另一层关系里。两个人无扰、快乐,这是理想的生活,但其实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动态的关系发生,它处在一种静止状态里,而当这种静止状态被打破,关系实现了重组,它带来的却是破坏,“我的感情与此事相悖,我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当爱德华接到上尉的信说起自己的朋友将要来这里,夏洛蒂预感到了不详,“我看到过一些朋友、姐妹、恋人、夫妻,他们的关系由于一个新来的人无意或有意地插足而完全改观,他们的位置完全颠倒了。”
夏洛蒂的想法的确只是预感,但是和奥托有关的关系学由此打开,的确是一种必然,按照爱德华的说法,上尉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他遭受了挫折,遇到了障碍,“把两只手插进怀里什么也不干,或者继续攻读,再去学习本事,他不需要他已经充分占有的东西了——够了,亲爱的,这是一种可悲的处境,他在自己的孤独中两倍、三倍地感觉到这种境况的痛苦。”上尉的无所事事,上尉的怀才不遇,造成了他的孤独和痛苦,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他同样遭遇了匮乏和痛苦,而听到爱德华对上尉的介绍,夏洛蒂也说起了在寄宿学校的外甥女奥狄莉,“这个可爱的孩子在寄宿学校里情绪极为抑郁,令我十分忧虑。”和夏洛蒂的女儿绿茜安被老师和同学喜欢不同,奥狄莉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她也和上尉一样在社会关系中面对着匮乏、经历了痛苦。所以当爱德华提出让上尉来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之后,夏洛蒂提到奥狄莉其实也意味着要让奥狄莉也回到庄园,为的是让他们适应新的生活,建立新的关系。
于是在上尉到来之后,爱德华、夏洛蒂和他展开了关于亲和力的对话。1775年瑞典化学家托本·柏格曼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1782年德国化学家海因·塔巴把它翻译过来,用“亲和力”来表述其标题,夏洛蒂首先问上尉关于“亲和性”的意义,上尉解释说:“那些相遇时彼此很快发生反应并相互发生影响的,我们称之为亲和。”他尤其提到了亲和发生的条件,举例说到了酸和碱,正是因为它们彼此对立,所以才会相互寻求、相互捕捉,为的是改变自身形态从而构成一种新的物质,“我们只需想一想石灰吧,它对所有的酸都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好感和一种强烈的结合欲!”上尉说到的亲和性局限在自然物质上,在三个人的讨论中,亲和性以及亲和力就变成了人与人的关系,“正如每一种事物自身都有着一种联系力,它对其他事物来说,也有着一种关系。”夏洛蒂这样理解,“正如这一切通过道德和法律可以结合在一起一样,在我们的化学世界里也有触媒,它把互相排斥的结合在一起。”爱德华则这样解读,也就是说,亲和性就是一种关系学,和道德有关,和法律有关,更与爱情有关,它是对立关系中的重构,是在排斥关系中的结合,由此形成新的关系,但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潜在的解读:当重构和结合发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分离也同时发生?
| 编号:C37·2240921·2180 |
“当亲和性发生分离的作用时,那才是颇为有趣的呢。”爱德华这样说,上尉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它确实让人看到了,一种关系优于另一种,一种关系被另一种取而代之。”而早就犹豫了不详预感的夏洛蒂对此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遗憾的是这类情况我太熟悉了,一种密切的、看来是不可分的两个人的结合,由于一个第三者的偶然介入就遭到破坏,先前结合得很好的一个被驱逐到没有着落的广袤之中。”所以亲和性并不只是意味着重组带来新的变化,结合产生新的关系,更意味着分离和破坏,而这种分离和破坏不正是匮乏?当三个人讨论了亲和力之后,他们想到了将关系维持在相对稳定状态的办法,那就是在让第三者介入之后,也必须让第四者也加入其中,“使每一个都不落空。”这一办法得到了上尉的响应,“在这种离异和捕捉,逃逸和追求上,人们确实可以看到一种更高一级的目的,人们相信这样的物质有着一种意志和选择的本性,认为亲和力这个新造的词儿是完全有道理的。”
在第三者之外让第四者加入,这更像是一个关于亲和力的游戏,所以奥狄莉从寄宿学校被接出来加入其中,形成了离异和捕捉、逃逸和追求的“十字架”,开始了关系学的化学反应。四个人在这里也不受打扰,他们或者在一起聚会聊天,或者在一起设计庐舍,在渐渐交往中,亲和力开始发生作用,夏洛蒂和上尉在进一步了解之后,在修建休息场所的计划实施中开始有了好感,而奥狄莉和爱德华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爱德华有了对奥狄莉“暗暗的、友好的爱慕之情”,奥狄莉的体贴、殷勤和乐于助人让爱德华体会到了某种爱,“在我们这四位朋友之间产生了一种极为愉快的相互爱慕之情。”亲和力不可避免地从夏洛蒂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尤其是当那次爱德华和奥狄莉一起去山间,奥狄莉佩戴着的那个项链,由于珍藏着父亲的相片,总是发出声音,在爱德华想要更接近奥狄莉的时候,它总是发出撞击的声音,像是对爱德华接近的一种警告,于是爱德华建议奥狄莉将项链取下来,“某种预料不到的撞击,一种跌落,一种接触,都会使您受到伤害、损伤呢。这种可能性使我惊恐不安。”奥狄莉也爽快地答应了,那一刻爱德华感觉心头的石头落了地,“仿佛隔在他与奥狄莉之间的一堵墙已经坍塌。”
亲和力快速发生着反应,直到当爱德华吹奏笛子时奥狄莉主动要为他伴奏,“他们惊奇的是,奥狄莉私下竟然如此完美地学会了这首乐曲,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她善于配合爱德华的演奏方式。”伴奏产生和谐,这正是关系发生改变的标志,这个标志更解构性的意义就在于,曾经为爱德华伴奏的是夏洛蒂,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奥狄莉,在爱德华和奥狄莉合奏产生的重构和结合的同时,夏洛蒂无疑变成了分离的一方。除了笛子伴奏之外,爱德华的那只烧制的酒杯上也刻着代表自己和奥狄莉名字首字母的E和O,在那一晚爱德华去找妻子夏洛蒂,竟然把夏洛蒂和奥狄莉混淆起来,在朦胧的微光里,他认为自己怀中抱的就是奥狄莉,“真够奇怪了,飘忽得使不在身边的人和在身边的人混淆不清,令人兴奋和狂喜的混淆啊。”当他得知奥狄莉锁在屋子里为自己抄写东西,他感到快乐,他觉得她是在为自己做事,也终于在那一刻他喊出了“奥狄莉,你爱我”的喊声,两个人也拥抱在一起。
亲和力无疑发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爱德华爱上了奥狄莉,当然奥狄莉也爱上了爱德华,之所以爱德华并不在意自己的背叛,因为他认为夏洛蒂和上尉之间也存在着暧昧关系,甚至他已经有了如何将两个人离婚的事体面地说出来的打算。他们彼此都经历了一段婚姻,之后爱情让他们又走在了一起,而现在在亲和力的作用下他们又寻找到了爱情,如此强烈,如此富有激情,是不是就可以通过离婚的方式再次拥抱爱情?在这里,歌德其实将这个问题变成了道德选择,爱德华和夏洛蒂之间是爱,而现在他和奥狄莉之间也是爱,两种爱都同样面对婚姻问题,甚至后一种爱的发生是在否定第一种爱,否定第一种婚姻,亲和力让关系发生改变,也让爱发生改变,那么面对婚姻困局,该如何在匮乏制造的痛苦中寻找到一种出路?在写作《亲和力》之前,58岁的歌德遇到了18岁的美丽少女米娜,不可遏制的爱慕之情左右了歌德,但是和《少年维特之烦恼》时期的歌德不同,他面对这份炽热的感情,选择了理性的阻止,这就是歌德所说的断念,而之所以要选择断念,在于歌德来说,是另一种更可以达到自由的选择——断念就是对道德的考量,就是对婚姻制度的批判。
爱德华和夏洛蒂可以说都是第一次婚姻的牺牲品,对于婚姻带来的匮乏,他们都有发言权,而来到庄园的客人男爵夫人和伯爵,他们不是夫妻,但是在短暂的时光中寻找爱情的乐趣,当然,他们对婚姻也进行了抨击,“确实是一种令人憎恶的婚姻,并且,可惜的是,请原谅我用一个更生动的词来表达,是一种愚蠢的婚姻。这种婚姻毁灭了最温柔的关系,而仅仅只是为了粗俗的安全感,这至少是为一方带来了某些好处。”但是面对婚姻,他们选择的是逃避,甚至是苟且。而不断调整人们关系的米德勒则把婚姻关系看做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婚姻是所有文明的肇始和顶峰。它使粗鲁变得温顺,最有教养的人没有比婚姻更好的机会,来表示他的温顺了。它是不可解除的,因为它带来那么多的幸福,使一切个别的不幸都变得微不足道。”当爱德华面对和夏洛蒂的婚姻,当面对和奥狄莉的爱情,亲和力带来的结合和分离终于使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离开——他的离开是为了让奥狄莉不再被送到寄宿学校去,他的离开是为了让自己的爱人能平安,他的离开更是为了让自己不再爱情中变得自私,“一出府邸,一出庭院,把她交给陌生人,那她就属于我的了,我就会把她占有。”所以他断念,所以他消失,甚至奔赴了战场,在爱德华看来,断念不是对爱情的消灭,而是激发强烈的想念,“我现在一直在思念她,一直在她心旁。我还有一种无比珍贵的长处,那就是我能够幻想:奥狄莉现在在什么地方,她在哪儿走路,在哪儿站立,在哪儿休息。”
并不只是从爱变成了想念,爱德华想要从这里寻找新的关系,“爱德华渴求外在的危险,以取得与内在的危险的平衡。他渴望毁灭,因为对于他来说,存在已变得不堪忍受。”在某作用程度上这是对既存秩序的抗拒,也是对亲和力继续发挥作用的一种构建,“他想到,他不再存在了,并因此使他的情人、他的朋友幸福,他觉得这是一种慰藉。”爱德华选择了离开,他以断念的方式维持着亲和力,而奥狄莉则以日记寻找着慰藉,而这些日记更是成为歌德寻找自由的一种表达:奥狄莉在日记中写到了德行,“品德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在里面显现出来。”写到了艺术:“除了借助艺术,人们很难有把握避开世界;除了借助艺术,人们很难有把握把自己同世界联结起来。”写到了爱,“面对另一个人的伟大优点,除了爱之外别无补救的方法。”写到了自由,“一个不自由的人却自以为是自由的,那么,没有人比他更是奴隶了。”更是写到了人:“人的形象是最优秀的,也是唯一酷似神的形象。这我们不学也能知道。”
亲和力已经从两个人或四个人的爱情关系变成了人和人以及任何社会的关系问题,而在这里,对既存秩序的批判开始显露,自由所付出的悲剧性也慢慢展现。夏洛蒂的孩子出生了,但是他的脸部酷似上尉,而眼睛却越来越和奥狄莉难以区分。这种相似性似乎是一个悬案,这是夏洛蒂和上尉生下的孩子?但为什么又像奥狄莉呢?孩子的脸部像上尉,而且名字和上尉的一样,歌德似乎隐藏了夏洛蒂和上尉之间关系的可能,也就是说在爱德华和奥狄莉产生爱情的同时,亲和力也可能将夏洛蒂和上尉带入新的爱情,孩子无疑是一种暗示。而当孩子的眼睛像奥狄莉的时候,歌德在这里赋予了奥狄莉一种“母性”,这才是和爱德华之间在亲和力之下发生关系而达到了一种结合,它是对匮乏的弥补,是对爱的命名,不需要婚姻,不需要所谓的道德,她也成为了孩子的母亲。所以当奥狄莉失守让孩子掉落水中死去,悲伤的奥狄莉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袒露出自己的前胸,让孩子拥到她裸露出来的乳房上,“泪水从她的眼中不断地涌出,滴在僵畺礓硬中不断地涌出,滴在僵中不断地涌出,滴在僵硬的孩子上半身上,使得他仿佛有了温暖和生机。”这就是一种母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孩子死去,对于母亲来说意味着一种罪,这是匮乏带来真正的痛苦,于是她最后也走向了死亡。
“答应我,活下去!”这是奥狄莉在临死之前对回来的爱德华说的话,但是即使爱德华答应了她,他也在断念中早已经抵达了死亡,而死亡和死亡在一起也许是亲和力最后的结合:“我的整个追求只不过是模仿,一种谬误的努力罢了,我是多么不幸啊!对她来说是极乐,对我却是痛苦。为了这种极乐我被迫承受这种痛苦。我必须随她而去,就在这条路上随她而去。但是我的天性和我的诺言却把我阻拦。去模仿不可模仿的,这是一项可怕的任务。我的好友,我看得很清楚,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才能,即使是去殉难也如此。”世间无法在爱的亲和力中结合,道德只能导演抽屉剧,所以死亡才能让他们最后在一起,而这就是断念后的自由,就是殉难中的重构,它也成为了优于另一种关系的关系:
这两个相爱的人就这样并卧长眠。和平在他们墓穴的上空飘荡,欢愉的、与他们相似的天使画像从穹顶俯视着他们。倘若有朝一日他俩再度苏醒过来,那该是一个怎样欢乐的时刻啊。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