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0《夜与日》:作为牺牲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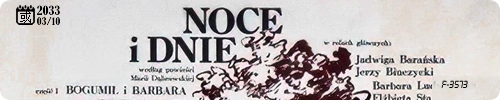
《夜与日》有三个版本,电视剧版本一共12集,总时长为632分钟;分成上下两集的电影,时长为245分钟;而观影的资源是电影版,却没有上下集之分,总时长却只有171分钟,而且这个版本还是波兰电影周的官方版本。当一部12集、632分钟的电视剧或者245分钟的电影被压缩到171分钟,它必然是一个“抽取”的过程,而抽取在另一个意义上不再是保持原貌的压缩,而是变成了一种“肢解”,甚至被完全打成了碎片。观影这个171分钟的版本,最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电影完全被剪辑得支离破碎,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个场景没有铺设,从一个段落到另一个段落完全缺少联系,从一种事件再到另一种事件也完全变成了切割:芭芭拉和博古米乌被介绍认识不久,他们就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为什么这是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变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从看到孩子芭芭拉想起了自己去世的儿子波特,但是除了回忆中一家三口的温馨场面和那块冰冷的墓碑,波特为什么夭折也完全没有交代,他的去世对于芭芭拉的婚姻带来怎样的影响也同时被忽略了;博古米乌和特蕾莎之间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后来竟然会被芭芭拉看成是一种暧昧?约阿希姆遗产中的6000卢布给了他们,约阿希姆和芭芭拉是怎样的家族关系?后来为什么打了水漂?
剪辑成这样一个面目全非的版本绝非是制作者的一种“创作”,内中的缘由不清,但是这样的形式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这部电影一种解读方式?“夜与日”的片名标明了一种从夜晚到白昼的过渡,但是“与”却并不是自然的连接,而是一种错开,关于爱情的错开,关于命运的错开,关于生活的错开,夜是黑夜的夜,日是白天的日,它们不是在不断翻过中构成了岁月和记忆,而是在各自的平面上成为一种隔绝,那么,“夜与日”必然呈现出一种断裂的关系,在这种断裂中,人生当然也再无法被弥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破碎的故事在形式意义上也就变成了“夜与日”的断裂,这反而变成了故事的一个隐喻。
的确,泽基·安特科扎克用“夜与日”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断裂感,这种断裂感首先就是个体的命运,在芭芭拉那里,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在博古米乌那里,则是永远无法拥有土地的土地情怀,他们都表现为一种错位式的缺失。芭芭拉和博古米乌走进了教堂,他们成为了夫妻,但是这一场婚姻没有爱情,或者没有平等和互为意义上的爱情,芭芭拉没有爱过博古米乌,而且从来没有,“没有爱情的婚姻将这个男人给了我,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 告诉过他我不爱他。”而将爱情从婚姻中抽离出去的原因,是芭芭拉爱上了另一个男人,约瑟夫·托利博斯基,这个和她跳舞一见钟情的男人,这个奋不顾身跳入塘中采水莲的男人,早就进入了芭芭拉的心里,从此再也没有位置留给博古米乌,对于芭芭拉来说,爱情就是跳舞、采睡莲、放烟花、在田野中奔跑的浪漫,浪漫而成为经典,浪漫也成为了永恒,约瑟夫从庭院深处走来,然后跨过那扇门,拉起她的手,两个人慢慢走出去,这也成为了芭芭拉永远的幻想。
| 导演: 泽基·安特科扎克 |
为什么她嫁给了在她口中粗野的博古米乌?为什么约瑟夫娶了富有的娜列卡为妻?破碎的影像里当然没有提供足够清晰的答案,但是很明显,爱情被抽离而剩下婚姻的外壳,对于芭芭拉来说,就是一种“幸运”的命运写照。如果在爱情世界里,芭芭拉是浪漫的日,那么博古米乌则是夜,但是芭芭拉说博古米乌并不知道自己不爱他,这只不过是自己的一种猜测,一个女人不爱自己博古米乌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只不过认同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或者在他看来,这样的婚姻更是一种幸运,这就是日的生活逻辑,“你让漂泊的我安定下来。”这就是博古米乌和芭芭拉在一起的理由,只有婚姻和婚姻所呈现的这个家才是结束漂泊的形式化象征,所以博古米乌在芭芭拉的隐秘和幻想式的爱情中没有挑明,所以博古米乌在芭芭拉面前一直在说爱她而且深爱着她,但是这也是一种断裂。博古米乌和嫁给了卢尚的特蕾莎有着暧昧的情感,这一点芭芭拉也心知肚明;后来博古米乌和沃纳洛夫斯基的女儿萨文妮娅在一起,萨文妮娅甚至问他为什么不离开芭芭拉,博古米乌的回答是:“只有疯狂才能让我们结合。”而博古米乌从来没有像芭芭拉对约瑟夫那样陷入痴情,芭芭拉既然能将痴情放在心里,博古米乌更不会为萨文妮娅而疯狂;博古米乌后来和庄园里的胖女人暧昧,甚至芭芭拉来到庄园目睹了他们调情的眼神,那次她是准备去绕道看望一直在心里的约瑟夫,但是在看到博古米乌时说:“我本来要去看一个男人,但我没有,我来看你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芭芭拉对虚幻爱情的一种放弃,在她看来,即使不爱,婚姻和家庭也是她的一种归宿。
博古米乌或者还爱着芭芭拉,或者也是为了把家当成归宿,但不管如何,夜是夜日是日的这种断裂就必然是他们爱情的写照。芭芭拉纠结于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博古米乌却一辈子走不出这块土地,而这也正是他对漂泊生活的一种终结。土地对他来说就是成熟的燕麦,就是丰收和拥有,就是生存和生活,他可以不被芭芭拉所爱,但是在他看来,“土地是唯一的。”土地就是他的爱情,成为土地管理员就是他和土地爱情的书写,所以博古米乌一生没有离开土地,和芭芭拉向往的城市生活相比,他对土地的感情是炽热的,是决然的,“我不为富人服务,我只为土地服务。”他看到燕麦风吹麦浪而高兴,他为塞尔维亚庄园的农民们改善住房,他甚至希望女儿阿卡涅露学习农业,而最后他也把生命献给了这片土地:在暴风雨到来之时,“我要到田里去。”他孤身一人站在土地之上,结果生病感染了肺炎,“我要死了”的博古米乌也许并没有后悔,毕竟这是属于他的土地,死后安葬他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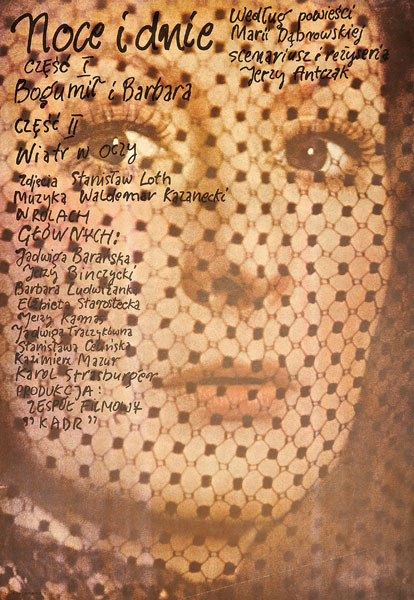
《夜与日》电影海报
芭芭拉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活着,博古米乌用土地结束了漂泊生活,这就是“夜与日”的不同命运,在他们的世界里,断裂不仅是在婚姻中呈现两个世界,更是理想和现实的巨大矛盾,但是“夜与日”的断裂又在活着的状态中连接在一起。无疑,在这个关于女人和男人、爱情和土地史诗般的故事里,安特科扎克想要表达的更多是历史际遇中的波兰命运,波兰在追寻着属于自己的爱情,在寻找着自己的土地,它们在现实意义上无法实现,但是在理想意义上却是一种可能,甚至安特科扎克要把这种可能变成新的现实。他们的女儿阿卡涅露无疑代表着这样一种理想,她受过教育,她得到了爱情,更为重要的是,她也将自己的毕生经历都投入到波兰的独立之中。对于他和男友的爱情,她充满了忧虑,“他是一个革命者,他容不下个人幸福,所以他会牺牲。”革命者就是充满了理想的人,他甚至会把个人幸福从革命事业中剔除出去,所以阿卡涅露认为这样的爱情必然会变成一种牺牲,但是芭芭拉却鼓励她,因为在芭芭拉看来,遇到理想主义者,遇到理想主义者的爱情,难道不正是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所以她把这种生活叫做奇迹,这是对自我命运的一种补偿。
当牺牲变成一个奇迹,芭芭拉基于个人命运的渴望在安特科扎克那里就慢慢变成了一种国家情怀,一方面,和阿卡涅露不同的是,他们的儿子托马泽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甚至慢慢养成了偷东西、说谎的恶行,博古米乌惩罚他,芭芭拉咒骂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基督面前祈祷他能改邪归正,但换来的是一次次的失望。托马泽科和阿卡涅露是他们的孩子,但显然在安特科扎克那里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波兰要从一个屈辱的历史中站立起来,不能光靠祈祷,需要的是那些挺身而出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革命者,只有依靠他们创造的奇迹才能让波兰走向独立,走向自由——芭芭拉的爱情和博古米乌的土地也许都是一种乌托邦的呈现,都是个体现在现实困境中的幻想,但是在国家层面上,它们却打开了另一个出口,它们带来了另一种希望。
于是安特科扎克在芭芭拉的回忆最后,设计了一个富有隐喻的结尾,她本来要去看一直在心里的约瑟夫,那是她多年来深埋在心中的爱情,但是当安置难民的约瑟夫并未在家,当她见到了约瑟夫的儿子,终于她在了却了心愿之后坐着马车离开。爱情不再是那个魂牵梦绕的人,爱情也不再是见一面的心愿,在被牺牲的岁月里,在没有奇迹的人生中,在夜与日的断裂中,爱情在心里就是一种永恒的存在,闪着理想的光芒而不会死寂,这也是她对于“一辈子爱一个人可能吗”的问题所作的终极回答。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