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2《格林童话初版全集》:故事不会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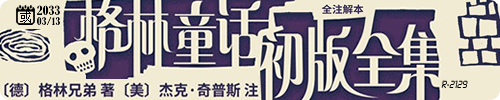
现在我们必须等他完全打开匣子,到那时,才能看见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金钥匙》
穷孩子在雪天收集取暖的木材时,发现了一把金钥匙,“如果有钥匙,那么一定会有一把锁。”他在地上继续挖,终于挖到了一只铁匣子,一把金钥匙和一只铁匣子,金钥匙一定能打开铁匣子,果然他找到了铁匣子的锁孔,他把钥匙插进去,然后转动钥匙……故事戛然而止,但其实故事并没有被真正画上句号,而是以一种等待的方式展开,等待就是把故事搁置在一种进行状态:穷孩子正在打开钥匙,故事正在发生,而每一个听到故事的人正在等待——永远的进行时态,意味着铁匣子永远没有被完全打开,意味着故事还在源源不断发生,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永远没有被讲完。
《格林童话出版全集》第二卷中的最后一个故事,但最后以悬置的方式发生着,这就是格林兄弟对故事讲述状态的一种隐喻,它预示着民间故事就像打开的铁匣子一样永不停歇,时间在改变,但是故事总是会随着时间而持续演变与发展:初版之后的七个版本,很多故事做了修改和润色,有的被删除了,但是格林兄弟都把这个故事放在最后,都以等待的方式结尾;和第二卷的最后这个故事一样,在初版的第一卷中,列在最后的是《狐狸与鹅》,它同样是一个没有被讲完的故事:一群鹅遇到了狐狸,狐狸想要把它们都吃掉,这时一只鹅鼓起勇气说:“好吧,如果我们这些可怜的鹅必须失去年轻的、无辜的生命,那么你至少仁慈地给我们做最后一次祈祷的机会,让我们不至于带着罪过死去。”当祈祷结束后,狐狸就可以挑选最肥的那只鹅吃掉,狐狸答应了这个要求,第一只鹅开始祈祷,但是它的祈祷很冗长,“嘎!嘎!”的祈祷声一直在继续,而第二只鹅也开始了自己“嘎!嘎!”的祈祷,它们没有完成祈祷,意味着狐狸不能吃它们,更意味着故事会继续将下去,“可是直到现在,它们仍在祈祷。”
《金钥匙》的故事来源于玛丽·哈森普鲁格的讲述,《狐狸与鹅》的故事则来自冯·哈茨豪森的口述,不同的讲述者,不同的故事,但是对于格林兄弟来说,将它们安排在第二卷和第一卷的最后,用意是明显的,等待打开,等待祈祷,故事将变得永无止境。这是将故事讲述变成故事流传的一种文本创造,但是当两卷本的《格林童话》最后以《金钥匙》首尾,却传递着另一个想法:当金钥匙插入了铁匣子的锁孔,在转动之后,一个世界就会以一种等待而注目的方式被打开,而这无疑就设下了悬念:铁匣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也许《格林童话》是这个铁匣子,而汇集起来构成这本童话集的德国口述民间故事更像是那个神秘而有趣的铁匣子,当格林兄弟以这样的方式设置打开的悬念,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为了完全打开德国民间故事的铁匣子。
2012年,是《格林童话初版》第一卷出版200周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出版全集,杰克·奇普斯在《英文版致谢》中认为自己完成的这项任务是为了把这一宝藏分享给年轻人,“格林兄弟的故事不仅是属于德国的宝藏,也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初版两百周年后出版全集,就是用金钥匙打开了那只铁匣子,而在200年前,格林兄弟在出版第一卷时,在序言中也说到了德国民间文学这只铁匣子里藏着的宝藏:“长久以来,故事为我们带来这么多欢乐与感动,它们讲述道理,其光辉从不朽的源头持续折射着,滋润人生,就像卷起的叶片上的露水,即使只是小小的一滴,也会在破晓时分闪闪发光。”从兄弟俩结识浪漫派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坦诺和浪漫派小说家阿齐姆·冯·阿尔尼姆,两位导师便开启了格林兄弟对民间故事收集的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民间故事构成了“自然的诗歌”的重要部分——经常使用这个词来形容令人敬畏的古日耳曼语及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学。他们认为,“自然的诗歌”可以复兴德国人民的真实天性,而民间故事包含着德国文化传承中最核心的真相,他们工作的背后,是对浪漫的渴求,更是在故事绝迹前挖掘并保存大众对德国文化作出的贡献,“壁炉侧方、厨房炉边、通往阁楼的石梯、仍在庆祝的节日、远离喧闹的幽静牧场与森林,尤其是那些不受干扰的想象力,都化作了树篱,保护着故事,使它们得以代代相传。”所以在格林兄弟看来,人会死去,但是故事不会,记录这些故事就是为了在讲述者渐渐老去之前把故事保存下来,然后放进铁匣子,让更多的后来人在期待中打开铁匣子,以一种等待和延续的方式把“金钥匙”永远握在自己手里。
但是,在这200年的时间里,不管是金钥匙还是铁匣子却没有维持它最原初的样子,杰克·奇普斯提到,初版第一卷出版于1812年,第二卷则在1815年出版,初版之后一些反对的声音也同时出现,他们认为里面很多故事不适宜儿童阅读,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道德低下,于是在1819年第二版出版时,编辑标准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改良:除了删除初版中大量故事加入了超过50个新故事、抽去注解、修订了《前言》和《导言》、添加插图等形式上的改变之外,在内容上则弱化了故事的残酷性,删除了冒犯中产阶层的故事,增加了宗教说教,使得故事风格化,从而唤起民间诗歌艺术和自然美德。进行改良是为了使之更趋近儿童与家庭读物,使之成为精致的、艺术化的宝石。但是改良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一种妥协,据说在1816年的时候,格林兄弟中的雅各布·格林反对对故事作太多的改变,抵制修饰和润色,初版第二卷序言中的观点可以代表雅各布的声音,他认为这些故事所代表的正是一种“自然”,“自然界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示范,它允许各种各样的花朵、树叶长出不同的颜色和形状,无论对人类是否有助益或有何用途。”这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就是反对人为对故事进行改良而和美化。但是后来因为事务缠身,雅各布将编辑任务交给了威廉·格林,而威廉·格林“无法控制自己使这些故事更加艺术化的欲望”,他的目的就是吸引更多中产阶层的读者。
| 编号:C37·2250503·2302 |
之后的六个版本到底删除了哪些故事?到底美化了哪些童话?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无法知道艺术化和道德化的改良如何破坏了有用的“自然主义”?但是正如反对者所提出的,在第一版中很多故事和“受伤”的年轻人有关,他们是和父母争吵的青年,是被残忍对待和抛弃的孩子,是陷入困境的战士,是被迫害的年轻女性,是滥用权力的王后和继母,是危险的闯入者……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暗黑童话”:第一卷中的《持刀的手》中,母亲把三个儿子视为整个世界,却歧视女儿,女儿只好被迫去野外挖煤,精灵见此便帮助她,递给她一把具有神奇力量的刀,用这把刀就能很快完成每天的劳作,终于母亲发现了蹊跷让儿子跟着她,兄弟得知了秘密于是趁精灵的手伸出来的时候,用那把刀砍下了精灵的手,“精灵血淋淋的断手缩了回去。精灵坚信是爱人背叛了他,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这就是整个故事的结尾;《聪明的汉斯》中的汉斯去嘉丽桃家里,嘉丽桃每次都会送东西给他,一根针、一把刀、一头小羊羔、一片培根、一头小牛,最后她把自己也送给了汉斯,当汉斯牵着嘉丽桃回来,母亲却说:“你真傻,汉斯,应该用眼睛投给她友善的注视。”于是汉斯把牛羊的眼睛都挖了出来,朝嘉丽桃身上扔去,嘉丽桃最后生气跑了,“这就是汉斯失去新娘的故事。”
在第二卷中,这样的暗黑故事更多,《关于蟾蜍的故事》中男孩和蟾蜍萌生了友谊,每次自己吃饭总是要给蟾蜍留着,但是当男孩长大后,母亲看到蟾蜍就冲过去把蟾蜍打死了,“从此,孩子日渐消瘦,最后死了。”《顽固的孩子》是黑森林的口述传说,顽固的孩子总是和母亲作对,最后生病死去,被放进坟墓之后他的一只手却伸出了泥土指向空中,人们将手臂按下盖上新土,但是手臂还是审了出来,于是母亲用鞭子抽打他的手,“这个孩子第一次变得老老实实,在地下安息。”约翰尼斯·普雷多雷斯讲述的《陷入饥荒的孩子们》的故事,是关于母亲和女儿的,因为贫穷母亲让女儿们出去找吃的,但是还是不能免除饥饿,“你们必须死,不然我们都要饿死。”于是两个女儿真的就躺下了,她们对母亲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躺下睡觉,直到审判日到来。”这些暗黑的故事和死亡有关,而且是变态的死亡、无法拯救的死亡、缺乏美德的死亡,没有救赎者,也没有感化者,而“暗黑故事”之所以暗黑,似乎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信仰的无力,《顽固的孩子》因为顽固,“连敬爱的上帝也不再关照他了。”而《陷入饥荒的孩子们》之所以放弃了寻找,等待的正是审判日的到来。
《格林童话》初版中的故事就像在序言中所说,是叶片上的露水,它带来的是欢乐和感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故事都流淌着相同的纯粹与天真,表现出孩童美好、可爱的品质。”这就是“自然的诗歌”在主题上具有的意义,不管是经典的《渔夫与妻子》《小红帽》《白雪公主》《灰姑娘》等故事,还是更多口口相传的普通故事,都是在传颂一种美德,而且是真善美战胜假恶丑,那些继母、王后、巫婆,最后都被美好的力量所战胜,“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成了几乎每个故事的结局。但是,初版中的这些暗黑故事能带来“欢乐和感动”?会变成“自然的诗歌”?初版之后的改良版和美化版删除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宗教教化的故事,在杰克·奇普斯看来,改良就是用“多愁善感的基督教精神和清教徒意识形态”为它们“接种疫苗”,从而在审查之后阅读的版本中起到免疫作用。这的确反映了当时中产阶层的价值观,格林兄弟的改良就是对这一群体的某种妥协,但实际上在初版中,这样的基督教精神和清教徒意识形态也在暗黑故事中成为一种预设。
在第一卷的《圣母马利亚的孩子》中,贫穷的伐木工把自己的孩子无奈交给了圣母玛利亚,玛利亚把她带到了天堂,有一次出远门她交给女孩十三个房间的钥匙,警告她第十三个房间的门禁止打开,但是小女孩出于好奇还是打开了那扇门,回来之后面对圣母玛利亚的质问,小女孩欺骗她说没有打开过,圣母玛利亚惩罚了她,最终让她失去了说法的能力,最后变成了王后的女孩被推上了火刑柱,这时候她才后悔:“在我死后,我想对圣母马利亚忏悔:我打开过天堂的禁门。长久以来,我一直不承认,实在是太不对了!”当一个说谎的人忏悔,那么天堂的门再次向她开启,于是火焰熄灭,于是开口说话,于是圣母玛利亚赦免了她的罪,“从此以后,王后一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在《死神与牧鹅少年》中,牧鹅少年厌倦了人世,他跟着死神越过了河,却看见了美丽国度,为什么死亡是美丽的,因为,“他环顾四周,首席牧羊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向他走来,将一顶皇冠戴在他的头上,把他领人牧羊人的城堡。”
而在第二卷中,第一次出现了“上帝”,他在《穷人和富人》中成为对人类道德的考验者,富人除了烦躁、浪费精力、牺牲一匹马之外,什么都没得到,“另一边的穷人则一直过着快乐、平和、虔诚的生活,抵达幸福的终点。”《天堂的婚礼》中,小男孩听到牧师说:“任何渴望进入天堂的人,必须一贯走直路。”他就这样走直线最后进入了一座教堂,那里举行着神圣的仪式,但那不是天堂,小男孩留在了这里,他变得更为虔诚,即使在生病之后恢复健康,他也要像圣母像弥补没有送来的食物,正是这份虔诚,在他死后,“他前去与上帝参加了永恒的婚礼。”在《太阳可鉴,真相终将大白》中,没有出现上帝,但是故事中的“太阳”就是上帝,只有他知道真相,“太阳可鉴,真相终将大白!”
从暗黑童话到上帝故事,《格林童话》初版中就有了关于救赎、虔诚的宗教故事,但这些故事很难说是单纯的说教,在抵达最后的天堂世界里,是不是也呈现出一种欢乐和感动,是不是也流淌着纯粹与天真?当然,这些故事的讲述手法已经具有了某种隐喻性,而在初版第一卷的序言中,格林兄弟明显是反对隐喻的,“这是故事早就懂得如何行使的权利,后来的‘讲故事’却拼命用隐喻讲出来。”在他们看来,不用隐喻将故事就是抵达故事的直率、质朴、尖锐,就是诠释着童话的本质,“最伟大和最渺小的事物都如此天真亲切,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实际上格林兄弟这一“讲故事”的标准设置并非在主题意义上,而是在讲述方式上:尊重讲述者口述的方式,原汁原味记录下来,这样才能像自然之露珠一样,所以反对隐喻是为了维护口述的权利,而格林兄弟投入大量时间和经历正是为了让口述成为口述,让故事成为故事,让“讲故事”真正讲故事,“既然这些故事如此贴近最早、最单纯的生活形式,也就解释了它们何以能广泛地传播。”
所以在没有隐喻的意义上,《格林童话》提供了关于“讲故事”最纯粹也最本质的形式:每一篇注解都提及了故事的来源,考察了故事的不同版本;将故事讲述者的名字和介绍列于文集的最后,这是对他们的最大尊重;而更为重要的是,讲述者自动进入到童话之中:多萝西娅·魏曼讲述的故事《聪明的农夫女儿》中,最后一句话是:“于是国王带着王后回到了皇家城堡,再次举办了婚礼。我敢肯定,他们至今仍在一起生活。”“我敢肯定”是对故事的美好祝愿;来源路德维希·冯·哈茨豪森和斐迪南·冯·哈茨豪森的《土地神》,故事在公主和年轻猎人的婚礼中结束,“我穿了一双玻璃鞋出席婚礼,在石头上绊了一下,只听见‘叮当’一声!我的鞋碎成了两半。”讲述者不仅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在场的;《两个国王的孩子》的最后一句是:“讲这个故事的最后一个人,嘴唇至今还热乎着呢。”讲故事的人不止一个,这正是故事在“嘴唇还热乎”中被流传;而在《安乐乡的传说》和《迪特马斯奇闻异事》的故事中,“我”讲述故事,也讲述我所见所闻的故事,讲述所见所闻之我的故事:
我曾经到过安乐乡,看到罗马和拉特兰宫悬挂在一根细细的丝线上,一个没腿的男人跑得比马还快,一把锋利的剑把桥斩成两段。然后我又看见一头年幼的驴长着银鼻子,正在追两只跑得飞快的野兔;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上长满烤饼,一只皮包骨的老山羊驮着一百卡车重的肥肉和六十车重的盐。你问我吹牛吹够了没?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