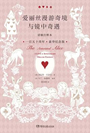2025-07-28《爱丽丝漫游奇境与镜中奇遇》:说个有胡话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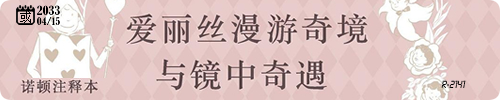
“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寓意。”爱丽丝大胆地说。
——《第九章 假海龟的故事》
公爵夫人重新出现,她热情地挽着爱丽丝的手,但是爱丽丝差不多已经忘了公爵夫人,直到公爵夫人在她耳边说话,“亲爱的,你在想事情,以至于都忘了说话。我现在无法告诉你这其中有什么寓意,但是过一会儿我就会想起来的。”当爱丽丝大胆地回应,其实是对公爵夫人所说的“寓意”的一种否定,想事情不说话也好,忘记了公爵夫人也罢,在爱丽丝看来这就是事情本身,“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寓意。”但是公爵夫人以呵斥的方式,否定了爱丽丝对“寓意”的否定:“所有事物都有寓意,只是看我们能不能体会而已。”
否定之否定,就是一种肯定,对寓意的肯定,马丁·加德纳在这一章的注解中引用了不同的文本来解读“寓意”之寓意:狄更斯在《董贝父子》第二章里写道:“每一件事物中都有道德寓意,只是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善用而已。”詹姆斯·金凯德在潘尼罗亚尔版《爱丽丝镜中奇遇》中引用卡罗尔的文章《牛津基督教堂学院的新钟楼》:“每一件事物都有道德寓意,只是看我们自己要不要去寻找。华兹华斯写的诗大半首都是寓意,至于拜伦就少一点,而塔珀的诗整首都是寓意。”不同的文本在表达着文字背后的寓意,连卡罗尔自己的其他文章也被引用,每一件事物都有寓意,每一个故事都有道德寓意,似乎我们所有的阅读都是像公爵夫人一样会想起背后的寓意,去体会寓意带来的道德目的,那么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是不是真的是对爱丽丝“根本没有什么寓意”的否定?
第九章《海龟的故事》中的确藏有很多的隐含意义:为什么所有玩槌球的人被拘禁并被判了死刑?鹰头狮和假海龟到底代表着什么?假海龟所说的课程“旋转”“扭动”“野心”“分心”“丑化”“嘲笑”又指代什么?加德纳的注释就是揭露这些文字背后的寓意:鹰头狮在中世纪时常被认为象征着基督身上人与神的结合,鹰头狮和假海龟是用来讽刺牛津大学里多愁善感的大学校友;假海龟所列出的学习科目都是双关语,“旋转”的音“reeling”近于“阅读”的“reading”、“扭动”的音“writhing”则接近“写作”的“writing",诸如此类,“野心”音近“加法”、“分心”则音近“减法”、“丑化”音近“乘法”、“嘲笑”音近“除法”……在这里,实际上注释的解读分为两种,一种是表面事物背后的象征意义,比如鹰头狮和假海龟的象征意义,另一种则是通过发音构建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连接,如果把象征看做是一种寓意,其实文字相关的双关则是一种形式意义的游戏。
如果我们像公爵夫人一样肯定每件事物背后都有隐藏的寓意,那么,“事物”可以看作是卡罗尔在文本表面的一种书写,它所构成的是《爱丽丝漫游奇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这两部作品纯粹在文字意义上的作品;寓意则是在文字表面之下深藏着的象征和隐喻,一个是被呈现的,另一个则需要体会、寻找和发现,由此构成了卡罗尔文本的两重世界,那么在这个寓意世界里,两者是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部经典的整体?还是在过度解读中造成了和文本真正意义的分离?要解开这个答案,也许从卡罗尔对这本书的解读的“直接性”中找到答案。这种直接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卡罗尔相关的介绍和阐述,另一个则是文本本身提供的答案。对于这本称为小说或童话的书,卡罗尔在1871年的圣诞节发表了《致读过<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所有小朋友》一文,他在感谢成千上万读过《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小朋友的同时,认为写作这本书就是为了“祝福着世上所有的小朋友”,为什么要祝福,“美妙是因为,你们回想起充满爱的生活,在其中可以找寻到真正的,唯一值得拥有的幸福,也就是由于让他人幸福而感到的幸福!”
同样,在1876年的复活节,卡罗尔发表了《祝每个喜欢<爱丽丝>的小朋友复活节快乐》的文章,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本书是“为我所喜爱的小朋友们写的”,因为书中的故事增添了“天真与健康快乐”,而且这种“天真与健康快乐”是作为童年永远的财富,即使“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会在回顾中不会感到羞愧和悲伤,“你的快乐不会因此消减,因为到了那一天,你将会看见更为明亮的黎明。”这个更为明亮的黎明有可爱的景象,又天使的手,有甜美的声音,“所有让这小小尘世中的人生蒙上阴影的悲伤与罪恶都会被你遗忘,就像是昨夜的一场梦!”这是一个关于童年“天真与健康快乐”的故事,这是一个在遭受挫折和痛苦中依然可以在回忆中带来快乐的故事,这是一个让你人生的悲伤和罪恶都可以被遗忘的故事,所以对于这个故事,卡罗尔所强调的就是天真、健康和快乐,它是为小朋友而营造,也为这些小朋友长大后经历了人生曲折之后重现发现童年之美好而创作。
| 编号:C38·2250604·2315 |
这或者就是卡罗尔在创作之初的真正“寓意”,但是一个“天真与健康快乐”的故事为什么可以抵御挫折和死荫?可以遗忘阴影和罪恶?那就意味着故事本身也是在书写挫折和死荫、遗忘阴影和罪恶,这也就涉及到卡罗尔创作这个故事的缘由,按照加德纳的说法,卡罗尔曾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学院教授数学,他是个害羞的单身汉,但是被基督教堂学院院长罗宾逊·达克沃思的女儿爱丽丝·利德尔所吸引。1862年7月的某个“金色的午后”,卡罗尔和罗宾逊·达克沃思带着可爱的三个女儿在泰晤士河上划船,爱丽丝就在其中,当时的爱丽丝只有七岁,卡罗尔就是在划船时被要求讲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个“爱丽丝漫游奇境”,“天气如梦似幻,/我气息微弱得连羽毛都吹不动,/她们居然求我说故事!”在卷首的这首诗里,卡罗尔回忆了这个讲故事的午后。实际上,这就是卡罗尔所谓的“死荫的幽谷”,他迷恋爱丽丝,但是爱丽丝年纪太小,他和爱丽丝之间的年龄差距就像卡罗尔和他母亲的差距差不多,而等爱丽丝长大之后她也嫁给了别人,可以说,这是一段暗恋的故事,之后的卡罗尔也结交了很多迷人的小姑娘,但是没有人能取代爱丽丝的位置,在爱丽丝结婚后,卡罗尔写给她的信中说:“自从认识你以后,我结交了很多儿童朋友,但他们与你截然不同。”
从七岁时就迷恋上了爱丽丝,因为爱丽丝接触其他迷人的小女孩,却发现根本无法喜欢她们,卡罗尔作为著名的无性生活的作家,爱丽丝其实已经构成了他人生的“寓意”,所以,一方面卡罗尔将这次游玩所讲的故事变成了《爱丽丝漫游奇境》,他把这个故事变成了对这种“天真与健康快乐”的怀念,“为了让我喜爱的一个孩子开心(我不记得自己还有其他动机),我写出手稿,并且自己动手画出一幅幅粗陋的插图(因为我从未上过绘画课,所以我画的图违反了解剖学与艺术的所有法则),直到最近我才以摹本的形式出版了这册故事。”卡罗尔在故事发生25年后的1887年4月写道,在这篇名为《舞台上的<爱丽丝>》的文章中卡罗尔描述了他笔下女主角的性格:
梦境里的爱丽丝,在你的创造者眼里,你是什么模样?他该怎样描绘你?可爱是最重要的,可爱与温柔:如小狗般可爱(原谅我这平凡无奇的比喻,但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这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能可爱得如此纯真而完美),如小鹿般温柔;然后是有礼貌——对所有人都一样,无论对方地位高低,高贵还是丑陋,是国王还是毛毛虫,即便她自己是国王的女儿,身穿金缕衣;再来就是愿意相信与接受一切最荒谬与不可能的事物,展现出只有做梦的人才具备的完全相信的态度;最后是好奇——好奇心无比强烈,而且对生活感到极度愉悦,这种愉悦只有在童年的欢乐时刻才会出现,因为在那当下一切都是如此新鲜美好,也不知罪恶与哀伤为何物——那只是两个空洞而无意义的词!
这就是卡罗尔真正的“寓意”,爱丽丝如小狗般可爱,如小鹿般温柔,相信与接受一切的荒谬和不可能的事,而且对生活充满了好奇,这一切是故事中爱丽丝的性格,也是卡罗尔对爱丽丝原型的一种理想化塑造,她所代表的就是美好,所以在卷首的歌曲中,卡罗尔写道:“爱丽丝!请收下这孩子气的故事,/以温柔的手/将它和童年的美梦摆在一起,/系上回忆的神秘丝带,/好像朝圣者花环上的枯萎花朵/采自遥远的地方。”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献给爱丽丝,献给代表美好的爱丽丝——即使,对于卡罗尔来说就是一个现实之外发生的梦,而且在形式上,“漫游奇境”就是一个梦,“爱丽丝陪姐姐坐在河畔,无事可做,开始无聊起来。”小说的第一句是一种“无聊”,而进入兔子洞所开始的漫游就是对无聊的一种摆脱,而当爱丽丝最后回到姐姐身边,这个梦也感染了姐姐,成为了姐姐的一个梦,于是这个“梦中梦”带入了另一种美好的境界,“姐姐先梦到小爱丽丝,只见她的小手环抱着膝盖,—双明亮热切的眼睛仰望着姐姐。”姐姐知道小爱丽丝会长大变成一个女人,但是,“她在那些成熟的岁月里依然可以保持童年的纯真与爱心。”这种纯真与童心的表达就是给更多的小孩子讲述奇怪的故事,讲述奇境之梦,“她会跟孩子们一样体会到淡淡的哀伤,也会在他们的纯真欢乐中感受到愉悦,回想起自己的童年,以及那些快乐的夏日时光。”
爱丽丝的姐姐梦到爱丽丝的梦,这是一种“梦中梦”的结构,它是循环,它是反复,但是在深层次意义上则代表着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长大。如此可以看作是卡罗尔创作的“寓意”,而在这个“寓意”之下,很多对故事的解读可能就变成了过度解读,比如沙恩·莱斯利认为故事中隐藏着一段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地区的宗教争论,他把故事中的“橘子酱”看成是新教立场中的“威廉三世”,因为威廉三世被称为“奥兰治的威廉”,即“William of Orange”;红白骑士之战则象征着托马斯·赫胥黎与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之间的冲突;蓝色毛毛虫象征本杰明乔伊特,白王后则是约翰·亨利·纽曼枢机主教,红往后是亨利·曼宁枢机主教;柴郡猫象征着尼古拉斯·怀斯曼枢机主教,而扎勃沃克“肯定是英国人对于教皇权势的恐惧心理的表现”……
对于《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创作“寓意”,还可以从卷首的那首儿歌找到进入的钥匙,三女孩要求卡罗尔讲述故事,大姐下命令“现在就开始”,二姐则希望“说个有胡话的故事”,三妹即爱丽丝则是喜欢插嘴,于是这个故事开始讲述,而在卡罗尔不知道该怎样讲希望“下次再讲”,三个人又说:“下次就是现在”,于是,“一段接着一段,/古怪的事件慢慢成形。”这是一个古怪的故事,但是在卡罗尔“即兴”的讲述中就具有了一种“孩子气”,而这也正符合童年的特质,正符合爱丽丝对荒谬和不可能事的相信这一性格,“所以故事一开始我就把女主角送进兔子洞里,但压根儿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而这就构成了这个故事另外的寓意:讲述一个荒谬、可能性、孩子气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就是一个“有胡话的故事”,于是,“胡话”便构成了故事的“寓意”,但这不是关于象征、隐喻的“寓意”,而是一种在形式意义上形成了“胡话”即nonsense的故事,而《爱丽丝梦游奇景》中的变大变小悖论、双关语的文字游戏、梦中梦的发倒转,“我是另一个自己”的主体颠倒,都构成了一种“胡话”——在形式意义上而不是在象征意义上的“寓意”。
爱丽丝掉入兔子洞,就是进入一个充满胡话的奇幻之地,这胡话就是随处可见的“双关语”,老鼠说到的“tale”(故事)与“tail”(尾巴)是谐音,假海龟列出的课程都是和音相关的双关语,鹰头狮说“they never executes nobody”,这句话里的“无人”不是没有人,而是“无人”,而爱丽丝说到的“我帮你把结解开”也是利用了“not”(没有)与“knot”(打结)的谐音制造的文字游戏——据说卡罗尔还为读者出了关于故事中“结”的难题,刊登在1880年的《每月讯息》杂志上,五年之后还是结集出版了《打结的故事》。同样小说中的那句“为什么渡鸦像书桌?”也变成了一个著名的谜语,卡罗尔在为1896年版写的新序言中还公布了自己的答案:“因为它能发出一些鸣声/用来写一些笔记,虽然都很单调。还有,它绝对不能够前后颠倒!”卡罗尔也承认,答案只是事后想出来的,“当初我想出这个谜语的时候,它根本没有答案。”但是在卡罗尔之后,这个谜语就被不同人解读,1989年,英国的刘易斯·卡罗尔学会举办了竞赛征求新的谜底;1991年,英国《旁观者》(周刊把谜语当成周刊的1683号竞赛题,得到了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因为如果没有两者,《美丽新世界》就写不出来。”彼得·维尔的答案是:“因为渡鸦会突然飞走( fiapping fits),而书桌配有写字板(fitting flaps)。”弗朗西斯·赫胥黎则认为:“因为它们的嘴/账单(bill)预示的是厄运(ill)。因为这两个词中各藏了一条河:涅瓦河( Neva)和艾斯克河(Esk)。”双关语变成了谜语,谜语让大家猜谜,无论是卡罗尔还是后来者,他们都把谜语当成了游戏,对它的解读也完全是在形式上完成的,这也许就是卡罗尔一直在强调的孩子气,也许就是小说所讲述的“胡话”。
最重要的一种“胡话”就是爱丽丝变大又变小的悖论,进入兔子洞之后,爱丽丝发现了小桌子,看见了桌子上的金钥匙,她发现自己变大了;当她发现桌子上写有“喝我”的瓶子,她又变小了,“此刻她只有十英寸高,一想到现在可以穿过小门,走进那可爱的花园,她的脸上就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把手上的扇子扔了,终于不再缩小,而掉下去的地方竟然是爱丽丝在身高九英尺时哭出来的眼泪池塘;吃蛋糕变小了,吃蘑菇也变小了……变大,是因为奇境里的东西都小,而当自己变小,那些东西又变大了,所以在这个悖论里,爱丽丝最想要的不是变大,也不是变小,而是不变来变去,而是有一个正常大小,当睡鼠说:“你没有在这里长大的权利。”这也成为了对“长大”这一规则的消解,“第四十二条规则。身高超过一英里的人一律要离开法庭。”就像审判是国王读出的“第四十二条规则”,在注释中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但是都成为了成人世界里的一种象征,实际上就像爱丽丝所说的,根本没有什么规则,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恢复成正常大小时,爱丽丝便戳穿了这个成人的象征游戏,“你们不过是一副纸牌!”
这只是一个“胡话”的故事,只是一场梦,只是一个充满童趣的游戏,“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寓意。”但是当卡罗尔停留在形式意义的游戏时,如果将形式意义赋予多元、丰富甚至繁多的寓意,实际上也是破坏了童话该有的天真、健康和可爱。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获得成功之后,卡罗尔又创作了《爱丽丝镜中奇遇》,让这个游戏更富有“胡话”意味,在这里他采取的是一种对倒的“胡话”:镜中奇遇,爱丽丝闯入的就是“镜中屋”,镜子具有一种不对称的相反特点,而这种“反转”就成为一种寓意,特威德尔丁和特威德尔当就是互成镜像的双胞胎,白骑士唱歌时提到把右脚挤进左脚的鞋子里,国王有“一个过来,另一个过去”两个新诗,奇数和偶数对应左和右……反转就是倒转,这不仅在爱丽丝变大变小中得到体现,也在逻辑中成为一种矛盾:红王后说起一座山丘非常大,眼前的山丘就变成了山谷;饼干可以用来止渴;为了停留在原地,爱丽丝必须最快的速度奔跑;白王后说,“规则是,明天有果酱,昨天有果酱 但今天永远不会有果酱。”爱丽丝质问红王后:“那五个晚上连在一起过就比一个晚上暖和吗?”红王后说:“当然,暖和五倍。”但这也意味这会“寒冷五倍”……
如果说《爱丽丝漫游奇境》是在一种“胡话”中构建充满孩子气的故事,那么《爱丽丝镜中奇遇》却成为了卡罗尔主动赋予寓意的小说,小说的棋盘结构、镜像隐喻在一开始就被体现出来,而且卡罗尔精心设计了一个迷宫:爱丽丝只能与相邻的棋子交谈,王后的丈夫只能待在原地,白骑士古怪的行为对应着棋子的移动;马必须先走两格再从左或右走一格……而且在序言中卡罗尔解释了棋子的走法,“红方与白方的交替顺序或许没有严格遵循规定,而三个后的易位也只是为了说明她们进入了王宫。”当小说变成了“严格遵守规则”的象棋游戏,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游戏,甚至将棋局和故事“巧妙结合”起来的做法无非是卡罗尔精心设计的一种体现,却不再具有可能性的趣味,相反,规则反而破坏了游戏,而过度的游戏又破坏了童趣。于是,在编织、创造寓意的世界里,爱丽丝终于成为了王后,白骑士终于离她而去,本没有寓意的故事也在寓意中被解构了,就像卡罗尔在卷首诗中就预言的:“声声叹息让整个故事蒙上阴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