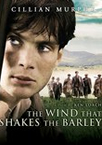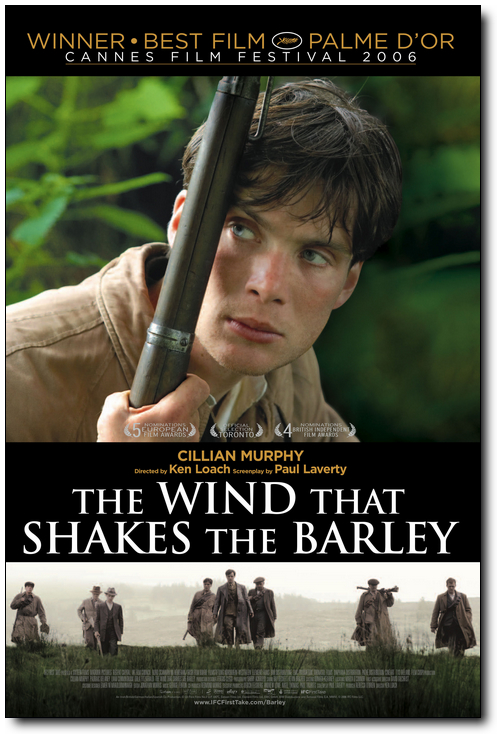2016-07-28 《风吹麦浪》:用子弹注解的兄弟情

“准备,上膛,瞄准,射击……”当子弹穿过戴米恩身体的时候,他面前站着的不是自己的哥哥泰迪,而是行刑者,是内战的敌人,是依靠合约妥协的爱尔兰政府军首领,所以在戴米恩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当他被绑在柱子上的时候,当面对黑漆漆的枪口的时候,戴米恩的目光里其实更多是对敌人的仇视,是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他没有在泰迪“还不晚”的引诱中屈服,没有在给他胸前戴上白布的时候投降,更没有在遗言中说出武器库的位置,当那些齐发的子弹射穿他的时候,他的耳边仿佛听见了奶奶佩姬曾经唱起过的那首民谣:“我心悲伤,不忍对你道出离别的话语;但我更不堪忍受,外族压迫的屈辱。于是我说,明天一早我要走向山谷,当微风吹动金色的麦浪,我将加入那支勇敢者的队伍。”
风吹麦浪,是不息的精神,是绿色的希望,是英勇的举动,而当兄弟情、战友情最后变成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的时候,所谓对于外族压迫的抗争变成了革命理想主义对于民族独立妥协的藐视。在最后被关押的牢里,泰迪走到戴米恩的身边,希望他说出武器库的地方,泰迪几乎以诱惑的方式让自己的弟弟放弃抗争,交代武器库的位置,然后就可以赦免,就可以回家,就可以做自己一直想做的医生。但是这种诱惑对于戴米恩来说,似乎变成了一种可耻,“我曾经一枪打穿了雷利的心窝,因为我从来不出卖同志。”因为在戴米恩看来,革命从来没有投降,独立永远不用妥协,否则,只有被子弹射穿的命运。
但是,作为一个坚定地在为爱尔兰民族独立作斗争的领袖人物,他用子弹结束了出卖情报的雷利的生命,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的坚持,是对于可耻背叛的惩罚,但是自己却依然死在哥哥泰迪的手上,死在同样曾为爱尔兰独立作出努力的政府军枪口下,是不是命运的一种喟叹?是不是革命的一次失败?而其实当他面对雷利的时候,面对泰迪的时候,都是民族主义对个人情感的超越,在他眼前,所谓的兄弟、战友,只有站在统一战线上才是自己人,才是朋友和兄弟,才能听见耳边响起的“风吹麦浪”的民谣,才会在开阔的山谷间看见希望。
|
| 导演: 肯·洛奇 |
 |
同样是关于武器库在哪的问题,同样是面对利诱,同样是为了革命理想,但是为什么这一场爱尔兰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最终却走向了不同道路,甚至让他们从战友变成了敌人?戴米恩面对泰迪的引诱时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想逃避却还是卷入了这场战争;如今我想脱身而不能。”实际上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矛盾,本来想逃避,却卷入了战争,现在想脱身,却再也无法回到曾经,也就是说,面对自己的兄弟,面对曾经的战友,他们已经无法以自我意志的实现来化解纠葛,更无法在枪口之下成为另一个自己。
在戴米恩来说,在1920年的爱尔兰,他一直想要“逃避”的生活,曾经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去往伦敦的医院深造。这种被讥讽为“添国王屁眼”的行为,在自己家乡的那些人看来,就是一种妥协。当英国“棕狗子”拿着枪来侵扰戴米恩所住的村子,用“爱尔兰佬”百般侮辱他的家人的时候,他还没有反抗的意识,甚至当米哈因为不肯用英语报出自己的名字,因为出拳反抗英国军人而最终被枪杀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也没有那种仇恨,“米哈因为不愿用英语说自己的名字而被枪杀,这也叫烈士?”质疑是因为还不懂革命的意义,是因为还没有独立的行动,还在幻想着到英国改变自己的人生。而当他准备登上火车的时候,看见英国“棕狗子”狠揍火车司机和相关人员的时候,他才见证了他们的暴行,也最终放弃了去往英国的想法,而成为一名为爱尔兰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革命志士。
|
|
| 《风吹麦浪》电影海报 |
对米哈之死出奇的冷漠,对火车司机被打却尤为愤怒,这两种遭遇对于戴米恩走上革命道路,缺乏逻辑性,或者缺乏情感的过渡,而实际上戴米恩对于革命的理解几乎像所有爱尔兰人一样,充满了宿命论,很多时候它可能就是情绪的一种渲染,可能就是意志的突然爆发,所以在泰迪和戴米恩一起加入革命队伍的时候,对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始终处在一种矛盾中。“除非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你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谈到更早的1913年大罢工,他们对于最后的革命理想用了一种假设,也就是说,争取的胜利不是为了一种彻底的独立,那么所有的革命,其实都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和自由。
所以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们抢夺枪械,他们伏击敌人,他们制造了一起起针对英国统治者的暴力袭击,他们在风吹麦浪的山野中夺取一次次战役的胜利,似乎都只是为最后的内战铺设一条宿命的道路。他们也曾被抓捕,也曾经受考验,也曾英勇反抗,但是在反抗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革命理解,使得他们又总是左右摇摆。在一次下议院认可的法庭审讯中,最终法官判定农妇不必归还高利贷者斯万尼的债务,这是一种革命平均主义的理想,戴米恩和其他同志支持法庭的判决,但是泰迪却把斯万尼带了出去,在他看来,在革命中需要的是财力的支持,只有财力才可以购买更多武器,才可以开展更多的武装反抗,所以他把斯万尼当成了革命的合作者,但是这种行为又变成了对于法庭的藐视,对于“我们的政府”的漠视,所以泰迪和戴米恩在相互的争论中,注解了关于革命的不同理解。
而真正产生分歧的是,当新芬党和英国政府最终签订停战合约的时候,所有革命者都以为是独立解放运动最好的消息,而其实,这种独立却是不彻底的,成立新的爱尔兰自由邦,看起来是自由的开端,但其实还是要效忠英国国王,甚至北爱六郡还要接受英国统治。也就是说,他们用战友的牺牲换来的依然只是一个傀儡征服,所以当这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在爱尔兰分立成两派,一派接受合约成立爱尔兰新政府,另一派则继续革命,继续追求独立。在这种分立中,泰迪成为合约派,他穿上了新政府的制服,成为新政府的一员,对于革命,他的说法是:“等我们足够强大了,就可以撕毁合约。”实际上,正是这种妥协让戴米恩非常恼火,他公开在教会里表达观点,“这条约只会让人成为英帝国的仆人,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自由,而不是折中的自由,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议会,而不是傀儡的议会……”
所以合约派和自由派,在革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却反目成仇,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甚至演变成一场爱尔兰内战。从一致对外到反目成仇,对于泰迪和戴米恩来说,其实面临的还有亲情的背叛问题,而他们的矛盾从本质上说就是革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对于这种矛盾,唯一化解的办法就是武力,就是子弹。如果把爱尔兰独立解放运动分成两个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最体现矛盾标志性的是两次枪决。在一致对外过程中,雷利因为约翰爵士和英国军人的威逼,终于出卖了革命信息,所以当从狱中被解救出来之后,戴米恩就把枪口对准了爵士和雷利,爵士是和英国人勾结,他的死对于戴米恩来说是一种快意的复仇,而对于雷利,这个从小和自己成长的伙伴,戴米恩体会的是一种悲痛和无奈,在风吹麦浪的山谷间,他终于举起了枪,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让“叛徒”倒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处决雷利,在戴米恩的心中所激起的是情感的巨澜,他告诉自己的女友辛妮:“雷利的母亲要我带去看雷利的坟地,我们走了六小时,她一句话也没有说,等到到了那个小教堂的时候,她看到了坟上的十字架,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辛妮,我踩过线了。”母亲面对儿子的死,是一种巨大的悲痛,而对于曾经的朋友戴米恩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残酷的考验,而“我踩过线”的自责也是对于革命行为的一种置疑,是的,在这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战争中,他们只学会了以暴制暴,只学会了枪杀和报仇,只学会了用子弹击穿敌人的身体。而未来在哪里?在政府让自己变得强大的现实里,还是自由派彻底、纯粹的革命斗争中?
当英国的棕狗子被赶出爱尔兰,当身穿政府制服的军队接管爱尔兰,这仅仅是另一种斗争的开始,或者是另一种宿命的继续,当卷入这无情的战争,必然要泯灭所谓的感情和人性,戴米恩拿起枪对准雷利,和泰迪拿起枪对准戴米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扼杀亲情的暴力,所谓正义,所谓自由,所谓革命,在何种程度上会成为真正的理想?在何种程度上又会制造怎样的死亡?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是妥协还是革命,不管是忠诚还是背叛,其实当田野的风吹来的时候,麦浪翻滚的世界里其实是看不见那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它若隐若现,它时隐时灭,而当子弹飞啸而过的时候,道路上只留下匆忙赶路的脚印,只留下仆倒在地的身体,只留下兄弟反目的仇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502]
思前: 谁在重叠而切割的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