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28《圣地亚哥在下雨》:如何“塑造”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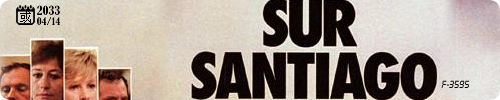
1973年智利发生了“9·11”军事政变,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为首的政府被推翻,皮诺切特成为智利新一任总统。这个1973年发生的历史事件,两年后变成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帕特里西奥·古斯曼导演的《智利之战》三部曲,另一部则是埃尔维奥·索托制作的《圣地亚哥在下雨》。古斯曼和索托具有共同的身份:在军事政变之前他们都是智利国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而在政变之后,他们都流亡国外,古斯曼逃到了古巴,索托则流亡欧洲,而在流亡期间,他们也拥有了共同的身份:电影导演,古斯曼将在政变前后拍摄的影像资料制作了“智利之战”纪录片,向世界公开了智利在极端政治思潮下的这段历史,其中最后记者冒死拍下的政变军队射击的镜头成为了经典,它以“见证了自己死亡”的方式隐喻了“智利之战”的镇压本性。
古斯曼用纪录片讲述历史,这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见证,而索托在流亡欧洲之后根据这场军事政变拍摄了这部剧情片,同样聚焦智利“9·11”军事政变,同样为民选总统阿连德站队,也同样揭露在美国支持下、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反政府的虚伪、血腥,但是剧情片和纪录片的最大不同,它是一种艺术化的再现——就像片名所示,《智利之战》是对历史的描述,《圣地亚哥在下雨》则是一种悲剧诗意的展现,“这是9月11日上午7点12分,春天即将来临,我很抱歉,圣地亚哥和东岛下得雨还是很大……”记者路易斯开车行驶在被坦克占据的大街上,就听到了电台里传出的声音,这就是对“政变日”的一种艺术化注解。当历史在剧情展开中被讲述,也就意味着再现历史变成了“塑造”历史,和纪录片的“记录”不同,《圣地亚哥在下雨》无论是在叙事结构上,还是在画面语言上,更多了一种主观性,而对于事件中的人物表现,则需要更多的典型性。
电影一开始就直接切入事件的中心,军队控制的舰队和美国举行联合演习,由此拉开了政变的序幕,军队首领对士兵们讲话:“我们的军队将再一次在智利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这是光荣的斗争,为了智利光明的未来……”而在街上行驶的坦克向着摄影机开来——这是一个强烈的主观镜头,“开来”预示着军事政变将掀起一场屠杀。索托通过反政府实施行动、煽动卡车司机、利用议会权力等情节展开,将政变一览无余展现出来。而在阿连德和阿连德支持者那里,故事通过塑造不同层面的典型人物进行叙事,第一个层面就是阿连德总统,但是在整部电影中,作为事件焦点的阿连德一直没有正面出现,在政变之前,主要通过阿连德的广播讲话得以体现;9·11当天当军人围攻拉莫尼达宫的时候,政府部门连同阿连德最后只剩下18人,镜头中出现了阿连德,但是依然没有正面,画面中的他拿起了准备好的话筒,向全国发出了最后的声音,他提到了矿产资源的国画化的必要性,提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也提到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的态度,“我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智利万岁,人民万岁,这是我的临终遗言……”
| 导演: 埃尔维奥·索托 |
也许这是索托对典型人物最具隐喻的一种处理,阿连德作为民选总统,作为国家领袖,并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是国家的象征,他是战斗的符号,他是不朽的存在。而对于“政府”这一意象的构筑,索托主要通过奥利威亚斯得以展现,他和阿连德政府部门的其他人一起坚守在拉莫尼达宫,已经好多天没有见面的妻子电话打来,她担心丈夫的安全,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更希望丈夫回家团聚,而奥利威亚斯在安慰妻子的同时,告诉他国家需要他,他还和路易斯见面交谈,认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更是和美国政府进行了国际战争,在收到“雅加达死神”的纸条后,他说:“战斗要开始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路易斯将智利的现状发到巴黎,让全世界知道“智利之战”的真相。最后奥利威亚斯和坚守在此的18人死在军人的炮火之中。在政府部门之外,索托塑造的典型人物,一个是纺织厂的领导何塞,另一个则是学生代表雨果,他们各自代表着支持阿连德政府的学生和工人,雨果的戏份不多,在和何塞接触之后他返回学校组织学生进行了反抗,最后被抓获,并遭到了军人的毒打,最后在唱出党歌“我们必胜”中死去。而何塞作为工人代表,牵出的是“智利人民团结联盟”这条线,这是智力左翼政党选举阵线组织,他们支持工厂国有化,“国有化意味着一切归于人民”,反对美国暗中干涉智利内政以窃取国有资源。通过何塞的回忆,影片回到了1971年5月14日成立时的庆祝仪式上,他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这意味着“工人重新赢得了尊重”,当时的财政部长佩德罗·瓦斯库维克也发表了讲话,大家还一起跳起了“库赛卡”舞蹈欢庆。但是仅仅两年,反政府不甘心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和美国勾结发动了军事政变,在何塞奔赴战场之前,他和妻子告别,和孩子告别,并对孩子说:“你们已经长大,你们是男人了。”那一句“再见了,同志”更是表达了何塞的一种决心。在经历了巷战之后,他们被军队包围,何塞面对他们的机枪,喊出了“阿连德万岁”的最后一句口号。
除了对阿连德、政府高层、学生代表和工人代表的塑造之外,电影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则是记者路易斯,他是“智利之战”的见证者,他更是揭露真相的书写者,在阿连德政府被推翻之后,皮诺切特召开了记者发布会,路易斯作为记者向皮诺切特提出了关于铜矿国有化被废止的问题,皮诺切特则回答说:“这是智利重建稳定经济的一个必要措施。”典型人物串联起“智利之战”,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塑造”,但是这种塑造对于历史的解读来说,容易形成一种单一性,而且在对整个事件的叙事中,矛盾的冲突只是呈现在不同政见者的对立上,缺少进一步延伸的可能,而且这些典型人物最后都在“智利万岁”“人民万岁”“我们必胜”“阿连德万岁”等口号表达中死去。
作为一部剧情片,索托最后依然回到悲剧诗意的表达之中,爱国人士突破军事政府的重重障碍,最终让聂鲁达的葬礼举行,而聂鲁达作为诗人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死是一场阴谋,“他们第二次杀死了他”,但他的死却又代表了智利精神的不死,索托通过这场葬礼,通过葬礼上对聂鲁达诗歌的吟咏,表达的就是正义之声,“那是我们的骨,在死亡之中去寻找你的死……”

《圣地亚哥在下雨》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