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2《裸体公仆》:镜子,以及更多的镜子

这是一部传记片,根据英国最早公开的同性恋者昆汀·克里斯普的同名自传《裸体公仆》改编;这是一部剧情片,由英国著名演员约翰·赫特扮演昆汀,讲述自己作为一名同性恋者的故事。传记片是对真实人物的记录,剧情片则是对人物的再造,在传记和剧情片之间,在真实记录和再造之间,一部电影到底指向什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杰克·高德在电影的“前奏”中就给出了答案。
“有人来找我,对我说,我们想把你的生活拍成电影,我说,是的,电影是幻想,是神奇的幻想,你可以让我的生活成为一种幻想,就像我曾尝试过的那样,但我没有能做到。”把生活拍成电影,就像把昆汀的回忆录变成传记电影,但是昆汀却把电影看成是一种幻想,他所说的就是一种“梦电影”,是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变成了梦工厂,这就是剧情片中必有的虚构。但是即使人生拍成电影也并非是要注入更多的想象,也并非把叙事看做是一种梦,为什么昆汀会如此解读电影?对电影的这种定性意味着昆汀将电影看作是和生活的真实有所区别的存在,也就是说,电影和生活并非是真正的同构,这里就显示出昆汀对现实的另一种解读,“任何电影,即使最糟糕的,至少也比现实生活要好。”这句话的意思不言而喻,现实是现实,电影是电影,电影即使是对现实的再现,也有着另一种美化,也是幻想之作,就像自己曾经尝试的那样,“我生活了66年,痛苦地尝试扮演昆汀·克里斯普的角色,但是我没有成功。”
电影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异构关系,就在于昆汀想要在生活中成为“昆汀”,想要扮演昆汀的角色,但是失败了。杰克·高德用昆汀的这段话注解电影和现实的关系,实际上凸显的是背后昆汀和“昆汀”的角色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带来的问题就是:昆汀为什么不能在现实中成为真正的昆汀?简言之就是:昆汀为什么不能成为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从昆汀和高德不同的视角会带来两种不同的解读,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就是两面镜子。从昆汀来说,自己就是昆汀,真实的昆汀,鲜活的昆汀,活了66年继续活着的昆汀,写作了《裸体公仆》的昆汀,但是当他认为自己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认为现实是糟糕的,生活是痛苦的,一切的原因就在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同性恋者,就在于现实的社会对于他的种种误读和偏见:是娘炮,是性变态,是怪物,是“男性妓女”。
| 导演: 杰克·高德 |
在这里,昆汀和现实的巨大矛盾、对立和冲突,是通过“镜子”得到反应的:昆汀提供了一张照片,一张孩童时的照片,在高德的电影里,这张照片变成了动态图画,那就是年幼的他在镜子前“看见”了自己,他在起舞,他在观察,他在确认,从这面镜子里他成为了昆汀,这就是昆汀作为一个特殊自我所看见的自我意识,父亲责怪他总是在自我欣赏,母亲不解其意,只有昆汀知道,自己是一个被传统道德社会所误解的符号,他只有在这面镜子面前才发现了真正的自己。所以从这面镜子所看见的自己出发,昆汀维护着自我意识,并努力成为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不需要扮演“昆汀·克里斯普”,他就是真实的、唯一的自己。但是家人、朋友和社会,又会如何看待他?他当然没有躲避,而是活在真实的自我中,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力,以更多的行为让自己成为自己。
他第一次走进了同性恋俱乐部,第一次面对镜子描眉涂红,第一次穿上了艳丽的衣服,第一次离开了被传统道德束缚的家,也第一次和喜欢的男人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对真实自我的界定是如此明确:“我不是女人,不想成为女人,我是一个成熟的男性,被其他男人所吸引。”这就是昆汀的宣言,他不会因为自己的特殊性而成为社会接受的男人,更不会因此成为女人,他尊重自己的“性差异”,并在这种差异中呵护着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生活。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当时的社会并不允许他这样的人“成为”一个人,男人们围住他,摸他的手,让他对他们说“我爱你”;警察说他是“三色堇”,并且跟踪他,甚至认为他干着非法的勾当,把他送上了审判席;他被人从酒吧里驱逐出去,出租车他把赶下了车,邻居举报他,在战争爆发服军役检查时,因为昆汀染了红头发而认为他变态,那张豁免书让他远离了战场,却也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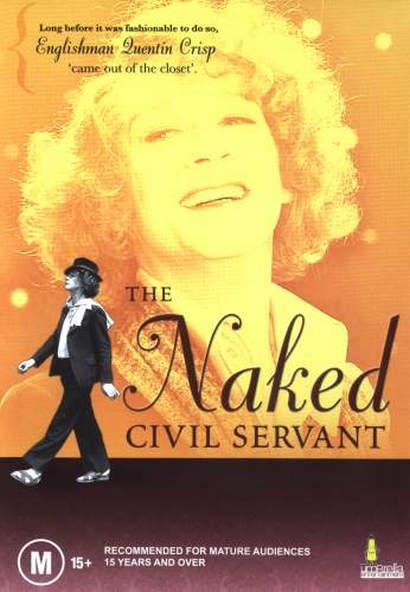
《裸体公仆》电影海报
尽管被人辱骂,被人毒打,被法庭审判,被心理医生诊断,但是昆汀没有成为被社会定义的人,“我必须为此而斗争。”虽然困难重重,但至少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就是镜子中看见的那个自己。所以在这里,第一张“照片”中的镜子就具有了双重含义:在镜子中他就是自己,通过镜子他看见了这个社会的偏见和丑陋。高德通过镜子的双面性透视了那个社会:不仅昆汀自己受到各种非议,遭遇各种痛苦,另外的人也在现实中无法成为自己,那个波兰男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最后只能以上吊自尽的方式结束生命;他心目中“黑暗、伟大的男人”经过他的身边,和他相伴,但都是短暂的,理想恋人最后都成为了泡影;从1939年战争开始,高德凸显了现实中的时间标记,从1939年到1945年,再到1948年,直到电影上映的1975年,数字的背后是对历史的真实呈现,而这种呈现背后是更多的现实灾难。
镜子让他看见了真实的自己,镜子也折射出真实的现实,这就是镜子叙事在昆汀“传记”中的意义,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高德也通过电影这面镜子折射、反射了“裸体公仆”的命运际遇。昆汀处在社会的误读和偏见之下,遭受着现实的“命名”,一方面可以说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昆汀是一名战士,但是无论是社会制造的压力还是昆汀进行的反击,都在非合理系统中构成了一种畸变:昆汀为了证明自己,把社会完全当做了对立面,进行着完全的解构,他认为性是“悲惨者最后的避难所”,他认为婚姻是“给那些放弃奋斗的人安排的”,他不相信上帝不信宗教,他最后甚至拒绝和社会进行对话,“我是英国庄严的同性恋者之一”,他在孩子面前如此定义社会中的自己,然后在高德全景式的俯拍中,昆汀行走在人群中,如此特立独行,而传来的独白是:“我从不看任何人,除非他们要求我看,我永远不和他们说话,除非必须和人交谈。”保全自己,意味着拒绝交流,意味着封闭自我,对于性、婚姻和自我的偏执看法,不正折射出昆汀的一种极端?不正代表着他过于猛烈的反抗带来的畸变?
所以,高德的这部电影也成为了另一面镜子,他让昆汀登场,让昆汀成为自己,让昆汀在镜子中看见自己,而昆汀的所言所行也成为社会的镜子,它照见了社会偏见中昆汀的痛苦、勇敢和自我,也照见了在社会反抗中自恋、偏执、封闭的昆汀,也许,任何一面镜子都制造了一个他者的存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