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12《培根访谈录》:因为我贪恋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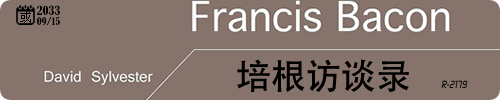
我已经厌烦了自己的脸,因为没有选择,所以只好一直画它。让·科克托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在镜子里注视着死神每天的工作。”这句话就映照出了画自己的行为。
——《访谈五》
自己的脸是1972年的小型双联画《两幅为自画像而作的习作》和直接命名的《自画像》,是1973年同名的《自画像》,是1974年小型三联画《三幅自画像习作》,是1976年和1979年同为小型三联画、同样题目为《为自画像而作的三幅习作》……无论是自画像的习作还是自画像的正式作品,无论是双联画还是三联画,它们构成了弗朗西斯·培根的自画像系列,这些自画像在培根的绘画人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后期出现了增多的迹象,当培根不断面对自己、不断创作自画像,他所看见的是怎样一个变化却让人厌烦、厌烦却依然在关照的自己?
“因为没有选择”,这是培根对大卫·西尔维斯特所提出问题的回答,没有选择而选择面对自己,那个如科克托所说镜子里的自己无疑构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影像,而这也是培根唯一可以看见的自己,也许当培根说厌烦了自己的脸而不得不面对它,在镜子的影像里他每天所看见的是完全不同的自己,镜子成为一种“反映”,也是一种投射,但是对于培根来说,以镜子为影像而完成自画像,那个自己其实已经在对表象的逼近中创造出了一种变形,而且在变形之中赋予了关于自我的隐喻。这样一种对于表象的探索实践其实并非是培根自画像的构建原因,如果说他对着镜子映照出自己,那么他对熟人肖像的创作则以照片映照的方式完成,“你制作的所有造型都有隐喻在其中,你知道的,当你描绘一个人的时候,尝试向他们的表象逼近,但你又想把他们能令你感动的因素把握住,因为每个形体都是有所隐喻的。”
实际上,培根在投入更大经历去完成自画像之前,他就是在画他的朋友,但是朋友并不是以模特的方式站立在他面前,而是以照片,“就算是朋友为我当模特也是一样,我工作喜欢用照片胜过模特,所以我才为画肖像拍照。”他拒绝面对模特作画,而是让他们变成照片,然后对着照片进行创作,培根认为这样工作起来比面对真实的模特更容易,因为面对模特无法自由发挥,“当你面前站着模特的时候,按我的经验来说,这会对你人为的过程加以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培根渴望不受打扰地创作,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这并非仅仅是创作的习惯问题,按照培根的说法,“这些照片常常对我有暗示作用。”当面对的不再是模特,照片其实已经完成了一次影像的构筑,而以影像的方式逼近表象,它为自由变形的展开提供了可能。这就是培根所说照片具有的影像意义,“我发现,照片是个媒介,我的思维通过它能在影像里自由奔走,这比直接观察所感受到的东西要真实得多。”照片不再是参考的物件,而是意念的先导,照片比模特更具有直击心灵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就在于能唤起内心的感受。
| 编号:Y34·2250914·2350 |
照片其实只是影像之一种,培根非常喜欢迈布里奇的摄影集,这是他画作系列的根源,里面展示的各种人体动作构成了培根对人体的透视基础,除此之外,还有那本《X光中的定位拍照》摄影集,里面的X光照片也是人体的影像,它以更真实的方式展现人体的结构;培根在国家画廊看到了埃德加的一幅绘画,妇人在擦背的时候,画面中的脊柱最顶端几乎突出了皮肤,“无论埃德加是否有意地让脊柱突出于肌肉,他的画成功了,因为你意识到肌肉与脊柱基本是在同一时间,而不是他仅把被掩盖的骨头画出来。”图片影像之外,则是电影影像,培根喜欢爱森斯坦的电影,更喜欢那部经典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他的作品《呐喊》就是汲取了电影中妇女呐喊的那个特写镜头,培根一直希望用画作表现人类不含特殊心理学因素的呐喊,但是感觉自己无法达到这个要求,但爱森斯坦做到了。迈布里奇人体姿态的照片吸引了培根,埃德加脊柱突出的画作影响了培根,爱森斯坦夸张而变形的呐喊影像带给培根更大的震撼,这些影像为什么会给培根带来一种自由创作的冲动?
“对我来说,绘画的奇妙之处在于,如何完美地呈现出表象。”看起来这些影像都在变形中远离了它们原本的样子,这并非是培根希望呈现“直接、原始的样子”,但实际上它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更为真实的表象,“对于呐喊,你可以认为它是恐怖的影像;而我想画的呐喊,实际上胜于恐怖。”在他看来,表象可以是图像式的或者是摄影的,但是它们只是提供了一个进入的口子,当画家将影像无限逼近表象时,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内在的捕捉过程,而且是一种非理性、非逻辑的捕捉,“从某点来说,你想要把完全真实的东西用非逻辑的方式做出来,而且是忽然间就完成了。”比如培根总是从熟人影像展现的身体进入迈布里奇的世界,又将迈布里奇的人体用在熟人的身形之上,这是两种过程,第一种过程可以视为对影像的把握,而当迈布里奇的人体用在熟人身形的创作上,对影像的把握已经转变为对表象的表达。什么是表象?培根的回答是:“表象会随着你工作时间的增加,愈让你觉得捉摸不透。”表象是变幻莫测的,是毫无规律的,甚至表象在你把握住影像而转身的那一刻“瞬间改变”,而这种发生在瞬间的改变却能创造出一种“神奇时刻”。
这个过程在培根对于雕像的阐述中更具体地表现出来,在一九七四的第四次访谈中,西尔维斯特就提到了培根曾经有过创作雕像的想法,培根回忆说自己曾经就希望在巨大的机械装置中构建雕像作品,这可以让雕像的位置所以变化,而且还可以制作轨道,材料必须是高度打磨的钢铁,当人没有钢铁也可以用青铜,“我会给它涂上涂料,当作它的皮肤,看上去像是浸过普通涂料、带有沙砾与石灰所造成的肌理一样。”这就是培根想要完成的会话雕像化的打算,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也许人类自古所创造的影像中,最好的就是来自雕塑。”雕像的移动性、运动性、可变性,以及特殊的肌理,都是对平面绘画的一种革新,当然这并不是材料意义的,而是它以一种更具难度的新造型使得影像逼近那个变幻莫测的表象,“事物的解答往往随着难度的增加而变得更有深度。”
影像直接呈现出它原本的样子,在逼近表象中又使得表象变得变幻莫测,培根希望绘画雕像化其实最根本的目的是一种变形中的创造,它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瞬间完成的,而这就是培根在访谈中不断提及的机运,“我总想要通过机运和意外发现表象,然后发展它,创造出其他的新形体。”在开始于1962年的第一次访谈中,西尔维斯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培根在三联画之后为什么开始偏爱有形体的东西?培根将这个时间节点定格在1946年,在这一年的所有创作中,有一幅画留下了深刻印象,培根当时想要绘制的是一只鸟落地的场景,但是当他画出了线条所暗示的东西,忽然就发现了“意外”,“这种思考方式,与我一贯的方式并不相符,而我根本毫无如此作画的意愿。”暗示开始了,它开辟的是一个全新的感觉领域,鸟看起来像一把雨伞,但是这并非真正的暗示,而是整个画作整体的暗示,这幅画三四天便完成了,培根回过头来想到这一事件,认为自己真正想画的就是一些非理性的东西,“从某方面来说,它纯粹就是种意外”。
一方面培根想要画一些东西,是一个预设,它是某种理性的思想,但是在真正作画的时候,最佳状态就是非理性支配下的创作,预设是必然,创作则是偶然,预设是意志,创作则是意外,从预设到创作直至真正完成,这个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是“变形”——培根画作中有各种抽象的变形,但是这种变形绝非是形式意义的,而是一种自由,“因为它有绝对属于自己的生命。”机运是意外,是偶然,是可能性,“它径自活着”,但是如果画家能够将这种具有自己生命的东西捕捉到,这才是真正的创作,“若想要对你所渴求的明确影像进行非理性重塑,且要不落俗套,只有按这个方式来。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我用最不理性的方法做,它能相似到什么程度?这样你就不仅仅是影像重塑,也是把自身理解的各种感觉重塑了。”在这个意义上,机运反而变成了比意志更具有必然性的存在,得到的影像更顺理成章。培根甚至透露他希望自己随时随地拥有一部照相机,“这样,我就能把它放在身旁,可以随时来记录事情的进展”,这样才能将机运捕捉到,但是培根也清楚,这样反而适得其反,因为如果真的把整个过程都拍摄下来、记录下来,但是这样反而就不是真正的捕捉了,记录下来的也不会呈现为意外,在这里培根提出有一种叫做知觉的影像,它就处在自身的结构之中,“当意外的发生促使这种影像开始形成的时候,你的批判能力就要有用武之地了,你开始在此基础之上加以构建,而且通过机运的作用,也许带给你的是一些很有机的东西。”
它是偶然的,更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但是捕捉却是建立在一种直觉意义上的,而这种直觉却是关乎画家的必然性构建,它反而体现了另一种“意志”,是属于“真正的画家”的意志。培根的机运论并非是直觉主义的,而是呈现出一种不被干扰的有机性意志,按照西尔维斯特的理解,“若是让机运工作,就是呈现出更深层次的人格。”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培根的画作为什么要表现扭曲和变形?为什么要创造恐怖的影像?“任何人看了之后,几乎都认为这些情境绝对不是腐朽中性的,画里的人好像陷于未知的紧急状况,也许是烦恼迫人的命运吧。”这是西尔维斯特对培根画作的感觉,他甚至提到了“暴力”,对此培根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小时候与父母相处不好,家庭中也总是充斥着争吵,后来一战爆发,家乡附近驻扎着的就是不列颠骑兵团,培根在真正期间去了伦敦,“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危机感。”十六岁去了柏林,目睹了柏林的城市暴力,后来又去了巴黎,一九三九年战争再次爆发,“这就是我说习惯居住在暴力形式里的原因了,或许这能影响到一个人,也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影响,但我想多半是会有影响。”所以培根认为生活本身的影像就是一种暴力,而自己的作品被认为表现了暴力,那是“因为我总能扯掉一两层的面纱或帘幕”。
暴力是影像,暴力也是表象,培根用自己的画作发展了关于暴力的新形体,这就是绝望,“我这一类的灵魂,是我拥有的一种绝望,也可以愉快地表达为令人兴奋的绝望。”一方面培根在镜子前画自画像,就像科克托一样注视着死神的工作,而且在厌烦了之后还不厌其烦地画,就是对死亡的一种凝视,“生命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活着的时候赋予了它意义。我们以某种态度活着,这使生命有了意义,尽管它本身真的是毫无意义的。”这也就是培根在后期更频繁得推出自画像的缘由,他在“活一天过一天的方式”中,在“一个没有目的的目的”的生命态度中,注视着必然到来的死亡。但是另一方面,活着作为死亡的反面,也是让毫无意义的生命获得了意义,他喜欢艾略特的《荒原》,认为诗歌激活了生命,他喜欢喝酒,在醉酒的状态中抵达自由,他会在过马路的时候往两边看会不会有危险,培根将这一切看做是自己的贪恋,对食物的贪恋,对美酒的贪恋,对喜爱的人和刺激的事物的贪恋,当然还有对艺术的贪恋,这一切也都是对生命的贪恋,“生命是非常短暂的,我希望自己的生命在我还能动、能看、能感觉的时候是充满刺激的。”也正是在这种凝视死亡的必然性中,培根的贪恋反而是为了捕捉生命的机运,“因为若是生命能让你兴奋,那么生命阴暗的一面,也能让你兴奋,比如死亡。”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