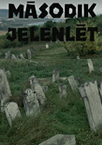2022-08-22《仪容之二》:谁演绎着不变之变

从8分钟到10分钟,从黑白到彩色,米克洛什·杨索时隔13年之后拍摄的《仪容》第二部,已经在形式上赋予了一种影像之变,而这种变化或许是外在的,当深藏在历史深处的“仪容”被现实看见,它是变,它也是不变,它更是不变之变。
被改变的是外在的环境,1965年还残存着战争记忆的火车已经远去,1978年驶来的火车装载着货物,装载着乘客,它已经变成了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一列火车疾驰而过,再一列火车疾驰而过,又一列火车疾驰而过,三列火车形成了关于现代社会的一种集束,它驶向远方,甚至驶向了可以遗忘历史的远方;还有从废圮的那个窗口望出去,是一根竖立的烟囱,在近和远构筑的视角中,烟囱的背后是建立的工厂,是工厂代表的工业,它们和呈现集束状的火车形成了一种呼应:这是属于1978年的时代元素,它必将使得这一处的废墟慢慢在时间中湮没。
| 导演: 米克洛什·扬索 |
被改变的当然还有里面的一切。从小镇那条路上通向教堂的门已经被水泥封住,只留下了三级台阶,台阶再没有进入的入口,它变成了历史的残留物;从另一扇门进去,走上二楼的楼梯也没有了,约柜也被封掉了;窗户残存着,风吹进来,连曾经的经书也只剩下了几张散落的纸,在风中渐渐飘散,就像历史的文本,一切都已经残破。
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陈设,都已经被改变了。但是沧桑没有改变,沉寂没有改变:小镇出奇地安静,几乎没有行走的人,晒着的衣服在风中摆动着;墓碑上的字没有改变,破损的石碑没有改变,四周的杂草没有改变——和历史、和记忆有关的“仪容”没有改变,13年过去了,一切还是一如既往地萧杀,是不是作为历史的残留,不变也是对历史不会改写的态度?
不管是变与不变,其实对于这一处的废墟来说,杨索在影像的记录中透露的情绪是哀伤的,但是一切的变与不变转向另一种时间的时候,却成为了不变之变:一个孩子独自在废墟里玩耍,没有同伴,没有朋友,他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中,即使是一种虚无,也代表着一种存在,而废墟里的那个红色自行车轮子,正是另一种游戏的存在证明:有人在这里寻找快乐,寻找独处之道,至少它不再是一种死寂的存在。之后走近来两个男人,他们穿过那道门,他们站在约柜的遗迹前,他们披上了诵经的披肩,他们点起了蜡烛,他们默念着经文。一种声音出来,和1965年打破沉寂的声音一样,它是活着的象征,它是信仰回归的证明,而且,它在变化中被赋予了使命感:和13年前的两位老拉比相比,1978年的两个诵经的拉比更为年轻,时间以一种逆向的方式发出声音,这是真正之变,它是更大意义的唤醒,它是更重要的复活,它甚至是信仰不灭的证明:经历了战争,经历了沧桑,经历了颓败,但是内心的那种力量一直存在,它以更鲜活的方式面向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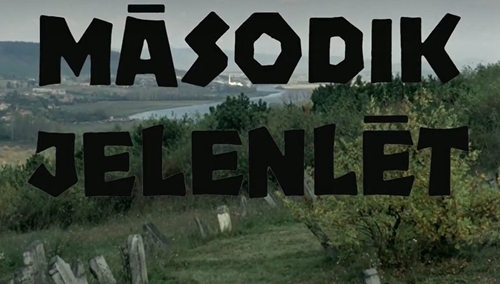
《仪容之二》电影片头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