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01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毒死一个希望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不管如何崛起,黑暗总在那里,并且作为时代和背景永远存在。一个人的黑暗,一群人的黑暗?还是象征的黑暗、虚构的黑暗?其实对于没有前传没有之前故事开启的黑暗,只是无数个现实的白昼之后呈现的一种夜色而已,所以,如果一开始就被切入克里斯托弗·诺兰三部曲的最后一章,在没有“前传”开始的现实黑暗中,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在直接送到了那个陌生而奇妙的世界,当真正看见四周的黑暗,真正被164分钟的电影所“劫持”,世界的黑夜,只不过是一个进入的理由。
现实一种,起源于黑暗的来临。8月之末9月之初,国产电影保护月的结束,仿佛结束了女体的每月之经历,世界洞开了一个呼吸的理由。所以在对于《蝙蝠侠》系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选择用一部电影来结束这种仪式感极强的承上启下的日子。一家人的选择就在这半是虚拟半是现实的“蝙蝠侠”,小五问,真的不是动画片?我在问的是,为何它是系列为何没有前戏依然会有未知的诱惑?黑暗中的神迹,蝙蝠侠是正义,是力量,还是一个图腾?不是动画片的意义或许在于: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一个有着欲望和希望,以及失望和绝望的人。当这种漫无边际的想象在电影之前被狠狠刹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提前进入了电影世界的某种哲理主题,我承认这是观影之后再回到最前所犯的“后入为主”的错误。那么单纯回到时间的秩序中,在电影之前,从城西的比高开始,遭遇大面积堵车、抢车位、拥挤电梯以及排队买票之后,那种超越我想象的嘈杂立刻成为到达电影黑暗之前最无力的反抗,而最为可悲的是,在长达半小时折腾之后,等即将获得买票资格的时候,才知道所有电影都是英语原声,这是一个未知的陷阱?英语原声对于小五来说,肯定没有动画片这种属性电影带给他的画面理解力,蝙蝠侠一定是属于成人世界的游戏,对于孩子来说,那可能真的是一个黑暗世界。
现实一种。离开原声电影,其实也是离开不属于我们的黑暗。而在再次奔波半小时之后,从城西到达城东的影视城之后,才看见了中文译制过的版本,两个黑暗世界,语言是一种媒介,它属于不同的年龄世界,我们的和小五的,而在中文的电影里,同样的黑暗,对于一个不认识所谓的正义与邪恶,谎言与真理,肉体与精神,恐惧与虚无,社会与秩序,以及爱与行动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是可以解读的?仅仅是蝙蝠侠的头盔、盔甲、披风、蝙蝠车所构筑的强大虚幻?还是“到底哪个是蝙蝠侠”的身份疑问?这一切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悬疑,都是身处在影院黑暗中的一种本能疑问,或者,都是现实白昼之后对于辽远而神秘的黑暗世界的极度不适应,那么好了,就让小五睡去,在非私密的空间里像回到温暖的床上安静地睡去,而留下的只有那个没有前传,没有前戏的真正黑暗帝国。
“你是躲在黑暗中,而我是生活在黑暗中。”这是两种不同的黑暗,之于蝙蝠侠和贝恩,这一场两个人的打斗的戏,其实是关于人生哲理的大讨论,或者说,这才是真正进入黑暗世界的入口。下水道,邪恶,死亡,对于哥谭市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黑暗世界,是地上那个看起来光明和秩序井然世界的对立,就想那个无底监狱,没有人能逃离到上面的世界中去,虽然能看见那井口的光明,作为希望的一种,它永远存在,但却永远无法企及,几乎无人能从这所黑暗的监狱中逃脱。而在大反派贝恩的这个地下世界里,所谓的秩序就是毁灭地上的文明,毁灭那一套的公正秩序,以及毁灭城市自身。而作为正义的代表,蝙蝠侠的符号意义就在于打击犯罪,摧毁贝恩一样的邪恶帝国。
但是,地上和地下,正义和邪恶,到底在什么地方有过分界?正义者是警察?八年前,就是警察局长戈登为了维护警察所代表的正义和秩序,用谎言把公权私用、为所欲为的警察登特树立成因公殉职的英雄形象,以安抚哥谭市民,而“蝙蝠侠”成为那个牺牲者,承受起破坏城市治安的罪名。在这种正义的秩序中,蝙蝠侠也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工具,那么正义是不是就是从一个符号变为另一个符号,而社会的秩序永远掌握在有产者、有权者手上?大反派贝恩发动的暴民革命,除了要建立自己的秩序和规则,摧毁被权利和谎言绑架的腐朽的哥谭市,另外,当然要在这种破坏中重建属于自己的秩序,使自己成为“影武者联盟”的领导人。一种秩序对另一种秩序的代替,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颠覆,所以,不管是警察为首的国家机器,还是以贝恩为首的反派,都只是为了一种统治,一种革命暴力下的新法则。
革命,当然是放逐之后的选择,对于贝恩来说,是重返“影武者联盟”的开始,而在另一种放逐中,蝙蝠侠从来都是为了某种正义而牺牲自己,包括八年前的“背黑锅”,牺牲自己就是牺牲传说中的那个符号,符号是可以消失和重建的,所以在蝙蝠侠身上,从来就有“被符号化”的悲剧,头盔、盔甲、披风、蝙蝠车,他从没有真相示人,在他看来,是为了“保护自己身边爱你的人”,但其实这是所有符号的特性,在能指中丧失真实属性,八年前为了利益蝙蝠侠消失,而八年之后,当新的利益诉求出现之后,蝙蝠侠也必须出现,这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在《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中,克里斯托弗·诺兰选择了开始了蝙蝠侠“去符号化”的努力,这种努力是痛苦的选择,或者是重生,或者是死亡,而真正的救赎,便是让那个在危难时刻出现的“蝙蝠侠”,脱去神的外衣,而返回肉体的人,真实的人,痛苦的人,甚至是伤病和失败的人,他的名字叫布鲁斯·韦恩。
从蝙蝠侠到韦恩,并不是简单的名字变换,对于这样的放逐和救赎,充满了痛苦和失败,沉寂八年,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他筋骨不会如以往敏捷,也就是说他尽管披着蝙蝠侠的一切装备,但是力量、勇气、智慧都在衰退,这种衰退正是蝙蝠侠武装之下的那个肉体的衰退,作为一个人的衰退,当管家含泪告别布鲁斯·韦恩,或许就是这种衰退必须经历痛苦的开始。是的,在与贝恩的正面交手中,蝙蝠侠已经明显处于下风,甚至是失败,他们的格斗就是一个英雄神话的破灭,贝恩打败了蝙蝠侠,也是打败蝙蝠侠所代表的那个符号,失败和痛苦,只属于面具之下的那个人。而在无底监狱里,布鲁斯·韦恩完全没有了蝙蝠侠的装备,也脱去了那个符号,他属于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躲在黑暗中”,充满着向上的希望的人,但是这样的“去符号化”仍然是不彻底的,贝恩说,只有真正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才会打败你,也只有绝望的人才会消灭所有的希望。也正是由于布鲁斯·韦恩还有蝙蝠侠的影子,还存在诸多的希望,甚至还有对死亡和城市灭绝带来的恐惧,所以他无法超越自己,那条力图走出无底监狱的绳子或许也是一种象征,看上去是一种解救的方式,但其实是束缚,是羁绊,也是符号,因为它,所有的逃亡都以失败而告终,而多年之前的那个雇佣军的孩子,就是在没有任何绳子的情况下,逃离了这个无底监狱。
当他用日复一日的康复还原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当他最重放弃绳子徒手攀援而成功逃离监狱的时候,蝙蝠侠才被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才最终摘掉了那个戴着的神话符号,而关于黑暗,关于恐惧,关于死亡和拯救,都完成了一次重新的命名,蝙蝠侠的复活完全是一次超越,“人人可以成为蝙蝠侠”正是完成了最后的救赎,只有成为真正的人,真正去符号化的人,才可能面对黑暗,面对自我,面对爱和欲望。而站在对立面的贝恩,从黑暗中来,用他的革命和暴力帮助蝙蝠侠完成了救赎,但是他却还戴着管子面具,这或者也是一种身份的隐匿,但面具本身也完全成为了一个符号,所谓的革命,所谓的权力,到最后也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同样是面具,一个是救赎,一个是沉溺,而最后,当蝙蝠侠再次回来的时候,贝恩革命般的颠覆也走向了末路。甚至到最后死的时候,也不知道管子面具背后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不一样的面具,是不一样的黑暗理念和自我意义,而在蝙蝠侠和贝恩的面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面具,那就是米兰达。作为一种拯救计划的有钱人,她几乎从一开始就在道德和良知的高度上,甚至最后也变成了贝恩团伙向高谭市的旧秩序绑架的一个人质,直到最后蝙蝠侠回归,找到了贝恩面具里的秘密而置之于死地的时候,峰回路转,或者那种戏剧性出现了,米兰达其实才是真正从黑暗中逃亡的那个孩子,那个背负着父亲的使命而掀起城市革命的真正主谋。她藏在巨大的面具之后,所有的观众都会被欺骗,这是克里斯托弗·诺兰最后的高潮,还是一个单纯追求戏剧效果的败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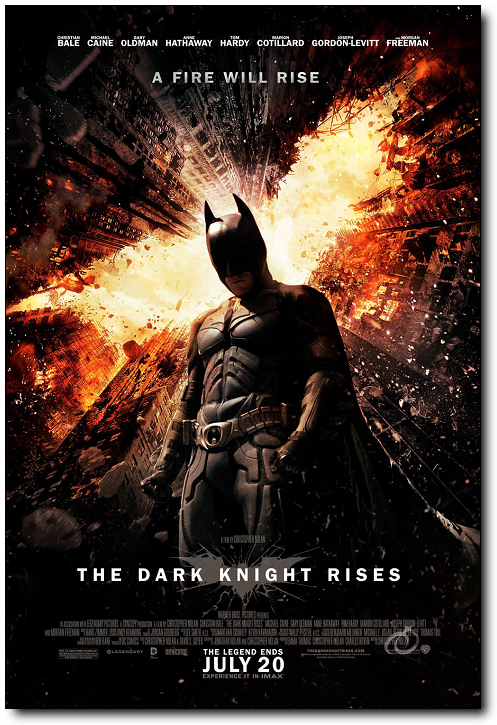 |
|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海报 |
从电影开头贝恩劫机开始,“大反派”已经成为了写在他面具上的一个符号,以及力量、勇气和人生理解的透彻性理解,都使其成为一个在“出生在黑暗中”,以绝望换取希望的大魔头,而最后他用炸药爆破哥谭市的段落,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人间炼狱的降临,他摧毁了蝙蝠侠的符号帝国,摧毁了社会秩序,甚至摧毁了文明和规则,但他却不是真正的黑暗骑士,不是那个从黑暗中唯一逃脱的幸存者和报复者。米兰达主动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摘下面具的方式是一把利刃,以一种穿透身体锋利刺进了蝙蝠侠的肉体,而这个肉体在那个雨夜,成为他们性爱生活的某种见证。
为什么米兰达要成为那个唯一的逃亡者?为什么她才是最后戴面具的人?她主动暴露身份直到最后喊着口号般为父亲报仇,都只是为了剧情更多看点而已,缺少内在支撑的逻辑主线,蜘蛛侠的回归是在贝恩的革命计划之外,贝恩节节胜利,而米兰达一直落在贝恩的手上,如果按照这样发展,那么米兰达永远无法告知观众她的真实身份,也只有等蝙蝠侠“去符号化”的回归中打败了贝恩,才得以使米兰达成为一个设计好的角色。
如果真要为最后米兰达的真实身份的揭开找到剧情的需要,那就是对于爱的阐述意义。米兰达和蝙蝠侠的一夜情缺少真正的爱,这是不是也是米兰达身上永远的劫?她的出生是爱的结晶,却是带着父母的离别和痛苦,那个雇佣军为了心爱的女人,被沉到无底监狱,而心爱的女人用自沉监狱的方式,换取了他的的自由。米兰达就出生在无底监狱,对她来说,世界才是真正的黑暗,黑暗中的爱是没有永恒的,只有逃离,只有亡命,也只有被欺骗被摧残,所以在那个雨夜,和蝙蝠侠的爱欲也只是黑暗中的肉体之欲望,甚至生火也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对爱的否定和背叛到最后是以一把刀子的方式呈现,这是面具下真正的黑暗世界,而“去符号化”后成为一个具体的人的蝙蝠侠最后却得到了猫女的爱,这是一种爱的还原,也是一种爱的超越,“人人都可以成为蝙蝠侠”在这种爱情之下变成了两个人的事,变成了更多人的事,而蝙蝠侠最初的疑问“一个人该如何改变世界”也便有了最后的答案。就像贝恩曾经说过的话,只有完全在绝望中才能拥有最后的希望,而曾经的希望都会变成绝望,套用《玫瑰的名字》的那个“毒死一个修士”的咒语,其实电影也在传递着如何“毒死一个希望”,当希望变成零,变成自己需要创造的东西,必须从绝望开始,从没有绳索的逃亡开始,从一场一夜情的背叛开始,也从战无不胜的蝙蝠侠走下圣坛开始。这种颇具禅理的主题就像《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里说的那样:“报杀兄之仇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抱这个人,拥抱他而又拒绝把他企图在她身上找到的爱情献给他要把他拖死,把自己的苦水一一挤出来,变成毒汁,把他毒死。”
毒死之后的重生,就是蝙蝠侠的回归,克里斯托弗·诺兰用他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帝国的覆灭和崛起,从《黑暗骑士》到《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克里斯托弗·诺兰用了四年时间,而从2005年第一部《蝙蝠侠:侠影之谜》开始,三部曲已经走过了漫长的七年时间,这时间几乎等同于蝙蝠侠背黑锅的八年,这是一个执着的导演,《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也没有拍摄成最流行的3D版,诺兰从来反对3D,这是他蝙蝠侠电影的底线。运用IMAX摄影机进行拍摄,也是克里斯托弗·诺兰“去符号化”的一次实践。他让蝙蝠侠走下神坛,那墓碑上刻着蝙蝠侠最后的名字:布鲁斯·韦恩,是的,这就是真正作为一名导演真正在寻求的价值和意义,宛如信仰。忠实的管家阿尔弗莱德最后在福罗伦萨的咖啡馆里,抬头看见了蝙蝠侠和猫女在他的对面喝咖啡,浓浓的希望复活了摘掉面具的英雄,蝙蝠侠没有死?是的,当中子弹远远地爆炸在海湾里,你只是观者,你不在现场,故事从来都有复活的可能,而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个蝙蝠侠到底有没有死都不重要了,“人人都是蝙蝠侠”,那么,人人都不戴面具,人人都找到了自我,人人都有了爱情。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