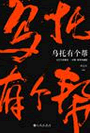2014-01-08 《乌托有个帮》:人生辽阔,就这么一意孤行

妹妹,你的咪咪很大,它比我的理想大
我说妹妹,我的理想很大,它比我们的未来大”
——李志《暖昧》
理想比未来大,咪咪比理想大,所谓覆盖,只是一只手的大小,只是一页纸的厚度,只是一个暧昧的表情,只是文艺的碎碎念,所以,即使我们说好了不回头,说好了一意孤行,我们还是在走出一段距离后回望我们的人生,回望那比理想大的咪咪,回望没有未来的现在,人生辽阔,所有的大都是小时代,所有的路都是断头路,所有的理想都是现实,都是眼泪和伤口,都是一事无成的青春,都是鸡飞蛋打的中年。
是的,已经进入了鹦鹉史航的“流动的盛宴”,那个海明威的系列故事已经将浪漫变成了浑身的小伤口和一个星期的胡桃汁脸,在“都值得回味”的浪漫中,付出的代价或者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理,甚至是那个比理想大的咪咪,而在我们手中,有时候握着的不一定是暧昧,是厚实的书,是被鹦鹉史航称为“慈悲的仓库”,或者是“游戏里神奇的空间戒指”。黑色,并不是永远的黑色,覆盖也并非是一页纸的覆盖,泼墨的字体,透明的腰封,它破解的是一种“密集恐惧症”,它说:“引导一切精神享乐”,它说:“献给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它说:“乌托有个帮”——里面是彩色,里面是丰富,里面是暧昧的暧昧,里面是文艺的文艺。“生活中很多种方式任君选择,不管红绿黑白。”又回到李志的“暧昧”,只是这一次他指向的是一次定格,一个态度,一种决定:“或者你可以选择认真做本杂志。”
|
| 编号:Y79·2131219·1034 |
还有什么是可不说的暧昧,还有什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还有什么是鸡飞蛋打的理想?“她们视我为异类,只是因为我不屑于掩饰我的轻蔑。”这是话剧《柔软》里的一句台词,而在郝蕾的解读中是保持真我的状态,一种“如是”的生存境界,从音乐、电影、戏剧到绘画、摄影、文学,在文艺的乌托邦里永远住着现实之外的异类,住着不屑掩饰轻蔑的异类,而它的同义词就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理想这个东西一直存在,足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可能年龄越大,就越不好思跟别人说起自己的理想。但幸运的是我生活在北京,这里有很多跟我一样,在而立之年还为的音乐理想而奋斗的人,你不会感到孤独。”这是郝云的一句话,这位被称为“脚踩大地头顶蓝天”的北京爷们儿用接地气儿、本土化、人情味儿的创作风格来表现自己的生活状态,这是摸得着看得见的理想,所以即使他说“我想四大皆空,我还想大闹天宫”,到最后还是会到脚踩大地头顶蓝天的现实中。
2010年郝云是“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其实理想一直在心里,在温暖和幸福,是发现自己的存在,林奕华在《贾宝玉》里就表达这杨的观点:“《贾宝玉》对于我来说,都是关于‘灵性’,是一个人可以找到的自己的终极价值。”自己的终极价值或许就是生活本身,但是灵性总是被尘土被世俗的欲望覆盖,被时尚潮流所淹没,而那些属于自己的存在声音就微乎其微,甚至已经销声匿迹,“很多人现在不懂得关心自己,他们只是宠自己。”所以林奕华的self-reflection才认为是电影或者戏剧“最被需要的境界”。
欲望的投影无处不在,它是我们不认识的自己,是异化的自己,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二手玫瑰”所表达的叛逆性和所坚持的原创性,这个从东北二人转发掘题材,从底层叙事和传统曲艺吸收养料的乐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从那天起,我不想在空中瞎飞,我要双脚落在地上,回到民间的血液里。”而这种“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调戏现实,娱乐观众的一种反应,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理想“往幼儿园里开”,成长出纯洁的花朵,所以“二手玫瑰”是一种拒绝,是一种反讽:“二手是个反讽,想要表达当代艺术许多许多都是复制和抄袭,而我要做一手的艺术。一手的意义就是原创,就是讲述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的生活,就是民族性,就是创新的源泉,多简单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许多玩音乐的人就不明白。”不明白的创作中有太多的复制,太多的西化,太多的“二手玫瑰”,所以怒放就应该是生命的原生状态,是自我的自然表达。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郝蕾要在近六十度的高温中重走佛陀成佛讲经的地方,为什么丁武要从梦中寻找音乐的灵感用绘画投影“出事儿了”的生活,为什么曹方听到极远处传来太阳鼓的声音会“莫名地被指引去走近它”。那是对自我的找寻,而这种找寻必须和现实进行对抗,必须让理想的玫瑰开出芬芳,那个挪威礁石上的字母A,是曹方遭遇的尽头,字母头上的圆圈是句号,象征着陆地的戛然而止,但是陆地之后呢?挪威之后呢?旅途之后呢?从行为方式变成艺术方式,或许也是一次超越,一次对理想的坚守。
从寻找自我到返身到艺术,这本是不可分割的过程,人生即艺术,艺术演绎着人生,HAYA乐队的名字里包含着“边缘”,但却也是从边缘中挣脱束缚,超然物外,它是融合万物的宝石,它将爱充盈真个世界,所以HAYA乐团要踏上迁徙之路寻找艺术的宝石;所以谢天笑要用柔似流水的古筝和密如雨点的Reggae相融在一起,寻找中国摇滚的突破口;所以赵淼要从《聊斋志异》的水鬼主题和傩戏的演剧方式中找到中国戏剧的另一种“形体”……张玮玮的牢歌收集、林怀民的“云门”舞蹈、徐昂的忧伤喜剧,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在创造着艺术,在坚持着理想,或者正像孟京辉所说:“表现人类应该表现的。”
而这种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盛开一束束的玫瑰,可以成为一个人引领的风景?似乎包围在外面的永远是逃避不了的中心,似乎永远是纷纷扬扬的碎片,孟京辉对先锋姿态下的定义是:“有一种曲线,它永远想要接近X轴,但永远接近不到,我觉得这就是姿态,一种趋向,一种美学观念,一种身体力行的东西。”是的,他们制造了趋向,他们表达了观念,他们身体力行,但是他们想要接近的X轴,却永远不能抵达,或者说,只能是无限接近,但不会是重合,文艺的尴尬或许也是如此,在众多自我的坚守和拯救中,往往会忽视那条曲线的指向,或者会误解那条无限接近的X轴。“二手玫瑰”在《征婚启事》中唱到:“混到了北京我混没了牵挂,混乱了生活我混长了头发,到底是什么让我无法自拔?”而这似乎解构着那些怀揣梦想的人,或者对于19岁那年的谢天笑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个体的反讽:“从淄博一路北上,追随崔健、唐朝和黑豹留在他印象里的痕迹来到北京”是不是所有文艺青年的必由之路?那个“北京”是不是也有黑暗之光是不是也在改变梦想:“这瞬间被建立的城市/是谁梦中片刻的意志/形状如此真实/回忆如此虚伪/你摧毁她经历的世界/或探索她已展开的边界/清晨苏醒之后/她已有了改变(雷光夏《她的改变》)而HAYA想要“唱给在城市中失根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些在“中心”湮没自我的人?
这是不是只是一个属于艺术的传说,一种神话,一个“天方夜谭”?“当‘文艺’染尽了坏名声,当传统媒体在衰退,当碎片式的新闻占据了人们日子里的边角余料,当‘审丑’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题,我们却两手空空得要把一个贴着‘文艺’两个大字、提倡深度阅读和精神享乐的杂志做起来。”这是写在《致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的碎碎念》这篇“后记”里的一段话,文艺沾染了坏名声,碎片式的解读占据了生活,审丑变成喜闻乐见的话题,在这样一个大众阅读的时代,艺术的传说,文艺的革命,以及理想、信念、激情、自我又去了哪里?所以提出任重道远的“解救”意义变成了一本书的职责,或者也只有一本书,才可以让人民大众抛弃碎片抛弃审丑抛弃那个比理想更大的咪咪。因为文艺是遥远的,深度阅读是遥远的,精神享乐是遥远的,它只属于那些行走在路上的“乌托有个帮”。
3年,100期,这是一本书的时间轴线和周期指数,但是不论是人物专访、LIVE,不论是Focus、看艺术还是艺述,几乎所有的篇章都以时间和地点作为标签,以及“记者某某”的观者标签,这些标签象征着时代性和现场感,2011年3月12日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的Eaqles 2011北京演唱会、2012年8月31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音之印象”音乐周、2013年1月12日北京·后山艺术空间的野孩子腊月音乐会,以及那些集锦式的各类音乐节,在图片的传递中并没有让人产生身临现场的快感,相反倒是感觉自己距离所谓的“文艺”越来越远。在一个大多数人生活的“非中心”的城市里,没有音乐节,没有摄影展,没有戏剧演出,所以从来没有艺术的现场体验,没有激情、疯狂、融入。而对于我来说,在这本“文艺红宝书”里,所检索到的和我有关的相关信息只有:郝蕾或者娄烨的《苏州河》、《颐和园》;不在书店里恶鸟的实验小说;放到网络上的孟京辉戏剧《恋爱的犀牛》以及去年曾有过某种臆想的乌镇戏剧节。
而其余所有的一切都是遥远而陌生,都隔着厚厚的玻璃,都是一个“天方夜谭”,艺术在别处,艺术高高在上,所以注定是“乌托有个帮”的群像,而那种渴望抵达”深度阅读和精神享乐“也只是一个不断被侵蚀不断被异化的的杂志理想,那些标注着记者的署名文章只能证明它是一本报道集,一本有关新闻的碎片化组合,甚至只是一本缩小了的杂志,它不是如丁武所说具有宗教意义的“图书”,所以在Focus中,那个关于大爱音乐节的报道在讲述圆满的梦和破碎的爱,更多只是在描述音乐节本身,“前所未有的豪华阵容,难以置信的舞台音效,以及细致入微的人性设置,都让习惯了国内音乐节标配的乐迷为之惊喜”,它所带来的却是“第三天工作人员罢工演出延迟开场,到音乐节结束后酒店追讨房费员工纷纷逃跑”,或者更多的只是报道“从大跃进到大逃亡,从捧上神坛到跌入谷底,短短四天辉煌带来无比沉重的代价”。其实,作为深度,并不能局限在音乐节本身,“2013年的音乐节更加层出不穷,音乐节市场被红了眼的人们越炒越热,突然热起来的市场也带来了迅速成长所必经的阵痛,重复的阵容,疏松的管理,随之而来的是票务漏洞、艺人与主办方的冲突、乐迷的审美疲劳……”这一句或者才是解剖的要点,但可惜只是一笔带过,无法完成Focus的深度挖掘。
而在《艺述》的不部分章节中,除了缺少深度,甚至还只是一种知识的普及,在《香港电影MOVIE in H.K.》文章中,参考“香港星光大道官方站点”的《香港电影发展历程》就是知识的传播,而接下去关于Made in Hongkong的新浪潮,也只是简略介绍徐克、许鞍华和谭家明三个人的电影,#港味影像#更是将香港电影的解读变成了碎片化的100条微博介绍,最后《我与香港电影》的采访是文周和飞鸟的对话,而飞鸟作为豆瓣小站“香港电影的电光流影”站长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至少在采访中,对话也仅是从关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香港电影、最喜欢或最怀念哪个时期香港电影、怎么看待香港电影新时代的没落期、最喜欢哪些香港影星这些简单的话题,根本没有在深度上去解读香港电影的发展脉络。
“幸福只有芝麻大一点,我奔走在它的边缘……”这是张浅潜在《幸福的芝麻》里唱出的心声,芝麻大的幸福对应的是咪咪大的现实,奔走在边缘对应的是主流和中心,“《文周》三年来采访过的人,大都注重自身专业领域的探索而隔离浮华。他们钻到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里,与这个有些坏的时代周旋,那其中的苦与乐,是一般人根本无法体会的私享幸福。他们生活在成人和孩子中间的青涩地带,渴望分享、渴望自由。正是这些人,让这个充满了悲观和负面情绪的世界,多了一些让人热泪盈眶的理由和干净的存在。”这里是有对于理想坚持的感动,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实践,有激情,有自我,但是“致所有在边缘的理想主义者”的后面是挣扎,也是无奈,对他们来说,现实或者也是一种无法逃脱的桎梏,而在这样一种芝麻大的世界里,所以他们拒绝中心却在抵达中心,他们远离碎片却在制造碎片,“战争中你鲜血流尽,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其实,做一个平静的人,写一本平静的书,更难。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421]
思前: 《小城之春》:城头上的变换人生
顾后: 极端是个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