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08 《卡萨布兰卡》:永志不忘的革命浪漫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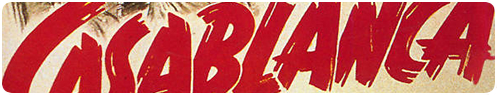
——你昨晚去哪里了?为何不来找我?
——我不记得那么久以前的事。
——那你今晚会来吗?
——我从不想那么远以后的事。
以前和以后,都在遥远的时间里凝结成一种回忆,是重温的经典还是被遗忘的伤感?巴黎在哪里?卡萨布兰卡在哪里?里斯本在哪里?只有力克咖啡馆的黑夜漫漫无期,爱情是不是也像艰苦迂回在逃离路线上的那些人一样:等待,等待,再等待。
“现在是1941年12月,自由睡着了,美国人睡着了。”而醒着的是那个叫力克的男人,和他所开设的咖啡馆一样,中立,抛开政治,这里既有德国少校,也有法国上尉,还有形形色色来到卡萨布兰卡,又想办法离开卡萨布兰卡的人,他们在这里探听消息,等候班机,甚至在夜总会酒店的外表下,藏着赌场、黑市买卖、各种阴谋伎俩,甚至还有个革命领袖。力克已经是个一“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他不关心政治,不关心谁是侵略者谁是反抗者,他面对的是一个金钱、消费、赌博、美女的世界,但是那晚,他喝着酒,痛苦地埋下头,酒杯被打翻,而背景音乐是山姆弹奏的那首熟知的《时光飞逝》(As time goes by)。
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突然出现,毫无预兆的出现,对于力克来说,注定是毫无设防的。就在黑夜之前,这里只有中立的力克,只有喝酒却不对女人感兴趣的力克,但是伊莎出现了,一同出现的还有伊莎以前,也是现在的丈夫拉斯路,而伴随他们到来的,还有那缠绵的《时光飞逝》钢琴曲。伊莎先是认出了山姆,央求他弹一曲《时光飞逝》,在音乐声中,她似乎想到了久远的过去,以及久远的一个人,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是26秒的长镜头,比音乐更缠绵,更伤感,因为她也知道,这不期而遇的咖啡馆里注定会有一双眼睛和她相遇,再也逃脱不了。
力克和伊莎,他们的相遇在巴黎,他们的过去在巴黎,他们的爱也在巴黎。那是战火中的巴黎,那是即将被德军占领的巴黎,那是她以为革命的丈夫牺牲的巴黎,当然,那注定也是一个“永志不忘”的巴黎。他们相遇而相爱,他们是战友,是对于纳粹战争的抵抗者,他们在并肩抵抗中说:永志不忘,而当德国占领了巴黎,对于他们来说,命运必须使他们离开巴黎,那时,他们相拥、接吻,他们又说着那句:永志不忘,而背后是德国的坦克、飞机,以及失陷的巴黎。
在战争中,任何美好的东西都是脆弱的,包括爱情。伊莎说:“这世界快倒下来了,而我们却挑这个日子谈恋爱。”爱情生不逢时,却无法阻挡。他们痛恨战争,痛恨这“疯狂的世界”,但是对于那种脆弱的爱情的守护,似乎只有一种选择:一起离开巴黎。或者这是一个向着美好结局进发的故事,但是正如力克所说:这故事的结局根本没有汽笛声。四点四十五分,这是他们相约离开巴黎的最后一趟火车的时间,雨夜的马赛火车站显得拥挤和混乱,当力克和山姆在站台苦苦等着伊莎的到来时,他们最后等来的是一封信:“我不能和你一同走,也不能和你再见面了,你一定不要问为什么。只要相信我爱你。”雨点打在信纸上,字迹模糊了……
 | 导演: 迈克尔·柯蒂斯 |
 |
但是,这就是宿命,“世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有那么多的酒馆,她却走进了我的。”伊莎来到了卡萨布兰卡,来到了那个结局“没有汽笛声”的故事中,她像被置换了的一个记忆零件,她是有丈夫的人,地下革命者拉斯路,马赛火车站的失约是因为发现丈夫并未在集中营死去,他只是受伤了。伊莎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对于她来说,这不仅是她对于感情背叛的弥补,更在于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要从卡萨布兰卡逃出去。而在力克咖啡馆,德国人已经发现了他,并且要将他逮捕。
相遇并不是爱情之火的重新燃起,伊莎说:“我们记住的日子,不是卡萨布兰卡,也不是今晚。”而是那个巴黎,久远的巴黎,“永志不忘”的巴黎,以及肝肠寸断而未能同行的巴黎。“我们永远拥有巴黎。”是的,对于那场背叛的爱情来说,巴黎是个过去式,是个错误,而来到卡萨布兰卡,甚至遇到力克,也只是为了那封戴高乐亲笔签署的过境信函。这信函是革命的希望,是战斗的希望,但是在力克身上,只有他能给伊莎和拉斯路离开的希望,但是对于力克来说,巴黎的雨夜永远是一个伤感的回忆,他的爱已被埋葬,他的革命也已经被埋葬,“我不再为任何事战斗了,只为自己。”他说。
在爱情面前,革命是不是只是个借口?当爱情泯灭的时候,革命是不是也会成为无意义?而当伊莎的眼中含着泪水,当“As time goes by”不断地想起,当那么多的酒馆伊莎偏偏走了进来,力克内心的声音慢慢被激活,当伊莎用“一个女孩伤害了你,你却要报复全世界”来诘问力克的自私的时候,力克冰冷的外壳被融化了,感情的伤害已经不堪一击,当德国人在咖啡馆里唱起纳粹军歌,拉斯路指挥着里面的法国人唱起了《马赛曲》,这是对立的革命,每个人仿佛都有了力量,力克甚至“感情用事”用赌博的方式故意让一对准备离开卡萨布兰卡的夫妇赢钱,他说,这是“向爱情致敬”,而致敬的似乎不止爱情,而当咖啡馆被查封,力克最后的决定是,将国境信函给拉斯路,帮他逃离卡萨布兰卡。伊莎依旧偎依在力克的怀中,他们第三次对彼此说:永志不忘。
疯狂的世界,三个小人物,在卡萨布兰卡,他们都无法安全保护自己,但是在爱情的名义下,他们都做出了牺牲。力克最后的决定是让伊莎和她的丈夫拉斯路一起离开,而他用枪逼迫雷诺上尉安排飞机,甚至在冲突中射杀了德国军官史查沙少校,当飞机起飞了,雷诺对里克说:“你不但是感情主义者,你也变成了一个爱国者了。”浓雾中的卡萨布兰卡,只留下这两个“革命者”的身影,I think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革命似乎在这样的浪漫主义下正式拉开了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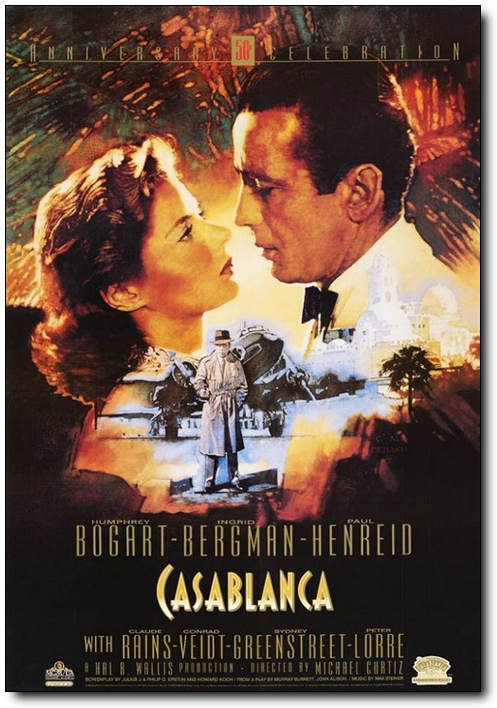 |
| 《卡萨布兰卡》50周年宣传海报 |
在革命事业中,这或许只是一个简单的三角恋的故事,对于1942年的这部电影来说,当然有着应景的意义,所以一切的爱都在让位于革命,让位于战斗,让位于崇高的事业,力克从“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找寻到了另一种为正义奋斗的理想,以致而最终重回“战场”,而伊莎对于巴黎那段爱情的放弃,以及拉斯路在明知伊莎和力克的故事之后依然没有责怪伊莎,是革命的崇高和大度?由《大家都来力克酒吧》(Everybody Comes to Rick's)改编的这部电影被认为不只是一部令人心碎的爱情电影,实际上更是一部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电影,而在世界电影史上,它也因荣获1944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奖而成为美国编剧协会公布的影史“最伟大的101部电影剧本”名单之首。
卡萨布兰卡里的革命浪漫主义在情节上似乎显得简单,但是透过这种战时的应景,那种离别和重逢的依然创造了某种经典,“As time goes by”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抵抗,那不是遥远的事,而仿佛就在眼前,就在缠绵的巴黎,在伤感的马赛,在浓雾的卡萨布兰卡,“As time goes by/I guess there are many broken hearts/In Casablanca/I fell in love with you……”心碎在卡萨布兰卡,多么熟悉的旋律,而这首经典英文歌曲《卡萨布兰卡》并不是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插曲,却完全是电影中流淌的那种忧伤的爱,隔着30多年,仿佛天衣无缝地合在一起,上世纪70年代,Bertie Higgins在看完《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后创作而成,用的是电影的名字,而Bertie Higgins也通过这首歌收获了那个“有汽笛声的结局”:“这首歌是我为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写的。我记得那是1982年,《卡萨布兰卡》是我们共同喜爱的电影,这部爱情片让我们如痴如醉。结合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我为女朋友写了《卡萨布兰卡》,她非常感动,还答应了我的求婚,成了我的妻子。”
Watching Casablanca 在看《卡萨布兰卡》的时候
Back row of the drive-in show 在汽车影院的后排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在迷离的光影里
Pop-corn and cokes 爆米花与可乐
Beneath the stars 在星光下
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也仿佛变成了香槟和鱼子酱
爆米花与可乐,香槟和鱼子酱,在另一种爱情中营造着“永志不忘”的浪漫。但是在革命之外,在电影之外,或许还有现实无法躲避的“隐喻”,在《卡萨布兰卡》中,柔情、忧郁的伊莎由瑞典籍女星英格丽·褒曼扮演,作为一个爱情的背叛者,伊莎因为丈夫的缺席而爱上了力克,从而陷入了欲罢不能的爱情迷局中,而在现实生活中,英格丽·褒曼也遭遇到了与电影一样的故事,1948年,英格丽·褒曼观看了意大利导演罗伯托·罗塞里尼执导的影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和《同胞》,被它们写实主义的风格所折服,主动写信给罗塞里尼要求与之一起拍片,罗塞里尼欣然接受。起先,他们只是合作伙伴,但渐渐萌生爱意成了情侣,她和彼得·林德斯特罗姆仍有婚姻关系,却替罗伯托·罗塞里尼生了个儿子,这使举世哗然。美国人心中所谓的“圣洁偶像”破碎了,她被逐出了好莱坞。
因为对于婚姻的背叛,褒曼为这那段没有结果的爱情付出了她7年的黄金时光,仿佛回到了1941年的卡萨布兰卡,直到1957年,褒曼才终于以《真假公主》中的杰出演技一举成为纽约影评人协会和奥斯卡双料影后。或许电影已经使英格丽·褒曼难以区分现实和虚构,1982年被病魔折磨的一代影星在伦敦去世,这位生死同日的女星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这里躺着一位伟大的演员,直到她生活的最后一刻,她还在演戏。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