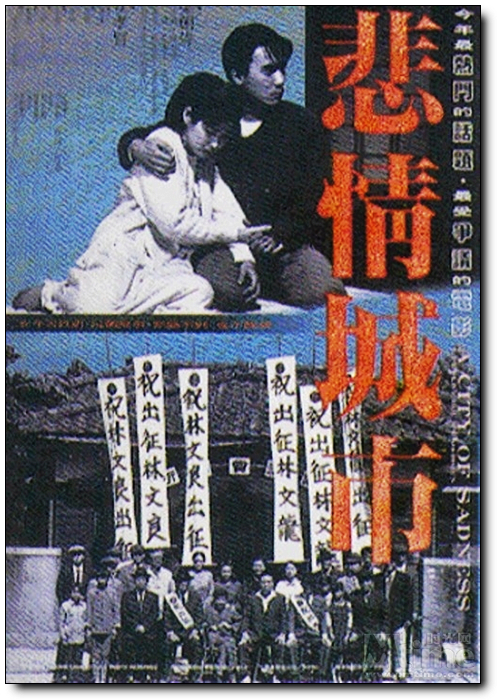2014-03-05 《悲情城市》:谁听到了海妖的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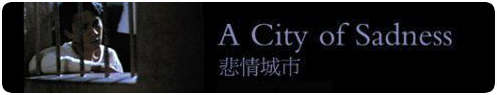
这是历史的结束,也是现实的开始:“一九四九年,日本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这是历史的开始,也是现实的结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开始是寂静而黑暗的夜,开始是昏黄的灯,结束也是寂静而黑暗的夜,结束也是昏黄的灯,158分32秒的故事里弥漫的是某种伤痛的轮回,在悲情城市里次第上演,而这一段历史深处的伤痕,是如此刻骨铭心,即使在40年后的侯孝贤身上,也是永远不肯结痂的痛。
当日本裕仁天皇投降诏书公告天下的时候,当日本战败投降的新闻在林家广播里响起的时候,时代似乎要展示的是一个清晰的段落,只是昏黄的灯光和女人疼痛的叫喊交织在一起,让宏大的历史变成了对于一个家族衰亡和新生的叙述。“林文雄在八斗事的女人生下一子,取名林光明。”这一段话承接在“台湾脱离日本统治”之后,这是痛苦之后生命的新生,但是对于孩子叫“林光明”的命名,对于伤痕处处的林家来说,是一种安慰,是一种寄托,是一种希望。林家的四兄弟在经历了战乱之后其实已经命运各异,本来开诊所的老二文森,战争期间被征到菲律宾当医生,至今生死未卜;老三文良,曾被征到上海当通译,战败后被以汉奸罪遭通缉,回到台湾,住进医院;而老四文清,八岁时因为从树上跌下致聋,现在在小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命运叵测,身体之残,唯一安全的似乎只有老大林文雄,他经营着一家商行,生活似乎是安定的。
|
| 导演: 侯孝贤 |
 |
青天白日旗代替太阳旗,却不知道是太阳在下还是在上,对于他们来说,政权的转换更多是一种尴尬,一方面是回到祖国怀抱的惊喜,林老师和宽容他们高声唱着《流亡三部曲》,唱着九一八唱着松花江,另一方面,有着新生的迷惘,甚至对于未来只是恐惧和不安。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后,台湾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真正的问题是失业问题,许多台湾人没有工作,以后迟早要闹大乱。”这是要谈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抱怨和害怕,而在当权者那里,许多政府部门都被有权力的人安排自己有关的亲戚、朋友,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受过日本奴役,所以要将那些奴化的人统统换掉。”但是面对官商勾结,腐败日盛的台湾来说,投降后依然是一个孤岛,依然是另一种奴役,甚至民众发出了“马关条约有没有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的质问,抗战虽然打赢了,但是老百姓还是苦,正林文雄的愤怒:“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对于林家人来说,这样的“可怜”的生存状态是怆然凄沥,甚至是陷害,是死亡。病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上海旧相识“上海佬”,在诱惑面前走上黑道,卷入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这些非法活动被文雄识破,他出面制止,不料上海佬勾结田寮帮,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陷害兄弟二人。文雄逃跑,而文良以“汉奸罪”再次被捕,文雄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向“上海佬”求助,在金钱公关下,过年之前文良终于被放了出来,但是由于在狱中受到非人待遇,出狱后文良又变成了白痴般的废人。而以“干你娘”为口头禅的文雄作为一家之长,终于也陷入了黑道的争斗中,而“上海佬”的那一枪后,粗壮的文雄倒下,这个家族彻底被推向了悲剧的深渊。
|
|
| 《悲情城市》电影海报 |
对于这个家族的悲戚命运,文雄曾经有过解读,“为什么老二没有音讯,老三发疯病,老四耳聋,是不是母亲的坟风水有问题?”将这样的家庭衰亡征象理解为风水,理解为家族的宿命,或许也是一种无奈,但实际上是对于悲情城市在历史更迭中的无解和迷惘。而与文雄粗暴的愤怒相比,以林老师和宽容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则是反抗的姿态,他们对光复后的国民党为政不廉极为愤慨,特别是爆发因查缉私烟而引发的“二·二八”事件之后,将这些进步人士的愤懑和反抗点燃,矿工医院里都是发生冲突而受伤的人,而广播里播发的则是陈仪对于事件的辩解,在这次事件中,国民政府虽然提出了“伤者治疗,死者抚恤”的温情政策,实际上是用“缓兵之计”大肆追捕进步人士,在滥杀无辜的现实面前,宽美护送哥哥回到四脚亭老家避难,但是却被父亲说成是“不孝子孙”,无奈之下,继续在山里成立抗政府的组织,他写给宽美和文清的信中说:“当我已死,我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
这种隐姓埋名其实是新的战斗形式,是对于现实的另一种反抗,“美丽的将来”映衬着丑恶的现实,而对于文清来说,这种丑恶先前对于他,则是不闻不问,是遗世独立。他是一个聋子,在八岁那年从树上摔下来而使耳朵致残,那羊的叫声、唱戏的声音似乎只留在童年的记忆里,而对于惨痛的现实来说,失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方式。他们在谈论着国事,而身为摄影师的文清却和宽美坐在角落里听一首德国的曲子。其实文清是听不到的,他与人交流只是将心里的想法写在纸上,而宽美也告诉他,在这首曲子里,莱茵河畔女妖有着美妙的声音,那些经过船只上的船员为她动听的声音所折服,但是正是因为这歌声,使所有的船只撞到礁石,最后船覆人亡。这个如塞壬一样的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现实,对耳聋的文清生活的一种隐喻,听到的或许是动听的美妙的歌声,但是这声音却是邪恶的,是灾祸的开始。
但是文清似乎不可能永远是聋者,一方面家族不断上演的悲剧使他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另一方面,在林老师、宽容的进步思想影响下,他也受到了牵连,甚至身陷囹圄。“你们连聋子也不放过,还有没有天理?”这是林家老父亲对于那些当政者的质问,而在这样一个没有规则的现实里,文清似乎并不是聋子,是他们一定要让他听到那海妖的歌声,只不过在监狱里,邪恶的歌声变成了刺耳的枪声。
监狱里传来预警的喊声,“开庭”实际上是宣布枪决,开门,文清坐在门口,狱友起身,在镜头外穿衣做准备,然后与文清握手、拥抱,平静的表情,缓慢的动作,没有喧哗,没有抗争,其实这就是临死之前的告别,他们知道自己的归宿,知道自己最后的命运,最后关上门,隔绝了文清和他们的世界,也隔绝了胜者与死者的命运。一声枪响,又一声枪响,两颗子弹在寂静的空击中呼啸而过,而坐在监狱窗边的文清依然茫然,是的,他或许是听不见那刺耳而血腥的枪声,但是在他看来,死亡早就被听到了,那颗子弹仿佛是打在他的身上,打在他耳聋的现实里,依然嗡嗡作响。接着预警又是一声叫喊“林文清,开庭!”仿佛命运要将他和那些被枪杀的狱友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在这一声叫喊之后,是文清茫然地走出监狱的门,长长的过道,阴暗的过道,像是生命必经的那一段路,只是走完这过道,文清并没有被枪决,在长镜头之后是他回到家中,坐在墙边,和家里人一起吃着饭。
固定的镜头,缓慢的节奏,这平静的叙述后面是擦肩而过的死亡,但并不是释然,政治的惊涛骇浪对于一个身体残疾、活在无声世界里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和痛苦,静默并不是逃避,不是无争,而是渺小个体的压抑,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换来的不是痛苦,而是一种自由的信念,在出狱后文清寻找那些狱友的亲属,把他们的遗物交给他们,而他们写给家人的信里是这样的话:“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以及“你们要好好的活着”。而“死生天命”、“好好的活着”的喟叹更折射出在政治风波中个体的渺小和孱弱,而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终于也没有远离文清的生活,终于用一种更加刺痛的方式侵入了他的生活。
在哥哥文雄葬礼之后,文清和宽荣的妹妹宽美成婚,婚礼在葬礼之后,两种仪式的交替传递着命运的无常,在林家,父亲已经老态,文雄被黑势力枪杀,文良变成一个只知道吃敬神的食物的废人,文清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而拜神拜祖先、跪拜叩首、夫妻对拜之后,并不是美满生活的开始,两个人相敬如宾,孩子阿谦出生,这也绝非是最终的幸福。那个夜晚送来的信又将他和整个家庭拉向未知的深渊,急促的敲门声之后,文清拿着信,依然没有大哭大喊,只是掩着面低下头,而正在给阿谦喂饭的宽美也没有失声痛哭,呆呆地坐着,而后悲伤地靠在文清的身上,哥哥之死,基地被查,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感知了发生的一切,也知道这个家、文清的命运会走向何处。平静里的悲伤更让人心痛,文清用自己手中的相机拍下了一家的合影,这完整的定格对于他来说是留下的最后怀念,三天之后,文清被捕,命运终于滑向了悲剧的深渊。
“阿谦已经长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来家里走走,九份开始转冷了,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这是文清被捕至后,宽美写给文雄的女儿阿雪的信,信里是满满的哀愁,是在无常命运前面的叹息,而对于温柔、善良的宽美来说,对于未来还留存着最后的希望,这就是那个像“四叔”的阿谦,那个还在呀呀学语的孩子,他是文清生命的某种继续,又像是对他耳聋这种身体之残的超越。在这一个和政治有关的“悲情城市”里,宽美似乎一直是一个旁观者,她用她的日记记下了这一段历史,而这样的历史在她那里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于幸福的追求。“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云,带着父亲写的介绍信,上山来金瓜石的矿工医院做事。哥哥教书没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来接我。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这是她初次来到旷工医院写下的日记,时间是日本天皇的纪年,而她看到的是这里的天,这里的云,这里的美景。林老师对她讲的那个日本少女自杀的故事,于她来说也是一种生命的精彩和美丽:“明治时期,一个日本少女在樱花盛开时,自飞瀑下一跃而下。她不是厌世,亦不是失志,是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跟樱花一般,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她的遗书,给当时的年轻人整个都振奋起来,当时正是明治维新,充满了热情与气概的年代……”
“同运的/樱花/尽管飞扬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这是一种诗意的人生,这是自由的生命。在和文清结婚,看着阿谦成长的时候,她写道:““今天下午,听到新年第一次春雷,声势很大,一阵又一阵,像要把山跟海都叫醒一般。”云天、樱花、春雷、芒花,这些自然界的事物对于她来说是纯净,是幸福,而她所追求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文清第一次被抓,对她来说”只要文清平平安安就好“,是的,这样一个女子,想要的就是平安,就是美好,就是一家人的幸福,但是这样的要求在那个时代,只能是一种奢望,一种无奈。
这是悲情的城市,这是悲情的时代,一个家族的悲剧隐含在那段惨痛的历史中,而在40年后,那个叫侯孝贤的台湾电影导演将这一处伤疤揭开,对于他来说,“台湾”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也不是和政治斗争相关的敏感词汇,它是一种生存状态,是一种自由意识,是艰苦追寻中的觉醒,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开始和结束是四年的历史,而侯孝贤放弃和政治有关的纪年,采用公元纪年,这种时间的“去政治化”正是他心中的那种自由和独立,而那刻在历史深处的伤痕,成为永远的警示。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