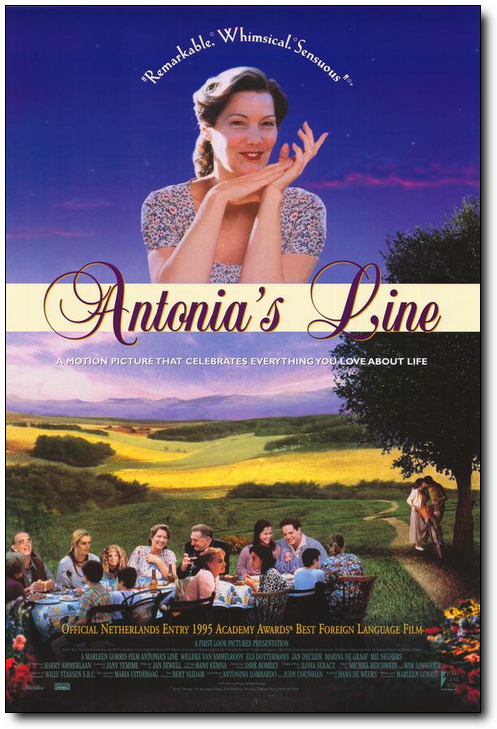2017-03-02 《安东尼娅家族》:生命就是被活着

这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是“现在是死的时候”,安东尼娅躺在床上,看着这个即将告别的世界,仿佛以预言的方式迎接必然要走向的死亡。她说“我想看看死亡有多么惊人”,当她面对镜子照见自己的面容,当她推开窗户容纳所有的阳光,当她在人生定格的照片里看见走过的一生,在回忆的世界里抵达生命的最后一天,其实死亡并不是惊人的,更不是惊恐的,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死亡正在自然地发生。
自然的死亡,充满爱意的死亡,在安东尼娅的身边是自己后来的丈夫巴斯,是开咖啡馆的邻居奥尔格,是那些正在成长的孩子,而最让安东尼娅牵挂的则是家族体系中的那些“心爱的人”,他们是自己的女儿达尼埃拉,是孙女斯拉西,是曾孙女萨拉,他们是“她们”,和自己一起组成了一个女性家族的序列,而在这个序列里,自己不是起点,最小的萨拉也不是终点,就像生命一样,在爱人身边,在回忆里,它就是一条自由流动的河,不是被剥夺了活着的时光,而是在一个人的死亡里继续向前,“长长的编年史,最后只有一个结论:没有什么走到了终点。”
这一幕似乎以相同的方式发生在安东尼娅母亲逝世的那一天,也是躺在床上,也是苍老的面容,也是坐着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但是当安东尼娅返回村庄为母亲送别,她看到的却是一种痛苦,一种仇恨,母亲不停地骂着早已死去的父亲,骂着像小偷一样卑鄙的父亲,甚至骂着前来送别的女儿安东尼娅,当在牧师的口中听到“安东尼娅”的时候,母亲狠狠说了一句:“像你父亲。”然后倒下了身子,然后睁大了双眼,然后走向了死亡。
|
| 导演: 玛琳·格里斯 |
 |
这是安东尼娅出生的地方,这是她20年前离开的起点,返回并不只是对于地理意义上的回归,而是情感的延续和新生。和母亲的逝世一样,这个刚结束战争的村庄,其实也挣扎在死亡的病态中,这里有对着满月像狼一样吼叫的疯子马达娜,有在男人的暴力中只能选择沉默的弱智者迪迪,有总是弥漫着小便气息的咖啡馆主人奥尔格,有被小孩子欺负总是傻笑的洛尼……他们生活在这个村庄里,仿佛是战争带来的后遗症,总是显出病态的一面。而当安东尼娅回到村庄的时候,在奥尔格的咖啡馆里,那些男人甚至骂她是“浪子的女儿”,充满了嘲讽,充满了厌恶。
但是回来就是为了寻找生命的另一种意义,当母亲死去,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母亲、安东尼娅和女儿达尼埃拉构成了这个女性家族在一起的第一幕,母亲是一种病态的死亡,安东尼娅是走出去之后的回归,而达尼埃拉,在无根的生活中窥见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她在葬礼上看见死去的祖母忽然做起来,和唱诗班的人一起唱歌;她在教堂里看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会露出诡异的笑容;她看见雕塑活过来用翅膀拍打犯下罪行的人。第一代的女人以死亡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第二代的女人以回来的方式重建秩序,而第三代女儿则以虚构的方式打开魔幻的现实。
|
|
| 《安东尼娅家族》电影海报 |
三代女人,是一个家族的垂直体系,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一种单性循环,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男性缺失的象征。母亲在临死前不断骂着像小偷一样的父亲,旁人总是讽刺地把安东尼娅称作是“浪人的女人”,暗示着那个已经死去的父亲是一个恶的符号,而安东尼娅自己呢,她也许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离开这个村庄的,但是当她20年后回到这里的时候,身边没有自己的丈夫,也根本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男人,所以对于达尼埃拉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存在近乎死亡的父亲。
父亲的缺失,其实并不是生命的无奈,并非是命运的捉弄,对于安东尼娅来说,甚至也是自己的一种追求,当农夫巴斯找到她表白自己的爱慕之心的时候,他说:“我想给儿子找一个母亲。”安东尼娅回答他说:“但是我并不想为自己找一个儿子。”这是一种冷漠的拒绝,更是对于男性主动的回避。而达尼埃拉,似乎也看见了男性世界里的那种恶,就在仓库里,她看见迪迪的哥哥竟然在强奸自己的弱智妹妹,一把作为农具的叉子被钉在了他的下体,然后达尼埃拉带着迪迪逃离。
迪迪被安东尼娅收养,这是安东尼娅从个体的家庭走向家族的开始,弱智和被强奸的迪迪,不仅是智力上的弱者,也是男性世界里的牺牲品,所以这种解救和收养具有某种对于女性的保护意义,而达尼埃拉主动成为那个保护者,就是把勇敢赋予自己作为女性的一个意义。所以当安东尼娅家族开始了这个起点,就是让女性从男性缺失的世界里出来,变成一个主宰者。达尼埃拉为什么会在安东尼娅面前说出“我想要一个孩子”?想要一个孩子,却不想要丈夫,这完全是是对于婚姻的否定,也是对于一种伦理价值的颠覆,因为她知道母亲的男人也就是自己的父亲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为她见证了男人的粗暴和罪恶,所以她只想要一个延续生命意义的孩子。
去了城里,在拉塔的努力下,她和那个骑摩托车的帅气男人皮特睡在一起,这是生命延续最简单的方式,她在他身上释放了欲望,甚至获得了快感,在倒立状态中种下了种子,但是皮特从来不是她的男人,当然也不是她女儿的父亲。父亲再次缺失,却是达尼埃拉主动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挑战的是伦理,颠覆的是道德,所以当挺着大肚子在教堂里做礼拜的时候,不仅是牧师,还要旁边的人,都在诅咒她,骂她堕落,说她是淫妇,必须在上帝面前忏悔,必须得到救赎。
想要一个孩子,是因为达尼埃拉否定男性的存在,否定村里的病态,也在另一种意义上,在成为只属于自己的生命体系中,她彰显的是一种独立的女性意识。而达尼埃拉生出的又是一个女儿,斯拉西,一个智力超常的女儿,一个成熟异常的女儿,斯拉西在安东尼娅面前对达尼埃拉的评语是:“你的女儿不正常。”不正常是悖论常理的,对于斯拉西来说,这不是蔑视,而是一种肯定,就像若干年后,自己和西蒙生下女儿萨拉,西蒙对幼小的萨拉说的那样:“你的妈妈不正常。”
不正常是达尼埃拉不需要丈夫而生下女儿斯拉西,不正常也是斯拉西被男人强暴而成为受害者,那个皮特重新来到村子的时候,已经不是骑着摩托的帅小伙,而是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他的到来不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不是给她一种爱的弥补,而是为了分割所谓的财产,甚至他把斯拉西强奸了。一个父亲强奸自己的女儿,这不是所谓男性的缺失,实际上就是男性在堕落中成为一个乱伦者,安东尼娅拿着猎枪把皮特赶走,而那些男孩们则在揍打中断了他的男根,而詹耐更是将他按在水缸里,结束了他卑鄙的一生。
如果说皮特的死是男性意义在肉体上的覆灭,那么智力超群的斯拉西对于男人的调戏则是一种精神上的虐待,在她看来,她们是虚伪的,是夸夸其谈的,“我和那些知识分子进行试验。”试验的是生理意义上的性,但最后他们都被脱光了衣服赶出了斯拉西的房间,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一种羞辱。即使她最后选择和巴斯的儿子西蒙结婚,并不是对所谓童年友谊的延续,也不是在试验之后女性意识重新回到男人世界,“我爱西蒙,但结婚是一种错误。”错误却恰恰是自己存在的一种荒谬感,母亲达尼埃拉只是想要一个孩子,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生下了自己,而皮特对自己的强奸则把伦理意义完全解构了,所以当成为西蒙的妻子,当怀孕而响起“想要”“不想要”的争论,最后到来的女儿萨拉,也变成了极端化的女性独立思想的一个生动实践。
而萨拉的到来,似乎是对于“快速出生”的一种终结,达尼埃拉生下了斯拉西,斯拉西生下了萨拉,巴斯拥有一大群的儿子,拉塔和曾为神父的男人生下了12个孩子……这是生命的奇迹,但是当萨拉在纸上写下死亡的时候,快速的生转变为快速的死:疯子马达娜在吼叫中死去,楼底下的新教徒抱着马达娜在月夜死去,他们葬在一起,“他们没有共享一张床,但是他们共享了一个坟墓。”詹耐被奶牛撞死,洛尼死于车祸,拉塔是在床上……所以在这生生死死的魔幻中,芬格提出的问题是:“快速的出生和死亡,谁来结束?”
安东尼娅、达尼埃拉、斯拉西、萨拉构筑的四代家族是一种女性独立、自由的象征,他们不是缺失一种父亲,而是不断地阉割男性。但是就如她们没有父亲的繁衍一样,当男性以肉体和精神的死亡方式存在于他们对立面的时候,其实这个家族式的故事,却在阉割男性之外,开始了另一种态度,那就是重构。安东尼娅接纳了巴斯,是把安东尼娅家族扩大的一个显著标志,她终于在压抑之后看见了自己的欲望,于是坐上了巴斯的拖拉机,于是走进了河边的小木屋,于是一种爱情悄然而至。而对于达尼埃拉、斯拉西和萨拉来说,她们的生缺失的是一种社会意义和伦理意义的父亲,但是却潜在地拥有精神意义的父亲,那就是在战争中幸存的芬格,他是安东尼娅的老朋友,他的一生和书为伴,达尼埃拉来到村子里的时候,首先被母亲带着去看望这个书斋里的男人,他成为达尼埃拉画笔下的人物;斯拉西出生之后,芬格给她讲述的是诗歌、宗教、哲学,说到的是叔本华、尼采,而萨拉也是和芬格成为好朋友,所以萨拉关于死亡的诗歌也是和芬格的启蒙有关。
芬格以一种精神之父的形象成为四个女人身边最亲近的男人,这是一种重构,但是这种重构最后还是以死亡的方式被终结,因为芬格认为世界是黑暗的,是荒诞的,从来没有上帝,所以他对于生命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在斯拉西怀孕的时候,他告诉她,不该把生命带到地狱世界里,“最好的事情是别出生。”他体验了存在的痛苦,他预言了死亡的生命,“我不信上帝,我控诉自己没有什么会更好——更好和更糟,没有什么区别。”更好喝更糟没有区别,所以生和死也没有区别,或者说生就是一种死,当他终于以上吊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其实宣告了生命在形而上意义上的终结。
这种死亡论或者就是战争给他带来的伤害,作为一个幸运者,他拥有的是生命,但是和死亡又有什么区别?所以安东尼娅家族带来的诸多生命,那种快速的生和快速的死又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安东尼娅以家族的名义将疯子、妓女、弱者都带进家里,实际上是真正在探寻活着的形而下意义,“生命是被活着”,战争之后是被活着,遭辱之后是被活着,但是活着的意义不是看见了死亡,“没有什么会永远逝去,一定会有新的成长。”所以当时间改变时间,当时间征服时间,并不是时间的一种消失,而是延续。
所以从母亲的终点到自己的终点,是一种关于活着的超越,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她看见的是延续的时间线,看见的是巴斯的微笑,看见的是女儿、孙女、曾孙女爱的目光,“我要死了”不是害怕,而是在平静中看见了灵魂从身体中抽离出来,在女儿、母亲、祖母、曾祖母的命名中完成了关于生命的编年史:没有什么会走到终点。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69]
思前: 《四千金的情人》:以共和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