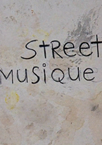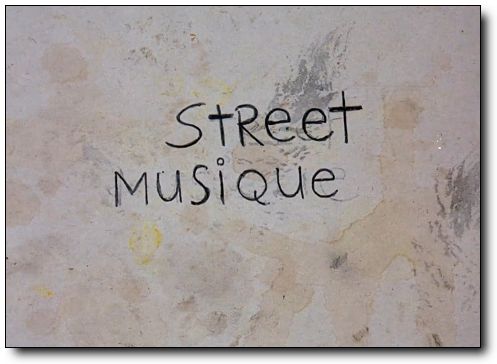2017-12-26 《街头音乐》:世界静默如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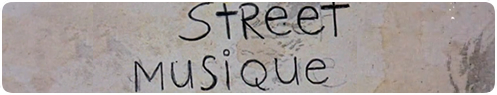
却是有声音,而且是美妙的音乐,动感的音乐,吸引人的音乐,当声音世界在乐器里打开,当音乐从街头乐手的手中弹奏而出,作为听者的你们,会听见什么?会在你的心里留下什么?音乐无形,但是在一种与听者建立的表达中,它却是有形的,甚至里面有一种被讲述的叙事,一个完整的故事。
音乐本身也是可以叙述的故事,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他们手拿着乐器,他们弹奏着音乐,或者缓慢而抒情,或者急促而制造动感,在音乐首先被打开的世界里,一定是制造者首先沉浸于此的快乐。三个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在街头表演,男人们演奏着乐曲,而女人则拿着礼帽,行人给他们的钱放在这里。但是这样演出绝不是为了赚钱,或者说,这是去除了目的性的演出,他们面带微笑,在音乐世界里叙说着令自己感动的声音,这是启迪内心的声音,而从内而外,音乐却也是开放的,那个繁忙的商业区似乎并不适合这样单纯的音乐,但是当乐向每一个路过的人点头微笑的时候,音乐也感染了那些经过的人,那些驻足的人,那些欣赏的人,音乐被传递,音乐被接受,或者就是音乐具有的分享意义。
但是瑞恩·拉金故意将街头的场景设置为黑白,黑白是过滤后的现实,是关于音乐被制造被听见的场景,但是音乐的魅力远非如这一场景一样,具有某种单一性,而是要让听见的人进入到多彩的世界。音乐依然在叙述,在抒情,但是却展开了它开放、丰富和多变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真正听见音乐的人才能看见,看见的是图形,是变化,是旋律,是节奏——当无形的音符转化成有形的图形,是瑞恩·拉金赋予音乐一种可见性,赋予声音一种表达意义,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打开那个静默如迷的想象世界。
|
| 导演: 雷恩·拉金 |
 |
从动到静,从静到动,从图案到影像,从影像到图案,所有变化的线条,都随着音乐的节奏而起变化。当音乐舒缓的时候,那里是一轮明月,高挂在天之上,而底下的红色就像太阳的光辉,照亮了天空。当节奏加快的时候,一圈一圈的圆形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色彩世界,发光的球体里演绎出一艘正劈波斩浪的船,而在无限循环而扩张的世界里,船而变成球体,是宇宙,是生命,是一种运动状态,那圆圈中心的图案又从船只变成了海边风景,月光下的树,树上的花,以及流动的光影,构成了美丽的世界。
|
|
| 《街头音乐》片头 |
美丽只是风景的一部分,在变成怪兽之后,世界又呈现出多样性,大象而变为蛇,蛇而吞噬人类,人又坐上了可以疾驰的摩托车;女人变成了飞翔的鸟,飞翔的鸟又变成行走的人,行走的人又变成了夸张的手,于是进入那一个鱼缸,躺下去,又变成椭圆的镜子,在镜子里世界被打翻了颜料瓶,在丰富的色彩中让世界呈现它的另一面。而那些人,也进入了球体世界,他们在奔跑,他们在游戏,他们像球一样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限循环的场景。
其实,变成什么,和不变成什么,也不需要带着目的论的观点去看,可以是长着羽毛的鸟,也可以变成凶神恶煞的怪物;可以是射击的男人,也可以成为在大海中航行的船,而所有呈现的一切,所有可想象的一切,都是因为音乐,音乐不表达逻辑,它只是在抽象意义上传递节奏,而那些具象的符号,不是解构音乐,而是在建构听者的想象,猴子、雪人、美人鱼,杂耍的人,手帕,河流,树木……被赋予的符号体系里,它们或者只是在表达自己。
表达自己,就是音乐最本质的特性,那些听者被感动,是因为音符表达了自己的心情,那些演奏着沉浸其中,是因为音乐让他们说话,当两只手握在一起的时候,现实和想象,抽象和具体,艺术和生活,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而这种结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继续着可能的变化,在体积、形态等方面成为一种隐喻,而隐喻就是一种开放的结构,就是在多义的阐释中找寻那个进入内心世界的声音。而当瑞恩·拉金又把镜头从音乐世界里转向现实的时候,那几个乐手依旧在街上,依旧在弹奏,而且继续,这是信手拈来的灵感,这是艺术世界里的自由,率性、随意,让音乐自己说话,让音乐自己寻找听者,让音乐永远在随意和自在中。
街上人来人往,音乐一如既往,打开的世界,当有人进入,他们其实都是唯一,而一起听到的音乐最后都变成了每个人的私密音乐,就这样演奏着,就这样想象着,就这样流淌着,没有目的,没有束缚,每个人都是音乐的主人,而每个人都在建造他们静默如迷的世界,分享而独享,集体而个人,他者和自我,都保留在那个最纯粹的地方。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405]
思前: 《逆向人生》:死亡依然无法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