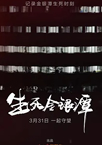2020-11-15《生死金银潭》:死亡可能会被遗忘

“3月31日一起守望”,这是片头的宣传语,三月,是还没有真正春暖花开的三月,是阴霾还没有完全散去的三月,是距离武汉解封还有半个月的三月,当三月还需要一起守望的时候,必定要凸显战胜病疫的信心和希望,而对于被命名为“生死金银潭”的纪录片来说,更多的也将是聚焦生死之“生”。
开篇航拍的镜头,是夜景下的武汉,原本熙熙攘攘的汉口火车站空空荡荡,作为武汉地标建筑的鹦鹉洲长江大桥上也是一片冷寂,作为中心疫区的武汉,仿佛就变成了一座空城,而在“中心的中心”的金银潭医院,却在上演着一场场生死之战,画外音传来:“总共66个病人,我都能吃(收)下。”“统统都能收下!”这便是对于信心和希望的诠释。信心,是关于救活病人的坚定信心,希望,是关于战胜病魔活下来的希望——信心更多指向那些医者仁心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站在生死战的最前列,肩负最重的使命,而信心指向的是那些被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的患者,他们需要坚强的意志迎来活着的新一天。
纪录片基本上是从这两个维度体现“生”的意义。21岁的梁顺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他穿好装备,进入病房,为2月26日住院进来的87岁吴女士翻身拍背;护士长贾春敏给护士戴好帽子,贴上冷凝胶,穿好防护服然后在29岁耐药结核科医生程文涛的防护服上写上他的名字;29岁的程文涛在进入病房后面对询问收费价格的患者,告诉他费用是全面的,“你要安心养病。”梁顺、贾春敏、程文涛,他们是金银滩医院的医生,他们组成了救死扶伤的强大阵容,他们不仅要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方案,还从情感上疏导他们,鼓励他们,就如38岁的护士张小倩所说:“我们真的没有想过我们要成为英雄,只是希望每一个患者都好,他们好了,他们的家好了,我们的大家就都好了。”
除了金银潭医院的那些医生之外,从全国各地前来支援的医务工作者也组成了关于“生”的强大力量,24岁的孙岸中是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的护士,他前来支援的是重症监护室,梁顺带他熟悉各种装备,提醒他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且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在这间病房里成为了战友,梁顺告诉他等疫情结束带他去吃武汉好吃的,特别是热干面,一定要让孙岸中记住武汉的美食,而第一次来武汉的孙岸中防护服上绘着一些卡通形象,他知道此次支援自己重任在肩;来自上海南浦医院的李晓静则回忆支援时的情况,那时大年三十,还没有和家人团聚的她就接到了命令,“我们连请愿书都没有写,直接就上了,根本没多想。”两个小时就全部准备完毕,然后他们搭乘绿皮火车一路向西来到了武汉,马上投入到了战斗中去。
| 类型: 纪录片 / 短片 |
无论是金银潭原来的那些医生护士,还是来自全国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生与死的考验中毫不犹豫,体现了一种忠于职守的职业精神,而作为站在抗疫一线的一份子,他们也代表着全国奋战的抗议先锋,在最危险的地方担负着最大的使命,他们的信心对于患者来说,就是一种生的希望,但也正是这种视角的单一化,对于真正处在生死关头的患者,缺少一种平等视角,甚至将“生死金银潭”这种生死一刻转化为某种单一的温情主义:当患者情绪开始波动时,医务工作者不管鼓励他们,将他们拉回到保存希望的界限里,有一个老人出现了ICU综合征,他不断叫着:“我不想活命了,没有太大希望。”程文涛安慰他,告诉他早上还和家人进行了通话,“他们都等着你回去团圆,咱们要好好活着。”而在医院的病房里,医患之间处处充满了和谐气氛,医生会给住院的病人剪头发聊家常,像家人一样陪伴他们,而等到患者出院了,他们会送上鲜花,然后和病人拥抱,病人在出院时对他们表示感谢。
在医务工作者的单一视角下,生只是变成了一种医学意义上的生,而那些凭着自己坚强意志战胜那个“死去”自己的病人,则基本没有进入纪录的视野,这种处在隐秘状态的记录,和为了保护打上的马赛克一样,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静态的物,完全靠着救治的运气。而这种单一视角最明显的不足是凸显了“生”的部分,却忽略了死亡的严酷性。“截至3月30日9时,医院累计收治新冠患者2780例,出院患者2129例,病亡患者318例……”这是最后的字幕,字幕里的数字很好地诠释着“生死金银潭”这一主题,当然,病亡病例相对于患者总数来说,是一个小比例,甚至只有出院病例的六分之一弱,但是这种将生死数据化的处理明显是为了传递正能量的要求使然,但是每一个死亡病例,不仅仅数数字,它更是一种生命的永远消逝,这种对死的某种忽视,也是对于生命本体的某种冷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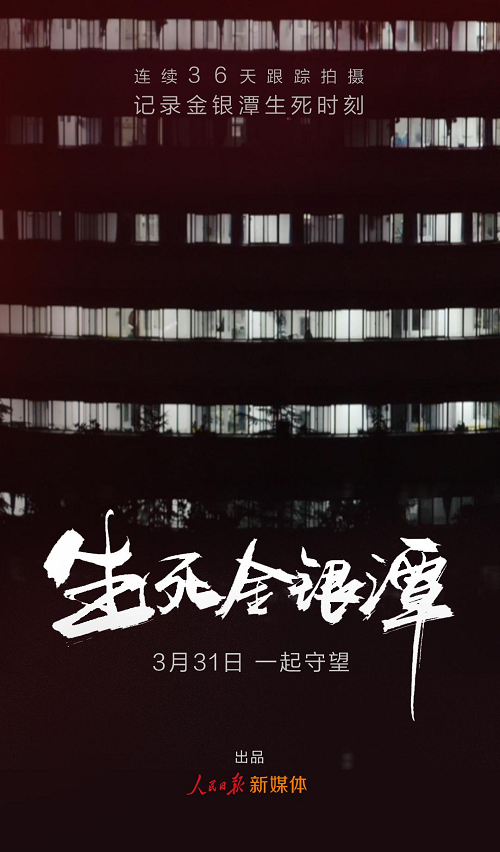
《生死金银潭》电影海报
在纪录片中,其实有着对于死的片段,那个叫着不想活命的患者,在长时间的住院中患上了ICU综合征,或者对于他来说,心理的疏导是第一位的,程文涛安慰他家人等着他团圆也是一种精神治疗方式,但是这个老人的痛苦并没有得到更细节化的展示;46岁的闵女士挥舞着无力的手,想要扯掉那根呼吸管,因为保守痛苦的她对于生已经不抱有希望,更重要的是,在她看来,插满管子的生比彻底的死更难受,医务工作者制止了她的行为,当那只手再次无力的垂下,一种生的痛苦便被遗忘了;46岁的黄先生说自己家里5个人感染了,自己的大哥已经不幸走了,这是一种已经发生的死和正在发生的死组合成的痛苦,而医生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安慰,在缺失了“将死者”的感受之下,张顺拍摄他平安的视频给家人反而变成了某种谎言。“自己上夜班的时候总有患者在自己手上去世,我恨懊悔。”当有人的生命在自己手上逝去,当自己眼睁睁看着死亡发生,这又是怎样一种体验,难道仅仅用“懊悔”这两个字就可以传递一种死亡经验?
死亡是隐秘的,死亡是简约的,死亡在生的反面却可以被生的信心和希望战胜,正是在这一种逻辑中,“生死金银潭”变成了一种对于生命的单一叙事,片末出现的字幕点名了在金银潭病区那些新冠患者的命运:80岁的吴先生3月8日去世,46岁的黄先生和闵女士目前病危,王先生即将出院,杜女士已经出院——从去世到病危,从即将出院到出院,仿佛就是以不同患者的结局构建了从生到死的序列,这一序列是完整的,也应该是纪录片的叙事逻辑,但是当“3月31日一起守望”成为一种当下情境,当“我们真的没有想过我们要成为英雄,只是希望每一个患者都好”成为医务工作者的唯一希望,当“他们都等着你回去团圆,咱们要好好活着”让患者在情感中树立信心,死被放在了一边,死变成了不被看见的存在,死又何尝不会成为历史深处那个被遗忘的关键词?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