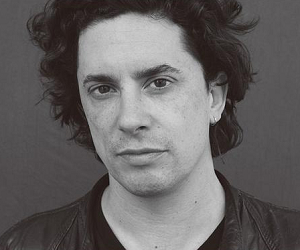2022-11-12《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唯一的智慧是悲剧

那我问他我的柠檬树还能活多久。他说没法知道,除非砍了它,数年轮。但谁会这么做呢?
——《后记 夜晚的园丁》
砍掉一棵树,数一下树的年轮,这是对生命最简单的计算,但是这种计算是残忍且残酷的,甚至它就是一种悖论:当树被砍掉而知道它的年纪,它已经死亡,死亡的树无法再回答“我的柠檬树还能过多久”的问题,戛然而止于一种人为的暴力,即使得出了确切的答案,它也以死亡的方式终结了生命——砍了它是得到答案的必然性行动,必然性的结果回答的是“还能活多久”的可能性问题,当必然性终结了可能性,是不是一种理性的胜利?但是“夜晚的园丁”却在质疑:“谁会这么做呢?”
既是回答,又在质疑,夜晚的园丁其实成为了“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的隐喻性存在:一个曾经搞数学的人,一个在职业生涯起步时就已经达到辉煌的人,为什么远离数学而“隐居”在山中的镇子里?他挖地,他看树,他抛弃家人,抛弃事业,抛弃朋友,在远离数学的地方活着——仅仅是活着?“如今他谈起数学,就像戒了酒的酒鬼谈起酒,既渴望又恐惧。”这当然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于他来说,对数学的恐惧就在于数学“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不是原子弹、计算机、生物战或气候的末日改变了世界,真正改变世界的只有数学,就像革新了几何学的格罗滕迪克,就像制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氯气的弗里茨·哈伯,他们一生都在研究数学,都在试图用数学更好理解这个世界,但是最后发现他们的数学制造了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亡,就像一棵柠檬树被砍掉而得出了必然性的结论,却扼杀了可能性的存在——按照园丁的说法:“但树木是种很不一样的生命体,这种过度繁育的景象不像植物,倒像我们人类无节制的增长,已然失控。”
这是园丁所认为数学的罪,所以他成为了园丁,所以他隐居在小镇,所以他和活着的树木生活在一起,但是这是放弃还是逃避?数学带来的是改变世界的灾难,但是当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园艺上的时候,那种灾难或死亡死不是再不会发生?他害怕那棵橡树,是因为小时候他看见奶奶吊死在树上;他知道这里有一种植物叫红叶桑寄生,当蜂鸟大口吸吮从树干中偷来的汁液,它就会醉倒甚至醉死;作者本哈明·拉巴图特和女儿住在这里的时候,就发现两只死狗被毒死在这里……童年留下记忆的死,蜂鸟喝醉的死,两只狗被毒倒的死,不也正是和树有关的死?它们和数学无关,却依然是对生命的扼杀,或者从另一个的意义上来讲,只有懂得数学才能解开这些死亡之谜,这也意味着数学并不是制造死亡和灾难,而是带来的解救,它是科学的组成部分。数学改变世界,带来的是死亡的灾难和不死的解救,既然数学有着明显的两重性,是不是真正的罪不是数学,而是和数学有关的人?
但显然,无论是夜晚的园丁,还是本哈明·拉巴图特都着眼于数学所制造的灾难,甚至夸大和放大了数学在人类科学史上的负面影响——本哈明·拉巴图特就是从那些数学天才的故事入手,讲述他们在用数学改变世界的过程中陷入的悲剧困境,他们站在人类科学的顶端,却最终没有让自己跨过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于是在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矛盾甚至悖论中,像“夜晚的园丁”一样,也许只有将柠檬树砍掉才能终止无节制的增长,对数学在纯粹科学和理性意义上的探究和实践,最后也在这种无节制中变成了人类的悲剧——在题辞中,引用盖伊·戴文坡的那句话,本哈明·拉巴图特就明确阐述了自己写作的主题:“我们攀升,我们坠落。我们通过坠落而攀升。失败塑造了我们。/我们唯一的智慧是悲剧的,它总是到来得太晚,也只为迷失者所知。”
攀升是为了抵达科学的一个个高峰,但是攀升却注定有一种悲剧性的命运:坠落,而且“通过坠落而攀升”,这是西西弗斯的寓言,推动那块大石头向上的西西弗斯在本哈明·拉巴图特看来,当然是一种失败,而且是人类命运的必然,所以,“我们唯一的智慧是悲剧的”,因为它是为迷失者所知——在这里,本哈明把智慧看成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就在于它所知的主体是“迷失者”,这种设定自然将数学的科学变成了某种谵妄,自然将智慧导向了悲剧的一面,自然把灾难看成了数学“不再理解世界”的存在:主体是迷失者,何来科学,何来智慧,何来理性?而探索智慧和科学的主体缘何会成为迷失者?
《普鲁士蓝》中的智慧就是“普鲁士蓝”:一七八二年,卡尔·威尔海姆·合勒用一把沾有硫酸残留物的勺子搅拌了一罐普鲁士蓝,从而创造了现代最重要的一种毒物。这是一次误打误撞的巧合,这是关于科学可能性的经历,但是可能性最终变成必然性:它是毒药,它将带来人类的灾难。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矛盾在“普鲁士蓝”中明显表现出来:起初只是为了要一种洋红的颜料,它是通过碾碎数以百万计的胭脂雌虫而获得的,德国鸟类学家、语言学家和昆虫学家狄斯巴赫从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仙人掌上获得了这种原料,后来他却依然发现了另一种颜色,这就是普鲁士蓝,从可能性得出了必然性,普鲁士蓝诞生了,它在狄斯巴赫的赞助人约翰·莱昂哈德·弗里施那里变成了具有极大市场潜力的“黄金”,在用勺子制造了现代毒物的卡尔·威尔海姆·合勒那里,则发现了“它极强的活性所赋予它的巨大潜力”——它是氰化物的真正源头。
| 编号:C64·2220905·1866 |
无论是变成市场的黄金,还是研制出氰化物,实际上科学都变成了人所操控的一部分,而这种操控背后是对科学理性的某种破坏:氰化物触发反射会“切断”呼吸,“一声可以听见的喘息声”带来的是心动过速、呼吸暂停、抽搐和心血管衰竭,起初应用于杀人犯和刺客的处决,后来英国政府用它对同性恋进行化学阉割;拥有犹太血统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第一次将它应用于战争,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日,驻守在比利时小城伊普尔附近的法军被杀得片甲不留,有人指责哈伯破坏了科学,哈伯的回答是:战争就是战争,死亡就是死亡,管它用什么方式造成的;二战时,整个德国国防军的军粮中都配给有甲基苯丙胺片剂,在市场上它叫拍飞丁,士兵们服用之后可以几周都醒着,在药效中完成作战是它的最主要作用,“绝对的静默统治着大地,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也如此不真实。我感觉自己完全失重了,像在我飞机上方飞行。”纳粹空军飞行员如此写道;最终导致的是狂躁或精神错乱,最后是成批的自杀,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自杀潮席卷了德国,一九四五年四月,伯林有三千八百人自杀;当然它也被用于集中营里的屠杀,在奥斯维辛、迈丹尼克和毛特豪森,被齐克隆B杀害的人,“一边死去,一边闻着一手造成他们灭绝的人在嚼碎自杀胶囊时品尝到的同样的芳香。”——在反犹主义中,将毒药应用于战争的哈伯到英国申请了避难,但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的妹妹和外甥,以及那么多的犹太人,都死在了纳粹手上。
切断呼吸,带来狂躁和精神错乱,在谵妄中自杀,也许这些是“普鲁士蓝”这种毒药本身带来的病态反映,但是当哈伯将其运用在战场中并认为“战争就是战争,死亡就是死亡”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背离了科学的精神,是不是已经亵渎了数学的智慧,是不是已经毁灭了自我的理性?而身为犹太人在二战中遭遇背井离乡和家人遭到屠杀的悲剧,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报应?哈伯去世时发现的那封写给妻子的信,似乎是某种科学精神的回光返照,带着内疚但没有悔恨的哈伯认为,他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做法将彻底改变地球的自然平衡:只要世界人口缩减到前现代的水平,植物就会疯长,到那时它将彻底填满地球表面,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将淹死在一片可怕的绿色里,“世界的未来将不再属于人类,而是属于植物”。
这是哈伯对未来人类命运的担忧,他似乎依旧站在科学家的高度,科学家属于理性,但是在因内疚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哈伯又是一种个体存在——科学家和个人身份并不都是在一个维度里,而个人具有的是远比科学更为复杂的感情,他有喜怒哀乐,他有酸甜苦辣,他有理性和欲望,所以在科学面前,他最重要的身份一定是一个人。《史瓦西奇点》中的史瓦西,在一个人的属性之上还有另外更多的属性: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德军中尉。一九一五年,当哈伯制造的毒气让伊普尔的法军片甲不留的时候,史瓦西关于广义相对论的第一个精确之解写在了信的背面寄到了正在伯林公寓里喝茶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手中,一个在战场上的德国中尉竟然在枪林弹雨之中完成了这个解,“这真是个奇迹。”
|
| 本哈明·拉巴图特:虚构了数学的原罪? |
奇迹是完全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的,“他分析了一颗无自转无电荷、呈完美球形的理想化的恒星,然后用爱因斯坦方程来计算这团质量会如何改变空间的形状,就好比一颗炮弹,把它放到床上的时候,床垫就会弯曲。”但是在个体意义上,这个解也成为了史瓦西自我囚禁的象征:当那颗星的引力大到让空间无限弯曲,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深渊,和宇宙的其他部分永远隔绝——这就是“史瓦西奇点”。史瓦西就这样把自己推向了这个无法逃脱的深渊,这个永远被隔绝的奇点:二十八岁时他成为了全德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成为哥廷根大学天文台的台长;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军,放弃了研究的他投身在战争的屠场;因为暴露在一次毒气攻击之下,他的身体里出现了疱疹,接着是急性坏死溃疡性牙龈炎,最后他无法吞咽任何固体,连喝水的时候口腔和喉咙都像在烧灼,“一个月后,它们覆盖了他的手、脚、喉咙、嘴唇、脖颈和生殖器。又过了一个月,他死了。”
也许史瓦西到死之前都不知道致病的原因,他也没有像哈伯那样带着内疚离开,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科学家和德国中尉,但是他陷在无法逃脱的深渊,却成为了“史瓦西奇点”的一个现代隐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科学的角度认为,“奇点不会出现,原因很简单,物质是不可以被随意聚拢的,否则的话,组成它的微粒就要达到光速了。”爱因斯坦把宇宙从灾难性的引力坍缩中解救了出来,但是人类理性的坍塌却没有被解救回来: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两位美国科学家发表了文章证明了史瓦西黑洞的存在,“只要热核能源枯竭了,一颗足够重的恒星就总是会坍缩的,除非它以衰变、辐射或抛出质量的形式削减自身质量”,黑洞可以将空间揉皱,可以将时间熄灭,到那时任何物理力或自然法则都无法让他们幸免——而在同一天,隆隆的纳粹坦克碾过了波兰国境线,另一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战场打响了。
史瓦西奇点和史瓦西黑洞,是身为科学家的史瓦西做出的科学贡献,而史瓦西作为个人,却在自我的奇点和黑洞中被吞噬。和内疚的哈伯、死于疱疹的史瓦西不同的是,《心之心》中的格罗滕迪克最后以完全自觉的方式选择了离开。作为数学家的天才,罗哥滕迪克被称为数学的王子,痴迷空间的他扩展了“点”的概念,在他看来,点不是一个没有面积的位置,而是具有复杂的结构,点形成了整个宇宙——在由“他母亲的死亡面具、一只铁丝做的山羊、一箱西班牙橄榄,和他爸爸在勒韦尔内集中营时人家给他画的像”组成的房间里,他将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的时间全部扑在数学上,甚至他能自行控制自己的睡眠。在数学研究上,格罗滕迪克提出了“心之心”的宇宙实体,他以超常人的精神不断发现这个科学宇宙遥远的闪烁点。
但是当一九六七年他在越南的一次研讨会上目睹了炸弹带来的死亡,当他受到法国“六八运动”影响,当他拒绝“卑鄙而危险的数学实践”,终于远离了政治甚至远离了数学,他说“搞数学就像做爱一样”,他创立了“生存与生活”组织,他开始禁食形成了自我摧残的习惯,他隐居到了维莱坎,最后他烧毁了自己写的两万五千多页书稿、父亲的画像,把母亲的面具送人——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那个像心脏一样的晦暗客体并没有最终照亮世界,格罗滕迪克最后死在了医院里,连死因他都申请了保密。格罗滕迪克的选择是一种决绝,对于他来说,无论是隐居还是禁食,无论是烧毁手稿还是保密死因,都是将自己从这个“卑鄙而危险的数学实践”划去,这是去数学化的行动,还原的也许是一个人的存在——从可能性到必然性,或者对于格罗滕迪克来说,是自我的一次解放,是归于理性的一次实践。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需要我们重新理解世界,本哈明·拉巴图特在《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中所说的“理解”就是在科学层面和人的层面两个维度展开的。在科学意义上,是关于基本粒子的研究,从海森堡到路易-维克多·皮埃尔·雷蒙德,从薛定谔到德布罗意,这些都是天才级的科学家都在探究亚原子粒子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试图理解这个科学意义上的世界——他们正是要把理论的可能性变成一种必然性,必然性的规律,必然性的定律,必然性的理性:即使爱因斯坦的那句“上帝不跟宇宙玩骰子!”似乎让他成为了量子力学的最大敌人,他也是尝试一条通往客观世界的归路,“这是所有科学中最精确的一支,必须驱逐混入其中的随机性。”即使最终讨厌量子力学的薛定谔精心设计了“一只既死又活的猫”,即使海森堡还在挑战常识,他的不确定原理也经受住了考验。在科学意义上,探究可能性是为了通达必然性,它本身就是在理性意义上完成,即使必然性从未抵达,也体现着一种科学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就是一种动力。但是,科学之外是人之存在,是七情六欲之人的存在,是非理性人的存在,是以科学为名满足自我需要的人之存在,就像德布罗意,“用一张帘幕将所有人隔开,那种羞耻感最终成了他与这个世界的屏障,连他亲爱的姐姐都没有能够解除。”
科学和人,理性和欲望,可能性和必然性,并不都是矛盾甚至对立的存在,所以攀升并非会坠落,智慧也不是悲剧,本哈明·拉巴图特试图揭示科学理念和人之个体存在的“理解”混杂性,试图将天才与人类无节制的增长之间建立关系,夸张而有失偏颇,最后就像薛定谔的思维实验,“它给出的结果是一种看似不可能存在的生物:一只既死又活的猫。”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46]
思前:关于说文解字的总体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