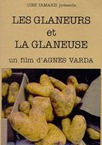2015-11-12 《我和拾穗者》:为垃圾寻找自己的主人

一只手拿着DV摄像机,另一只手则去捡被遗弃的那些土豆,对于阿涅斯·瓦尔达来说,这是在一种仿效中体验拾荒者的艰苦生活,还是进行着一场类似“新浪潮电影”的行为艺术?这个年过七旬的电影导演似乎要在自己摄像机镜头前凸显“我”的存在,那一只手是布满皱褶的手,是长满斑点的手,而另一只手里的摄像机则在不稳定地摇晃,一只手代表岁月的苍老,另一只手则代表生活,在这种跳跃的画面中,或者能体会到一种现实意义的组合,时间改变了一个人,改变了一个时代,改变了生命的历程,但是当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尽管是不稳定的,甚至是即时性的,但也一定指向当下,指向生存的现在时。
就像阿涅斯·瓦尔达站在那副著名的《拾穗者》油画面前的时候,她的背上就放着一束麦穗,仿效着油画里那个女人的动作,阿涅斯·瓦尔达似乎能体味到走进时间沧桑的感觉,而她又在自己的现实里,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自己的摄像机前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拾穗者》是被激活了,这是一种对传统的激活,对艺术的激活,也是对于生活的激活。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笔下的《拾穗者》展示了夏收之后劳动妇女捡拾那些遗落的谷物的情景,这是一首劳动的赞歌,是生活的写照,而当劳动和生活变成艺术品的时候,是不是距离我们太过遥远,是不是只能高高挂在博物馆里?阿涅斯·瓦尔达似乎希望把这样的场景还原到现实中,还原到当下,而当“拾穗者”真的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就叫做“拾荒者”。
|
| 导演: 阿涅斯·瓦尔达 |
 |
那些很大很硬的土豆,那些被机器筛选的土豆,那些被切碎的土豆,从农场的垃圾车上运来,倒在一起,每一季4500吨土豆里大约有50吨会被这样扔掉。黑衣人就拿着袋子,仔细地挑选那些心形的土豆,然后把土豆放进袋子,一天大约能捡拾70磅的土豆,这些土豆和其他捡来的食品能够让他维持一天的生活。“我每天都会想他们,他们在距离我500公里的地方。”在男子的心里,这样的生活是一种无奈,却也保持着某种希望。而和黑衣男子一样的那些拾荒者,有人却把这里当成“土豆王国”,“和鲱鱼一起烧味道很好”;孩子们则唱着土豆之歌,像是在玩一个游戏;而慈善助餐组织的志愿者,则将捡来的土豆分给那些生活更穷困的人。
“土豆王国”里有歌声,有想念,有帮助,实际上,这些土豆似乎具有了物品之外的意义。实际上,对于垃圾而言,最基本的意义是从中发掘出起“剩余价值”,那个厨师会把烧好菜剩余的东西重新制作,他也会自己去葡萄园采集那些被废弃的水果;那个叫所罗门的拾荒者,每天像一只迁徙的鸟,去垃圾桶里捡拾丢弃的东西,那里有刚过期两天的面包,有还可以食用的水果,有鸡翅好和鱼,他捡拾回来之后,又放进那些被废弃又修好的电冰箱、烤箱,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美餐”;那个有着硕士头衔、学过生物雪的年轻人,在市场外翻捡水果、蔬菜,他是一个素食者,他吃着欧芹说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而在捡拾垃圾之外,他却免费帮助那些移民教授法语。而在水果园里,当收获的车子过去之后,很多拾捡者会走进果园,摘取枝头上遗落的那些水果,有些人是为了果腹,而更多的人并不为生计而发愁,但却在这种拾捡中感受一种乐趣,吃着自己采摘的水果,或者拿去酿酒,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生活。而有些水果园为了满足拾捡者的这种乐趣,和他们订立协议,做好注册和等级,以规范的方式进行拾捡的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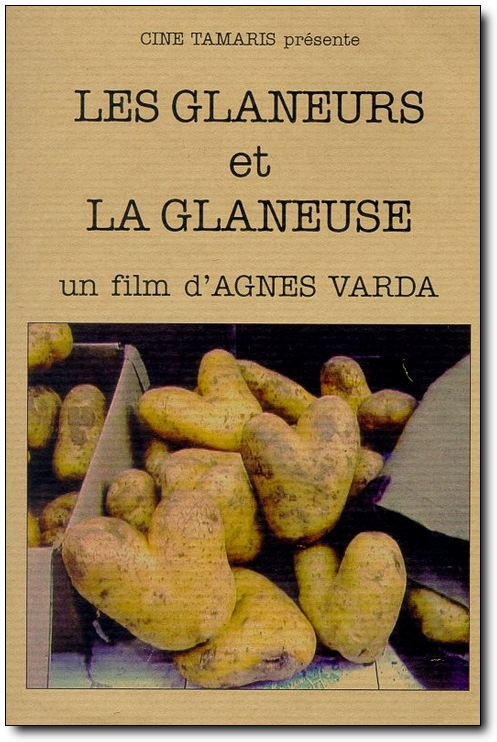 |
| 《我和拾穗者》海报 |
拾捡者利用垃圾的剩余价值,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被社会接受,很多人鄙视,反感,讨厌这样的行为,在诺伊穆迪尔这个小岛上,潮汐过后总会有许多的牡蛎被冲上沙滩,很多拾捡者准备好篮子、耙子,纷纷走向海滩,拾捡这些牡蛎,而近旁却是牡蛎的养殖场,本来在养殖场和拾捡区域中间有25码的距离,拾捡者不能越过这个距离,但是养殖人员总会和拾捡者发生矛盾,在他们看来,拾捡者甚至有一种偷盗的欲望,所以在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戒备。而在城市里的超市中,有一些流浪者去垃圾桶里寻找食物而打翻了垃圾桶,超市管理者将他们告上法庭,并说他们侵犯了私人财产,在法庭上,这些流浪者被骂成“没脑子”的人,而在他们看来,在垃圾桶里捡拾垃圾仅仅是为了生活,“我们不是反社会的人。”
将拾荒者对立在社会的边缘,这是一种误解,而其实阿涅斯·瓦尔达带着摄像机奔波在法国的角落,寻找这些拾荒者的群像,也是为了给设个群体一种肯定,而在这肯定的过程中又指向了社会的某种不合理。那些吉普赛人居住在郊外的棚子里,他们抱怨政府的安置是一种不公平,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被社会故意遗弃的,而那个穿着橡木胶鞋的男人并没有生活上物质的担忧,他甚至还有各种保障,但是他却在街头的垃圾桶里寻找食物、水果和各种有“剩余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扔掉了这些原本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一种浪费,在这个消费的时代,这是人类的一种病态,他举例说因为到处扔垃圾而导致的环境污染,使得许多鸟类在浮油的水里死去。所以为了不使鸟类被这个消费社会所扼杀,他把捡拾垃圾看成是一种美德。
遭人鄙弃的拾捡行为,变成了一种反对浪费的美德,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升,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抨击,男人说他吃了15年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食物,从来没有生过病,所以垃圾对于人类来说,也是一种误解。社会的消费制造了大量的垃圾,而这些垃圾反过来又折射出人类的丑恶,那些被捡来的冰箱,重新修好之后,不是作为盛放食物的器具,而是变成了一件艺术品,打开,是一排的人偶,里面传出来的是他们愤怒的声音,像是示威者对于社会不公平的讨伐。用垃圾反衬人类的“垃圾行为”,对于拾荒者来说,已经完全超越了垃圾本来的属性,甚至已经超越了垃圾的“剩余价值”,而成为一种态度,一种艺术。
“虚拟世界2000”就是用废弃的垃圾做成的一个艺术中心,那个年轻人展示着从各处拾捡来的垃圾做成的艺术品,里面有饭盒,有石板,有烟盒,“他们很有生命感。”而且这些垃圾带来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捡拾的人太多,一会儿功夫就找不到了。他的这个艺术中心被称为“自己的可爱洞窑”,像是一个和社会隔绝的庇护所,在艺术的世界里全然没有垃圾的可恶感。而退休的泥水匠,则将各种废弃的洋娃娃组合在一起,制作了大量的造型艺术,老伴微笑着拉着他说:“他是一个业余艺术家。”而路易斯·庞斯则从垃圾堆里获得艺术灵感,创作不同类型的绘画,在他看来,“每一个垃圾都是一首诗,而艺术的目的就是整理。”
垃圾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艺术层面,都是对于垃圾的另类阐述,而其实,垃圾作为一种无用的东西,代表着废弃和遗忘,而在这表面意义之外,垃圾也是一种无主的物品,也就是只有在主人缺席的情况下它才成为垃圾,那个拿着法典的律师站在街上,念着法律的条文,她说,垃圾是无主的东西,捡拾故意抛弃的东西就不能算偷,一旦被人带走,那么就属于他们。所以当垃圾被拾捡起来的时候,是重新找到了主人,重新赋予了意义,就像流浪者一样,需要社会的接纳,这样他们才会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于阿涅斯·瓦尔达来说,她拍摄这些拾荒者群像的意义,就在于在拾捡那些无助的物品中,找到它们新的主人,或者作为生活所需,或者成为艺术品,都完成了对于垃圾的重命名,完成了垃圾的另类意义。
“在一部关于拾荒的影片中表现马莱显然非常困难,但这的确是一个惊奇。我允许自己自由地去发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可以说这也是一部关于我自己的寻访拾荒者之旅的影片。”阿涅斯·瓦尔达这样解释自己的拍摄目的,所以在她将那些拾荒者作为拍摄目标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了拾荒者,纪录片的副标题是“艾格妮捡风景”,就是在不断凸显主观情景中,将垃圾作为一种自我寻找的风景。阿涅斯·瓦尔达在路边拍摄挡路的羊群,那是一种偶遇的风景;阿涅斯·瓦尔达对着自己漏水的天花板,欣赏受侵蚀而形成的图案,那是一种随意的艺术;阿涅斯·瓦尔达在拍摄葡萄园歌唱者的时候,拍下了自己DV摇晃的镜头,那是一种运动的美;阿涅斯·瓦尔达将自己不满皱褶的手安放在伦布兰特半身肖像油画上,那是一种触摸艺术的感受……她发现生活中存在的各种艺术细节,发现美,而这也是一种拾遗,在拾遗中体会美,体会生活。“我发现我自己像个动物,更糟的是,我是什么动物呢?”或许是因为遗忘太久,或许是废弃太多,生活中有那么多东西变成了垃圾,变成了无主的物品,而人类自己呢?是不是也越来越成为自我遗弃的物品。
葡萄园园主不仅经营酿酒的葡萄园,还是一位哲学家,提出的反自我的哲学,而这种哲学对于垃圾世界来说,也是一种寻找,而另一个葡萄园的地下室里,却都是发明电影的先驱者之一马来的照片和摄影机,存放在地下室,却是一种活着的历史,活着的电影,马来的后代对于电影先辈的崇敬,其实就是在反抗遗忘,反抗废弃,反抗无主,而他们其实都成为拾穗者,成为在当下那些垃圾的真正主人。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739]
思前: 《唐老师》:简化成数字的人生影像
顾后: 《凤冠情事》:问归来朱颜认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