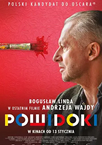2023-04-24《残影余像》:在毁灭和存有之间

从橱窗的模特身边倒下去的时候,那一只假肢还悬在那里摇晃着,这是艺术作品不被毁灭的象征?“1952年12月6日,弗拉迪斯瓦夫·斯特泽敏斯基逝世。”字幕之后,女儿妮卡走近医院的那张床,呆在父亲死去的地方久久不可离开,这是生命永恒的守望?安杰伊·瓦伊达在这位波兰艺术家逝世54年之后,用电影再现他生命的最后遭遇,是用影像保留人格的残影余像?作品倒下了,生命逝去了,艺术创作走向了终点,但是总有些东西是不被毁灭的,它被纪念,被书写,被铭记,它最后抵达了永远存有的世界。
无和有,毁灭和存有,构成了瓦伊达镜头下艺术家的命运主题,而这便是“残影余像”——片名来自于电影的第一个场景,来自波兰的汉娜在山坡上找到了正在进行写生的罗兹学校师生,单脚从山坡上滚下来的斯特泽敏斯基仿佛在实践着自己的一次行为艺术,学生们也学着他的样子纷纷滚落,之后斯特泽敏斯基对学生们说起了“残影余像”:“当我们凝视一个物体,眼中会形成映像,当我们不再看它,目光投向别处,眼中就会有物体的残影余像:物体留下了痕迹,它们形状相同,但颜色相反,那是你眼底深处观察到的物体颜色……”物体和映像构成了看的两个对象,一个是现实的,真实的,另一个则是和物体形状相同、颜色相反的残影余像,那个残影余像的存在,其意义何在?
在写生时说到的残影余像,是斯特泽敏斯基站在艺术角度的阐述,这一观点也在斯特泽敏斯基对梵高的作品解析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看,不是一种单一、不明、抽象的行为,而是一种行动,观察某一瞬间的过程,大自然拥有一个聚焦点能够吸引他人的关注,我们的视线跟随焦点移动,当我们凝视梵高画中的风景,他是否以一种寻常的、自然的、生理的眼光去观察自然?答案便不言自明,沿着地平线共有四个目光投射点,每个都以自己的聚焦点为中心,于是完全相同的透视部分就呈现在画面上了,这并不是因为梵高某些主观原因造就的形式主义美学,而是他准确再现了观察风景的过程,运用他身体的物理机制,用四束平行相继的定向目光去观察,这就是梵高的现实主义,源于鲜活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目光去看,而是运用了他身体中活生生的生理机制,这并非精神层面的经验接受,而是生理层面的。
残影余像的观点被斯特泽敏斯基写进了《视觉理论》的书稿中。在纯粹艺术的层面上,残影余像是现实的一种投影,也是创作的一种运用,但是在那个时代,“残影余像”却也成为斯特泽敏斯基命运的写照。山坡上阐述的残影余像,有两个层面的运用,一个是颜色的转变,当凝视物体的动作完成,在眼底留下的残影余像就变成了和物体“颜色相反”的存在,而斯特泽敏斯基的命运就在这“颜色相反”中遭遇了毁灭性打击。1948年12月,斯特泽敏斯基正在自己的画室里创作,街上的广播传来了洪亮的声音,这个国家正带领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接着,画室被笼罩在红色之中,一切物体都在红色中变成异样的存在,斯特泽敏斯基拿起拐杖走到窗口,窗户以及整个楼层都被红色覆盖,斯特泽敏斯基拿起拐杖朝着外面的红布戳进去,红布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而这块被拉起的红布正是斯大林的巨大画像。
瓦伊达在这里书写了一种关于颜色的隐喻,斯特泽敏斯基在作画,光线是自然呈现的,但是当红色的画布布满了整个大楼,自然的光线变成了红色的海洋,这是一种覆盖,一种异化,对现实的覆盖和异化就是一种政治符号,而斯特泽敏斯基用拐杖捅破了红色的画布,似乎在斯大林的画像上割裂出一个可以呼吸的口子,这是对政治威权的一次破坏,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街上的警察发现了斯特泽敏斯基的破坏行动,于是上楼踢开了门并且撞倒了斯特泽敏斯基。这是一个非常有表现力的场景,瓦伊达在色彩的转换中暗指了巨大的政治压迫,也让斯特泽敏斯基接下来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残影余像。
红色是政治,是革命,是社会主义,红色在此后还有出现,但显然已经从单一的政治色彩变成了和生活相关的颜色。斯特泽敏斯基的妻子克罗布也是艺术家,但是她在电影中并没有现身,是通过妮可以间接的方式出场。在学校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参观斯特泽敏斯基的“新艺术造型”展厅的时候,妮可站在作品前不肯离去,因为那里有父亲和母亲共同创作的作品,当老师问她:“你是他们的孩子吗?”妮可回答:“但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夫妻已经被分开,克罗布住在医院里,只有妮可会去看望她,所以在回到家里之后,妮可总是会说到母亲的话题,她回忆母亲买的雪橇,一家人在雪橇上。后来正在课堂上学习“十月革命”的妮可得到了消息,她赶去医院,母亲已经去世,在只有她参加的葬礼中,她身上穿着的是一件红色的外套,路边的妇人在讨论着:“葬礼怎么能穿这样的衣服?”妮可很难过地说:“我没有其他衣服。”之后她将外套换了个身,红色变成了黑色。
| 导演: 安杰伊·瓦伊达 |
穿红色的外套参加葬礼,这是生活造成的无奈,而用红色换成黑色,颜色的转换更是困境的表达。红色最后一次出现则是在斯特泽敏斯基在失去了学校工作之后,经学生罗曼介绍去了一家普通消费合作社做油漆工,在一阵咳嗽之后,斯特泽敏斯基看到那一口痰里的红色血液,这是病入膏肓的证明,但是斯特泽敏斯基没有告诉妮可,他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直到逝世也没有和被人说起。红色在电影中具有色彩的多义性,它是和政治有关覆盖了现实的颜色,它是困厄的命运写照,它是生命走向尽头的暗示,政治、命运和死亡,构成了红色的三重寓意。而在红色之外,斯特泽敏斯基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当他从妮卡的口中知道妻子已经病逝,自己却无法看上最后一眼,泪水从眼眶里涌出,然后他告诉妮卡要在妻子的坟上放一束蓝色的花:“蓝色是她眼睛的颜色。”他和她曾经在艺术和生活中相濡以沫,他和她在政治的逼迫中生活在别处甚至阴阳相隔,谁制造了这一悲剧?最后当斯特泽敏斯基自己也在昏倒街头之后送到医院,在得知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他带着病重的身体将家里唯一剩下的白色花朵,用颜料染成了蓝色,然后去了墓地放在了妻子的坟上,了却了自己最后的心愿,妻子蓝色的眼睛似乎将永远陪伴他。
红色是命运被迫害的残影余像,蓝色是怀念生命美好的残影余像,它们都不再是物体的本来颜色,都是在经历了磨难并且继续在磨难中而存于眼底深处的颜色。色彩学是瓦伊达在电影中阐述“残影余像”的一种运用,残影余像的另一个运用则是和真实物体所构建的关系学,看见并保存在眼底的已经不再是物体本身,而是“残影余像”,也就是说,物体在这种凝视的过程中变成了无,但是保留在眼底的残影余像又变成了有——可以说,斯特泽敏斯基的命运就是在不断地打击中慢慢走向无,但是无的背后并不是毁灭,而是存有,它是艺术,是精神,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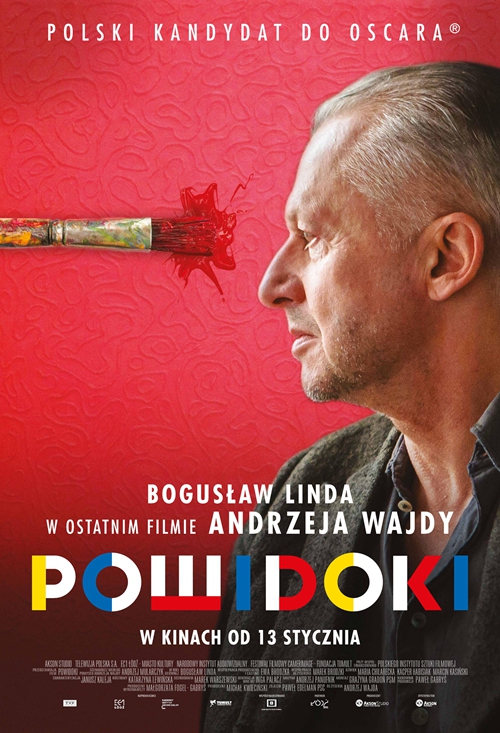
《残影余像》电影海报
斯特泽敏斯基是波兰的先锋艺术家,他提出了“新造型艺术”理念并付诸实践,他为波兰筹建了第一座也是欧洲第二座现代艺术博物馆,1945年他还倡议组建了波兰罗兹美术学院,并被聘为学院教授,他制定自己的教育计划,教授艺术史,他认为艺术应该反映艺术家的内心……斯特泽敏斯基在艺术上的贡献是巨大的,这是一种有,即使他在一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即使生于明斯克的他不认为自己是苏联人,这些都是身体上、身份上的无,但是这些无对于斯特泽敏斯基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失去,“我是个波兰人”反而证明他在追寻着有的存在。但是随着波兰政治的变化,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把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圭臬,在艺术上、在生活上,他的有逐渐被剥夺,他也变成了一种无的存在。
正在将梵高绘画的教室要变成文化部长演讲的舞台,这是从有到无替换的开始,课程被中断,学生们被迫离去,文化部长站在讲台上宣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提出政治与艺术的界限已经被消灭,艺术家是政治统一的战士……面对部长的讲话,斯特泽敏斯基拄着拐杖站起来,“新艺术应该得到尊重……”但是这句话也成为他被迫害的开始:校长认为斯特泽敏斯基散布反动言论,于是给他定罪,接着他的课程被取消,学校解除了聘用他为教授的合同;文化部长对斯特泽敏斯基非常生气,诅咒他“应该被电车撞死”;他失去了工作,艺术家协会同时将他开除,他想去商店买颜料,但是没有协会会员证没有购买资格,他去购买生活物质,因为没有粮票他空手而归;他的工作室被秘密警察破坏,所有作品都被砸掉,“新造型主义”展厅上的作品也被全部下架,“异国”咖啡馆创作的浮雕也被凿掉;他的书稿《视觉理论》无法出版,学生们从学校里拿来打字机整理书稿,但是被秘密警察盯住,汉娜被抓,罪名是制作反动材料……
艺术课程、教育工作、会员资格、创作的作品,艺术理论著作,斯特泽敏斯基所拥有的东西是一步步失去的,没有工作,没有食物,甚至没钱支付家佣,拖着一条腿,斯特泽敏斯基终于倒在了大街上,有人还嘲笑他喝醉了酒,只有一个妇人打电话叫了救护车,但是送到医院的斯特泽敏斯基正受到了肺癌的折磨,在他给妻子的坟地送上蓝色的花,在他最后一次触摸橱窗里的模特,在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那些作品,生命也终于走到了尽头,1962年12月26日是他生命彻底走向无的标志。无是破坏,无是毁灭,无是死亡,但是无却是一种残影余像,它最后变成了存有:它是斯特泽敏斯基的艺术作品,被砸坏被下架但永远没有消失;它是斯特泽敏斯基的艺术精神,他坚持艺术表现内心,坚持新艺术的开拓;它是斯特泽敏斯基的人格,不与政治势力妥协,不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生命走向终点,但是艺术却走向了永恒,“残影余像”永远留存在眼底在心底——当2016年的瓦伊达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它也成为了瓦伊达艺术生命中的“残影余像”,在上映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瓦伊达和编剧在同一天与世长辞。和斯特泽敏斯基一样,残影余像成为了遗作,但电影没有死去,艺术永远活着。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