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14《野蛮人入侵》:用自我守卫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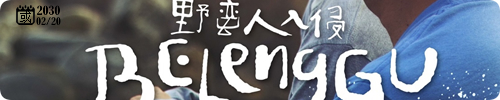
叙事结构上最本能的问题是:“戏中戏”是什么时候真正开场的?这里的背后问题是:拍戏的生活和真正的电影在哪里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无疑,拍电影的终点是清晰的:当祖力亚扮演的“阿男”和李圆满扮演的“阿妹”寻找孩子,在码头附近找到了纹身男,纹身男拿着刀追逐他们,最后刀扎向了阿男的身后,阿男在镜头前做出跪倒的姿势,然后倒在地上,“停!”剧组人员喊停,导演胡子杰便从监视器上看刚才拍摄的镜头,因为不是很满意,于是重新拍摄了这个场景。
一声“停”就是对故事的中断,就是从生活变成了电影,这是生活电影分开的界标,除此之外,在李圆满见到僧人之后,一个人在海上练习棍术,仿佛在大海深处行走,镜头一转,才知道这是拍戏的另一个场景,水上的动作表演其实是一次特效的实现:水面之上铺设着一块透明的玻璃,踩在玻璃上就像在水上行走一般,随着这最后一个镜头完成,电影也杀青了,李圆满和剧组人员还在讨论着剧情,而孩子宇宙也和祖力亚坐在海边。最后的杀青当然也是和电影有关的标志,它和那一声“停”共同组成了电影叙事,但是在电影被标记了中断和继续之外,从生活“进入”电影的标志又在哪里?
李圆满和祖力亚扮演的阿男被人追杀的场景是电影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相遇和之后的相爱也是电影的一部分,照此推论,李圆满寻找儿子宇宙遭遇纹身男也是电影,宇宙在她故意不理睬的时候被人抱走也是电影——电影是从宇宙失踪开始进入“拍摄”的?但是,这中间根本没有明确的“开始”,还可以往前推,那么李圆满在训练馆里练习棍术也是电影?胡子杰告诉他前夫祖力亚要进入剧组和她演情侣也是电影?李圆满带着儿子来见胡子杰“重出江湖”也是电影?如此推论,那么整个故事都是那部电影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胡子杰邀请李圆满出山,李圆满刻苦训练证明自己,就是为了拍摄一部电影,另一方面,胡子杰在介绍这部电影时就说讲述的是一个在海边被救起女人的故事,李圆满被人打晕丢在海里之后就是被人救起的,阿男还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终于让两人迸发出爱的火花,第三,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传来了“预备,开始”的声音,这是进入电影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整个故事就是一部正在拍摄的电影,但是故事又不时地把电影剥离开来,李圆满曾经就是第一个电影明星,胡子杰这次邀请她拍摄的这部电影,是一部东南亚版的“谍影重重”,而宣传的卖点是“影后离婚后重出江湖”,为此胡子杰还要求在没有替身的情况下完成全部的武打动作,李圆满三个月的训练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圆满曾经是电影明星,她的婚姻遭遇变故,重出江湖是为了证明自己,这些又都是在电影之外的故事,沿着这条生活线,李圆满和祖力亚之间的恩怨当然是无法绕过的重点,当胡子杰说起祖力亚在其中扮演男主角,并让李圆满和他搭档讲述一个爱情故事,李圆满却选择了退出,“只要有他在我就离开”,之后胡子杰还告诉她一个消息,因为出资人的要求,主角不再是李圆满而是另一个人,这就更坚定了李圆满退出的决心,但是当李圆满收拾行李离开剧组,胡子杰又告诉她,出资人那边已经推掉了,电影不能被资本劫持,主角依旧是李圆满,但是李圆满留下一句“太迟了”,便要带着宇宙离开,而正当离开时,宇宙被人劫持,李圆满开始解救儿子,后来遇到了祖力亚……
| 导演: 陈翠梅 |
如此看起来,生活和电影并不是同一个故事,至少生活中李圆满受到了祖力亚的伤害,电影中李圆满和祖力亚成为了情侣演绎爱情,在“预备,开始”和“停”的拍摄口令中,在最后剧组杀青的结尾里,故事是故事,电影是电影,但是这不同的故事在没有明确分界线的情况下,看起来又是一体的,实际上,导演陈翠微既设置了两者相异的标志,又将它们糅合在一起,在无法完全分清生活和电影的情况下,“戏中戏”的结构隐含着陈翠微的另一个目的:将生活电影化和将电影生活化,电影有时候就是生活,生活有时候也是电影。回到胡子杰最初给李圆满讲述关于宫本武藏的故事,就是一种主题先行:宫本无藏和年轻人相约决斗,但是直到太阳快要下山宫本无藏才出现,而背对着阳光的宫本无藏在关键时刻故意让刺眼的阳光照到年轻人身上,一瞬间就把他杀了。这看起是胜之不武,但是胡子杰对此的解读是:“对那个年轻人来说,剑就是一切。对年老的宫本武藏来说,一切都是剑。阳光是剑,时间也是剑。”从“剑就是一切”到“一切都是剑”,这里完成的是一个本体论的置换,当“剑是一切”的时候,决胜的关键在于武器,但是当“一切都是剑”的时候,剑是有形之剑也是无形之剑,决胜的关键就变成了对机会的把握。
讲述宫本无藏的故事,胡子杰为的是说明另外一个道理,“以前,电影就是一切。到了现在,一切都是电影。如果我们置身事外,在自己的生命里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生活就是一场电影。”和剑一样,以前“电影就是一切”,是以电影为中心构建的生活圈,而现在“一切都是电影”,电影超越了电影本身,电影成为一切的代名词,所以李圆满出演的电影是电影,李圆满的故事也是电影,因为“生活就是一场电影”。电影被泛化,它朝着电影生活化和生活电影化两条路前行,而两条路殊途同归,就是让你分不清哪里是生活的片段,哪里是电影的场景,哪里是演员哪里是自己,哪里是开始哪里会叫“停”——这样的泛化模糊了电影和生活的分界,于是当“野蛮人入侵”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何处要防范何处要坚守,谁是敌人谁又是自己该爱的人。
“戏中戏”的叙事结构之外,陈翠微更重要的用这样的形式来阐述电影的真正母题:你是谁?李圆满被包装成“影后离婚后重出江湖”,这是一次自我的重塑,但其实真正对李圆满产生困扰的是自己的定位,这种困扰来自于自己破败的婚姻,更来自于生下来的儿子宇宙。从李圆满来见胡子杰开始,她似乎一直围绕着宇宙:宇宙想要风火轮,李圆满拉着他没有买,在自己要进厕所的时候,也必须拉着他进去;在训练馆里接受棍术训练的时候,宇宙在玩耍却总是捣乱,这让李圆满无法安下心来,而李圆满被击打发出喊声,宇宙便上前来要找人报仇;当李圆满终于决定让胡子杰的助手小余照顾宇宙,不想宇宙却失踪了,李圆满和胡子杰四处找人,终于在海边的一爿小店找到了宇宙,宇宙找到了一个小女生并和她成为了朋友。

《野蛮人入侵》电影海报
“你不能被孩子操控生活。”这是胡子杰对李圆满的建议,的确,身为一个单亲母亲,李圆满唯一牵挂的人就是宇宙,宇宙是她生活的“宇宙”,正因为这份牵挂,她无法全身心投入到训练和拍戏之中,而这就是陈翠微的电影主题:野蛮人入侵——引用自汉娜·阿伦特的名言:“每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宇宙年幼无知,没有防范意识,也没有规则意识,在缺少父亲的角色介入中,李圆满就这样被这个野蛮人入侵了,她在和胡子杰、小余说起怀孕时的感受时也说:“孩子不是我的作品。母亲只是孩子来到世界的通道,类似于某种更高级的3D打印机。”因为怀孕,李圆满遭受了别人异样的目光,更因为生下了宇宙,她变成了“母亲”,一个被野蛮人赋予的角色,一个必须承受野蛮人入侵带来困扰的角色——而实际上,这种“野蛮人入侵”的困扰也在陈翠微的身上体现,“怀孕生产后,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身体变成了一片废墟,健忘又疲惫,工作被小孩干扰,电影计划不断延后,最终取消。小孩三岁前,我都活得狼狈不堪。成为母亲后,我才发现作为女人的各种不平等待遇。这是我创作《野蛮人入侵》这部电影的起源。”当陈翠微自导自演成为“李圆满”,这或者也是生活电影化和电影生活化的双重构筑。
野蛮人入侵,对于李圆满来说,就是重新回到自我,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我是谁”的成长故事,在训练馆里,教练让她学习棍术,从可见的棍到日常生活用品的武器化,这是寻找自我的“器”阶段,武器的泛化是对于“一切是剑”的实践;最后教练问的问题是:是谁在挨打?是谁在痛苦?是谁在躲?问题刚提出来教练的拳头就落在了李圆满的鼻子上,鼻子里冒出了血,谁在挨打——是我;谁在痛苦——是我;谁在躲——是我,李圆满的本能反应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这就是我,是肉体之痛的我,是身体之击打的我,也是精神之我;僧人送给她的那本书是《是谁拖着尸体在行走》,对她的启示是:“思想才是你身体的监狱……”行尸走肉的生活,灵魂被禁锢的现实,这就是没有自我而被野蛮人入侵的困境。所以对于李圆满来说,不管是生活还是电影,都让她开始寻找自由而独立的自我,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
宇宙失踪是生活矛盾激化的象征,也是电影叙事走向高潮的开始,但是对于李圆满来说,失去宇宙并非只是失去儿子,她也失去了自我的表达,所以寻找宇宙既是对儿子的寻找,也是对自我的寻找。从打晕到冲上海滩,她失忆了,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对着镜子问自己:“我是谁?”遇到了祖力亚扮演的阿男,她在自己身体的纹身处看到了两个字:宇宙,这是儿子的名字,失忆的她把宇宙当成了自己的名字,这一种自我命名其实也是一个隐喻,自我就是宇宙,是包罗一切的宇宙,奋不顾身寻找儿子,和祖力亚迸发出爱的火焰,这些都是重建自己宇宙中心的开始,而最终在完成电影拍摄时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自我在生活中,在电影里,也许,在经历了生活和电影的双重考验之后,成长也意味着“一切都是自我”。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