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18《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是宗教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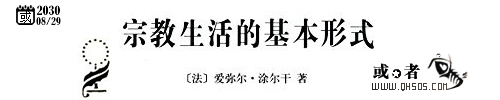
就其自身存在的方式而言,任何宗教都是真实的;任何宗教都是对既存的人类生存条件作出的反应,尽管形式有所不同。
——《导言》
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宗教现象?什么又是宗教生活?它源于泛神论还是自然崇拜?它具有灵魂观念还是精灵或神的观念?一系列问题被提出,爱弥儿·涂尔干其实一开始就指出了这些问题背后的内核:“本书的宗旨,就是要研究实际上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宗教,分析这种宗教,并尝试作出解释。”对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宗教进行分析,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宗教的本性,而分析之后要做的事是“尝试作出解释”,这个解释的意义,在身为社会学家的涂尔干那里,也是明确的,那就是要证明宗教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社会就是宗教的起源。
在《导言》中,涂尔干开宗明义了“研究主题”,那就是对宗教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的主旨是了解和重建业已消逝的各种文明形式,还要和实证科学一样,“解释的是与我们近在咫尺,从而能够对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现实的实在”,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所要解释的这个实在不是别的,就是人。宗教社会学解释人这一实在,就是为了理解人的宗教本性,也只有宗教才能展现出人性的本质的、永恒的方面。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学的前提是:人类制度绝不可能建立在谬误和谎言基础之上,即使最野蛮和最古怪的仪式,即使最奇异的深化,都传载着人类的某些需要和个体生活或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当信仰试图证明这些仪式和神话是错误的,它也需要科学的方法,而因为宗教与实在有关“并且表达了实在”,所以宗教都是真实的,都是对既存人类生存条件作出反应。
“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总的结论是: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在这样一种结论面前,涂尔干所要做的事就是证明这一结论,而科学的证明在他那里的方式只有一个:赋予原始宗教特殊的地位,而且是最原始的宗教,因为只有它能在组织得最简单的社会中找到,只有它可以不必借用先前宗教的任何要素便可作出解释,“原始宗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分解宗教的组成要素,而且还具有方便解释的巨大优点。”涂尔干将宗教放置在一个空白的源头,重新梳理宗教的产生和作用,阐释宗教与人这一实在有关,具有社会性,那么,他就必然要回答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宗教?
什么是宗教,这个问题需要回答的则是:宗教的起源是什么?对于宗教的起源的理解,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神秘观念,比如说神性概念,对于这些观点,涂尔干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神秘观念不是最原始的起源,也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正是人类自身塑造了神秘观念;宗教的力量也并非都是从神性人格中产生的,很多膜拜也并非是要将人和神祗联系起来,宗教远远超出了神或精灵的观念。涂尔干回到宗教的起点进行思考,他认为宗教很明显是将世界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领域包括所有神圣的事物,另一个领域则包括所有凡俗的事物,当神圣事物确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形成统一体,由信仰和仪式构成的便是一种宗教:信仰是舆论的状态,仪式是明确的行为——但是,巫术也划分了神圣和凡俗,巫术也结合了信仰和仪式,那么,巫术和宗教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里其实就表达了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巫术是巫师个体的行为,请教巫术的人也是个体,无论是巫师还是巫术的追随者都不能联合成群体,无法形成共同的生活,当然更不会信奉一个神,遵行同一种膜拜,而宗教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集体成员都要奉行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正是信仰和仪式都具有集体性,当它把集体变成一个统一体,宗教就和巫术区别开来了,宗教也成为了社会性存在——涂尔干把“教会”看做是这个统一体的外在表现,它使得宗教的社会性成为一种道德共同体。由此,涂尔干得出了宗教的定义:“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个统一体既是在宗教意义上的,也是社会的一种缩影。
但是,在对宗教进行定义的过程中,涂尔干必须澄清另一些宗教的主导概念。一个是“泛灵论”,很多人认为泛灵论就是原始宗教,这是泰勒、斯宾塞提出的观点,涂尔干分析认为,如果泛灵论是一种原始宗教,那么就应该得出几个结论:灵魂观念是重要的宗教观念,按照最原始的宗教的解释,灵魂应该在不需要汲取先前宗教的任何要素便可形成;第二,灵魂要成为膜拜对象并转变为各种精灵;第三,泛灵论认为自然崇拜是泛灵论的附属和派生形式,所以还必须解释自然膜拜如何从泛灵论的精灵膜拜派生出来。考察泛灵论,涂尔干认为,灵魂就是野蛮人观念中的“互体”,互体是另一个自我,它可以游离自己的身体漫走他乡,而且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可塑性,但显然在涂尔干看来,灵魂无法脱离身体,灵魂必须依附身体,当它和身体一起的时候,它不可能成为任何膜拜的对象,相反,灵魂的性质、起源和功能都是宗教的,也就是说,灵魂是宗教的表现而不是相反。
| 编号:B83·2231021·2015 |
而最重要的是,涂尔干认为如果泛灵论是宗教的起源,那么宗教只能表现为虚幻,这就使得宗教没有任何客观基础,而宗教科学的原则就是表现自然中的存在和社会中的实在,“如果有一天,泛灵论的真理被人们认识以后,宗教也就不可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了,因为人们不可能不摒弃那些连其性质和起源都已经暴露无遗的谬见。”除了泛灵论之外还有一种观念是自然崇拜,和泛灵论相反,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首先是产生了自然崇拜,然后再派生出泛灵论。马克斯·缪勒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宗教建立在经验之上从经验中取得自己的权威,“未有感觉,便无领会”,所以在宗教上,他认为如果我们最先没有感觉到信仰,信仰就不存在。很明显,涂尔干也认为,自然崇拜也缺乏客观基础,它把宗教变成了一个幻觉体系,而实际上,信仰本身就拥有支配自然的神圣力量,它的神圣性和真实性和合二为一的。
泛灵论是梦的幻觉带来的变形,自然崇拜则是通过词语的空洞意象带来变形,两者都将宗教变成了谵妄的想象的产物——涂尔干也认为宗教是谵妄,但是它并不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只有多神圣事物和凡俗事物之间的对立中才能发现宗教的萌芽,才能发现最原始的宗教。对泛灵论和自然崇拜进行分析和批判之后,涂尔干将宗教起源的问题归于自己的观念之下,他认为最原始的宗教不是别的,就是图腾膜拜,这是最基本、最原始的膜拜,而且按照罗伯逊·史密斯的看法,图腾制度意味着人与动物“在先天本性或后天本性上的相似性”,在《闪族宗教》中他更是认为图腾制度是祭祀体系的最早起源,“正是在图腾制度中,人类获得了圣餐仪式的原则。”涂尔干考察了澳洲现存的一些图腾信仰,他们将由氏族集体名字命名的物种称为图腾,氏族的图腾便是每个成员的图腾,这个图腾具有的特点是: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图腾具有独立性和氏族的标志性;图腾可以是标记、纹章、也可以是一种名字——动物的、植物的和氏族人员的;图腾被用于宗教仪典之中,是仪式的一部分……
考察原始图腾的特点之后,涂尔干认为,图腾制度就是宗教的起源:一方面,图腾的形象和图腾物种都是神圣的,而且正是因为图腾属于氏族的每一个成员,所以氏族成员也都被赋予了神圣性;图腾形成的信仰不是零碎的集合,它是一种观念体系,它包含了普遍事物,它是一种世界的完整表现;信仰图腾的氏族不是个体的结合,而是一种集体,“集体图腾是每个个体族内身份的一个部分,它一般是世代相传的,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与生俱来,单靠人们的愿望是于事无补的。”图腾制度体现了神圣性原则、集体性表现和普遍性存在,但是对于图腾制度形成的信仰,涂尔干还深入一步,阐述了这些信仰的起源,从而确定这就是最原始的宗教。
他首先批判了关于图腾制度的不同观点,泰勒和维尔肯认为图腾制度是从先前的宗教派生出来的,涂尔干以澳洲部落为例,他们没有对死者的崇拜,也没有转生的说法,他们的图腾制度根本就没有先前的所谓宗教为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图腾制度导源于自然膜拜,杰文斯就持这样的观点,涂尔干认为,这种观点犯了理论简单化的错误,其假设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假设就是:“人们为了确保能够得到那些神通广大的超自然存在的帮助,就会优先注意其中那些最有力量的和所许下的保护好处最大的超自然存在。”弗雷泽和托特等人的观点,则是以个体图腾来解释群体图腾,涂尔干认为,如果集体图腾制度是个体图腾制度的普遍化形式,那么个体会让其他人也敬奉他的图腾物种,但显然事实不是这样的,同时,如何解释一个部落不同氏族具有截然不同的图腾现象?个体的膜拜只是个体行为,它不可能产生集体膜拜,而实际上,图腾作为一种圣物的形象,它和氏族有关,和氏族成员有关,只有成为集体图腾,它才具有神圣性,“谁也不能完全拥有它,但又都可以分享它。”
在这里,涂尔干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图腾并不只是一种形象,一种被命名的物种,而是一种宗教体现,而且是“一种匿名的和非人格的力的宗教”,这个力所体现的就是事物的本质要素和生命本源:它是物质的力,能够机械地产生物理效应;它更是一种道德的力,具有普遍的道德属性;而且这种力可以转化为确切意义上的神性。物质力、道德力和神性力,构成了图腾制度的生命本源,更重要的是,力的观念就是宗教的起源,它就是宗教力,“宗教力是现实的,而无论人们借以想象这些力的符号是多么不完善。”对图腾制度中的力的阐述,涂尔干便将这种宗教力引向了社会,“社会只要凭借着它凌驾于人们之上的那种权力,就必然会在人们心中激起神圣的感觉,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社会之于社会成员,就如同神之于它的崇拜者。”当一个人服从他的神就会相信神与之同在,就会发挥社会作用,所以宗教不再是无法解释的妄想,“因为这个力量确实存在,它就是社会。”
在这里,涂尔干再次返回到了很多人提出宗教中的灵魂观念和神性观念,在这里,他不是把灵魂观念和神性观念看成宗教的起源,而是认为宗教中必须有这两种观念,而且这两种观念也具有现实性和社会性。灵魂观念是对圣物信仰的一种独特应用,灵魂观念具有一种宗教性,当人们赋予灵魂神圣性的时候,并不是把灵魂看作是纯粹幻想的产物,“和宗教力或神性的观念一样,灵魂观念并非没有现实的基础。”是社会从外部调动和影响我们,使得我们在内部确立自身形成了灵魂,所以灵魂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灵魂也是人格的符号表现。精灵和神的观念则是宗教力个体化的重要标志,“正是通过它,人格观念才被引人了宗教领域。”
将灵魂观念赋予现实性,将神的观念人格化,这些都是宗教具有社会性的表现。这些是涂尔干对于信仰的考察,而在仪式上,他更是突出了宗教的社会学意义。涂尔干把仪式分为消极膜拜和积极膜拜,消极膜拜是一种禁忌形式,它的主要表现就是苦行主义,“苦行主义是一切社会生活所内在固有的,即使在所有神话和教义都破灭以后它仍会留存,它是一切人类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还有一种是积极膜拜,它是一种对宗教生活的建构,使崇拜者脱离凡俗世界,它的主要仪式就是祭祀,“祭祀之所以产生,并不是为了在人与神之间制造一条人为的亲属,而是要维持和更新最初就已经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天然的亲属关系。”在积极膜拜和消极膜拜之外,涂尔干还介绍了禳解仪式,它是对灾难的纪念和痛悼,表现形式便是哀悼仪式,“哀悼并不是因为骤然失去亲人而受到伤害的私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群体强加给他们的责任。”
在信仰上圣俗之分,在仪式上有积极消极之分,对于图腾制度考察之后,涂尔干更是确定了最原始宗教具有的社会性。当我们参与了宗教生活,他就会获得膜拜带来的欢乐、内心的平和、安宁和热烈,这是一种宗教力的效力,所以是社会把人提升起来,使他超越了自身,或者说,是社会造就了人,“因为造就了人的乃是由智力财产的总体所构成的文明,而文明则是社会的产品。”同时,信仰者通过共同行动,社会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赢得自身的地位,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是宗教的起源,而且所有重大的社会制度都起源于宗教。不仅如此,在宗教的社会起源中,宗教力带来了人类的力量和道德力量,“它倒像是个集体生活的学校,个体在这里学会了理想化。”更为重要的是,当宗教思辨成为哲学家反思的主题,自然、人和社会也就融合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界限:科学不是反宗教的,宗教也不是反科学的,它们就是“宗教科学”,而这便是开辟了关于人的科学新途径的社会学,这才是涂尔干考察“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真正用意:“只要我们认识到在个体之上还有社会,而且社会不是理性创造出来的唯名存在,而是作用力的体系,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人类。”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