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31《希腊三部曲》:命运对否定句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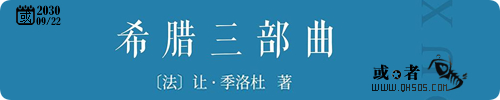
在王族身上总能实现卑微者无法成功的经验,诸如纯粹的仇恨、纯粹的愤怒。总是与纯粹有关。这就是悲剧,加上乱伦和弑杀亲人。
——《厄勒克特拉·中场》
园丁说到了生活唯一的目的,那就是爱,它是欢乐的一种体现;园丁认为欢乐和爱比尖酸和仇恨更可取,但是,“生活显然失败了”;园丁说出生活显然失败之后,却又说“生活却又很好很好”,“一切显然不顺利,什么也没解决,你们却不得不偶尔承认,生活好得很,一切顺利解决……”不管是欢乐和爱是生活的目的,还是尖酸和仇恨不可取,不管是生活已经失败了,还是生活很好很好,园丁的一切说法都是在围绕着人类的生活,都是对人的关注,而人的关注在这样的矛盾中,就变成了悲剧:“总是与纯粹有关。这就是悲剧,加上乱伦和弑杀亲人。”纯粹的仇恨,纯粹的愤怒,纯粹是王族在卑微者那里无法实现的经验,但是纯粹通往的结局是悲剧,因为,“纯粹,总的来说就是无辜”,纯粹的女法老自杀了,她把自杀说成是希望,这是悲剧;纯粹的元帅背叛了,他却说这是忠诚,这是悲剧;春错的公爵杀了人,却说成是温情,这是悲剧——自杀、杀人和背叛,都变成了无辜的行为,无辜带着纯粹的面具,最后都走向了悲剧,而园丁最后认为,“这是爱的事业,所谓残酷……抱歉,我想说的是,所谓悲剧。”
纯粹、无辜,以及最后造成的悲剧,也都是人类的写照,但是在这对人类的命运进行诉歌的时候,园丁最后转向了神,最后恳请神,“作为您的疼爱、您的声音、您的呼喊的明证,我恳请您沉默片刻……这更有说服力。请倾听……谢谢。”神站在高处,神俯视人间,神当然要倾听人类的呼声,只有在“沉默片刻”中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人类的悲剧是如何造成的。从人开始,到神首场,这是关于园丁诉歌的“中场”,而园丁第一次在“被排除在戏外”的情况下谈论命运,局外人的身份对于神的恳请,像自己也站在神的位置,像自己最后也在沉默中倾听——园丁和神到底能倾听到什么?对于人类的悲剧会不会有救赎的意义?
《厄勒克特拉》二幕剧的中场,戏中人成为局外人,让·季洛杜抽离出剧中的人物,起到了中断戏剧幻想效果的作用,这一创新手法似乎是对古代悲剧歌队形势的回归。回归古希腊传统,回归古希腊悲剧,萨特认为在那一代法语作者里,季洛杜是“最直接地浸染于古希腊文学”的作者,但是季洛杜为什么又将三部从古希腊悲剧改编的戏剧称为“希腊三部曲”?从古希腊到希腊,季洛杜又在这转变中注入了怎样的现代意识?而从园丁诉歌的人和神的转换,季洛杜又如何“重述”这一经典的悲剧?引用莫里斯·布朗肖的说法:“重点不是述说,而是重述,并且每一次重述都是头一次述说。”头一次述说就是一种原创,它和抄袭无关,和改编无关,它就是季洛杜对于人类命运的原初阐述——那个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希腊三部曲”、这个以回归的方式重述的“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又如何被倾听?
沿着园丁所说的观点,在厄勒克特拉的故事里有欢乐和爱,有尖酸和仇恨,有失败的生活,有纯粹的思想,也有乱伦和弑杀,当然也变成了悲剧,在从爱和欢乐到悲剧的命运通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它和人有关,从在戏中的园丁和外乡人的对话开始,他们谈论到了阿伽门农王宫那面古怪的墙,谈到了“眼下这王宫又是哭又是笑”,谈到了厄勒克特拉的窗,谈到了两岁就被送走至今杳无音讯的俄瑞斯忒斯,而这一切都印象了一个悲剧:“我们的王阿伽门农,厄勒克特拉的父亲,他打仗回来那天在那里滑倒,摔在自己的剑上,摔死了。”而这个悲剧牵涉出的是复仇:厄勒克特拉认为是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和情人埃癸斯托斯设计害死了阿伽门农,所以她要向母亲和埃癸斯托斯报仇——这就是季洛杜所说的“厄勒克特拉的爆发”,而按照国王埃癸斯托斯的说法,“在她爆发的那一天,阿特柔斯家族将面临多少烦恼和不幸。”这里的爆发已经变成了战争的“爆发”,一场家庭的恩怨演变为国家之间的战争,“爆发”带来的是双重的悲剧。
可以说,厄勒克特拉对母亲怀有的仇恨很小就开始了,他也罢弟弟俄瑞斯忒斯被送走和小时候被母亲摔在大理石上的行为联系起来,尽管克吕泰涅斯特斯一直否认有过这样的行为,尽管克吕泰涅斯特斯认为对女儿也会充满了爱,但是厄勒克特拉一直在培育爆发的情绪,之后便是她要实施的报仇,在最后得知外乡人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弟弟俄瑞斯忒斯的时候,她也把这个复仇的任务交给了俄瑞斯忒斯。那么,这一场悲剧是不是源于一种纯粹?这种纯粹背后是不是无辜?纯粹和无辜是不是会改变欢乐和爱这一生活的目的?季洛杜引入了“庭长”,法庭之上的庭长,是一种公正的象征,他就说到,厄勒克特拉身上具备正义、宽宏、责任,“但是,一个人毁掉国家、个人和最好的家族,不是由于自私和图便利,恰恰是因为正义、宽宏和责任。”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国家,都需要正义、宽宏和责任,但是庭长却认为这恰恰可以毁灭一个人、一个家族和一个国家,因为它们就是纯粹,“因为这三种美德包含真正致人类于死命的唯一因素:顽强。”而真正的幸福不是顽强者的命运,“幸福的家庭是局部性的投降。幸福的时代是全民性的妥协。”
厄勒克特拉表现的纯粹就是顽强,这就是对仇恨的坚持,埃癸斯托斯对她的爆发感到心有余悸,他说到了这是一种“布尔乔亚”思想,这是季洛杜现代意识的一种反映,但是对于纯粹,他更是通过俄瑞斯忒斯和克吕泰涅斯特斯之口提出了疑问。在姐弟相认之后,厄勒克特拉告诉了俄瑞斯特斯真相,“我不恨女人,我恨我的母亲。我也不恨男人,我恨埃癸斯托斯。”恨母亲是因为她让俄瑞斯特斯小时候摔倒,恨埃癸斯托斯是因为他废黜了俄瑞斯忒斯的王位,当然更重要的是,父亲阿伽门农就死在他们的阴谋中,“我叫醒你就是为了找到他。但愿是同一个人。你只需捅一刀就够了。”在这样的真相面前,俄瑞斯忒斯却一次次发问:“为什么这么恨我们的母亲?”而对于厄勒克特拉所揭示的真相,克吕泰涅斯特拉否认自己有情人,并认为厄勒克特拉的行为是世间不幸的原因,“自诩纯洁的人想要挖掘秘密,把真相暴露在太阳光下。”但是对于自己的行为,克吕泰涅斯特斯将其命名为爱,而且是女人的爱,“厄勒克特拉,我们是女人,我们有爱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她反而对厄勒克特拉说:“既如此,别再做我闺女。别再恨我。只做个女人吧,就像我对你一心盼望的那样。”
阿伽门农死于阴谋,厄勒克特拉对母亲和埃癸斯托斯充满仇恨,俄瑞斯特斯需要一种力量,而克吕泰涅斯特斯却提到了女人的权利和爱,当然,这些都是人类的情感纠葛,甚至在厄勒克特拉说到仇恨之后,也流露出同情,““其实我同情高贵的王后,她原来傲视人间,突然惊慌卑微起来,逃避一个婴儿就如逃避偏瘫的祖先。其实我同情埃癸斯托斯,他残忍专横,命中注定有一天要惨死在你的还击下……”无辜也好,悲剧也罢,它导致的命运也一定是人类的命运,都在人的层面里展开。但是正如园丁所说,这一切需要神来倾听,那么神对人间悲剧又是如何看待?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剧中的乞丐在城里来来去去,被侍从认为是神明,而听到侍从的说法,埃癸斯托斯表达了对神的敬意,“我相信诸神。或者不如说,我相信我相信诸神。”虽然神存在着冷漠,虽然神在消遣,但是诸神存在的意义是在从无意识到意识中创造了人类,“这种无意识如电光闪过,全知全能,被雕琢成千万个镜面。”埃癸斯托斯对神的所谓敬意是不想造成公民之间更多的阶级差别,而这就是对神“示意”的一种表达,当人类脱离自身命运就是“示意”,它必将遭到诸神的嫉愤和复仇。
在人类的这场悲剧面前,神在倾听之后出现了,他们化成了三个小“报仇神”,但是,被命名为“报仇神”却并不是为了让人类加速复仇,报仇神是厄里倪厄斯的讳称,在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中,报仇神苦苦追赶杀母的俄瑞斯特斯,直到雅典娜女神解除了阿伽门农家族的诅咒,而在季洛杜的笔下,报仇神实际上就体现了字面上“善心神”的意思,它是命运神,它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在俄瑞斯特斯见了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斯之后,报仇神模仿了俄瑞斯特斯的走位,戴着面具的他们最后说的是:“我既不想杀我心爱的姐姐,也不想杀我仇恨的母亲……”所以最后的俄瑞斯特斯劝告厄勒克特拉,“我们逃离这座王宫吧。我们去色萨利吧。你会看到我那淹没在玫瑰茉莉花丛里的家。”这一建议当然被厄勒克特拉否定了,最后她要求为自己的父亲报仇,“拿着你的剑。带上你的仇恨。鼓足你的力量。”
厄勒克特拉一心要复仇,带来的是更为悲剧的结果,那就是城邦被毁,阿尔戈斯已经被敌人围攻,此时的埃癸斯托斯甚至在祈求厄勒克特拉放弃仇恨,“厄勒克特拉,等明天阿尔戈斯获救之后,我负责让罪犯们永远消失,如果有罪犯的话。别再固执下去!厄勒克特拉,你是温柔的。你骨子里是温柔的。听我的劝吧。这城邦快亡了。”但是一方面厄勒克特拉坚持自己的想法,“就让它亡吧。”虽然厄勒克特拉最后还是对对烧毁战败的阿尔戈斯产生了爱,但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却也在坚持身为女人的权利,“是的,我爱埃癸斯托斯。十年来我爱埃癸斯托斯。十年来我推迟这桩婚事,就为了照顾你,厄勒克特拉,就为了悼念你父亲。”一个是纯粹的复仇,一个是纯粹的爱,母女之间的纯粹制造了阿尔戈斯城陷入战火的悲剧,即使这一场悲剧无可避免,厄勒克特拉依然在说自己还有正义还有良知,克吕泰涅斯特拉还在说不要给厄勒克特拉以自由,对于这一切,“纳尔赛斯家的”说出了战争带来的罪恶,“在太阳升起时,一切已被错过,一切已被破坏,空气倒还能呼吸,什么都丢了,城邦烧毁了,无辜的人互相厮杀,有罪的人奄奄一息。就在这新升起的白日一角。这叫什么?”
| 编号:X38·2231217·2048 |
都是女人,都是爱的表达,都是纯粹,但都导向了悲剧,这是不可调和的人性矛盾?这是人性引发的悲剧?“纳尔赛斯家的”所问的“这叫什么”也是季洛杜想要找到答案的问题,最后通过乞丐的口说出的这一切叫做“曙光”:“这个名称很美,纳尔赛斯家的。这叫曙光。”但是,这很美的曙光到底是带来希望的曙光?还是世界末日的曙光?是一种对悲剧的赞许还是对人性的讽刺?回答不是消弭了矛盾,不是提供了解答,而是设置了更多的矛盾,乞丐代表的神明命名曙光,也成了神明的矛盾。同样和女人有关,同样探讨人性,同样是神明矛盾的体现,也同样和一场战争相关,季洛杜的《特罗亚战争不会爆发》看起来是对于战争的否定,是对于和平的获得,但是标题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它在改变历史、改变古希腊悲剧的同时,也在改变战争和人性的定义,更是在神的意义上命名了这一种和《厄勒克特拉》一样的“曙光”。
“特洛亚战争不会爆发”,从戏剧一开始,赫克托尔的妻子安德洛玛克就对阿波罗的女先知说:“特洛亚战争不会爆发,卡珊德拉!”如此肯定,如此坚决,更像是对拥有预言能力的卡珊德拉的一种嘲讽,“老看到和预见到可怕的事情,你不累吗?”而安德洛玛克用这样的口吻说出战争不会爆发,她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取代了女先知的位置。而安德洛玛克认为战争不会爆发的原因只有一个:帕里斯不在乎海伦,海伦也不在乎帕里斯,既然海伦和帕里斯之间没有爱,所以为争夺女人而带来的战争就是一个空无。但是当安德洛玛克预言战争不会爆发,卡珊德拉却把两个人之间的“不在乎”说成了一种否定,否定不是指向“战争不会爆发”,而是指向了命运的悲剧,“你看,命运对否定句感兴趣。”当安德洛玛克问“命运是什么”的时候,卡珊德拉的回答是:“命运就是加速形式的时间。命运真可怕。”
对真正的预言变成了对命运的否定,而命运就发生在人身上,就是人性矛盾的体现。赫克托尔无疑也支持战争不会爆发,虽然他身经百战,对战争也抱有某种喜好,“某种温存浸润你,淹没你,那是战斗的温存变幻无穷。因为无情,所以温存,想必这就是诸神的温存吧。”但是温存也是悲剧,所以最后赫克托尔说:“我倒觉得我恨战争……既然我不再爱战争。”他建议父王普里阿摩斯关闭战争之门,“上紧栓,挂好锁,连一只苍蝇也不让飞过。”战争之门要关闭,战争不要发生,无疑这一切要取决于海伦,赫克托尔也对海伦说:“今晚你必须回希腊,不然我就杀了你。”而面对帕里斯,赫克托尔也逼问他,帕里斯说自己爱的是“海伦不爱我的方式”,就像海伦所说对帕里斯只有崇拜。但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赫克托尔一直没有阐明什么是爱,也不知道海伦对于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意义。按照得摩科斯的说法,海伦是“美的化身”,剧中的几何学家更是阐述了和谐之美,这是古希腊对美的一种定义,“没有米,没有克,没有海里。只有海伦的步子、海伦的肘长、海伦的目光和声音所及的距离,而她走过的气流就是测量风的尺度。”海伦成为美的刻度,这是超越一个具体的人的美。而在赫克托尔看来,海伦只是一个女人,“你们偷换概念,假称要我们为美而战,实则为一个女人而战。”
海伦到底意味着什么?海伦也终于出场,海伦说她听帕里斯的话,说自己不会回希腊,对于爱,她不知道别人的感觉也不想知道自己的感觉,对于赫克托尔的逼问,海伦也拒绝做出选择,而且她说:“我看不见和平。”出场的和平女神让自己浓妆艳抹,但是在海伦面前还是不够美。实际上,出场的海伦在美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化身,但是她又用不同的否定句让自己成为命运的代言人,只有在特洛伊罗斯面前,海伦才可爱地以肯定的方式想要一个拥抱,“他想拥抱我。”海伦的确是一个女人,但是是一个美的女人,一个有着否定命运的女人,所以在卡珊德拉的预言和安德洛玛克的预言之间,海伦所带来的战争不是特洛伊战争,而是人和神的战争,战争的傲慢也是神的傲慢,“要歌颂,要时刻奉承,要不停恭维战争庞大躯体上或清晰或含糊的部位。否则就会惹恼战争。”得摩科斯所说的战争不正是体现了神的特点?
当希腊军团上岸,战争一触即发,作为诸神的信使伊里斯出现在空中,他表达了诸神对战争的看法:在阿芙洛狄忒看来,爱情是世界的法则,它是神圣的,所以神要保护情人,禁止拆散海伦和帕里斯,“否则战争就会爆发。”在帕拉斯看来,理性才是世界的法则,天下有情人都在胡言乱语,所以他命令要拆散海伦和帕里斯,“否则战争就会爆发。”而在诸神之王宙斯看来,“在世间万物中只看见爱情的人和看不见爱情的人同等愚蠢。”所以他委托赫克托尔和奥德修斯,双方的将领,要拆散海伦和帕里斯,同时又不要拆散他们——诸神的说法和命名一样矛盾百出,但是他们代表的是权威,是神圣,那么战争到底会爆发还是不会爆发?季洛杜让战争不会爆发体现在剧名上,却又让战争爆发出现在最后,作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前史,“特洛亚诗人死了……轮到希腊诗人开始吟唱。”战争爆发了,战争之门终于缓缓开启,但是海伦却在门后亲吻了特洛伊罗斯——一种和女人、和人性、和爱有关的故事发生在战争和诸神背后,是不是一种渎神?
命运对否定句感兴趣,但是海伦却以肯定句的方式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种命运,同样,在《安菲特律翁三十八世》中,身为女人的阿尔克墨涅也在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命运,而且她不是在诸神的背后而是在诸神面前。在这出戏剧中,季洛杜让人和神之间的矛盾在一开场就出现,朱庇特带着墨丘利来到人间,观察阿尔克墨涅,按照墨丘利的说法,“朱庇特,您爱上一个凡间女子,竟至放弃属神的特权,为了看一眼阿尔克墨涅的影子,在仙人掌和荆棘丛中待一整夜,这真让我佩服!”放弃神的权力而爱上人间女子,这是神的屈尊,而里面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朱庇特为什么要如此屈尊,因为他对人间的爱感兴趣,因为他要了解爱的仪式,即使知道阿尔克墨涅只爱她的丈夫安菲特律翁,朱庇特认为,一方面,“一个妻子凭着爱能把丈夫当成自身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阿尔克墨涅不是安菲特律翁的那部分则要完成一次受孕,生下半神的儿子——那么,受孕是属神还是属人?按照墨丘利的说法,属神的方案是带她到我们的高度,“让她攀升躺在云上,过会儿再恢复她那背负得起一个英雄的重量。”属人的方案则是简单直接:“进门上床,再跳窗离开。”
无疑,朱庇特选择了属人的方案,但是要让阿尔克墨涅爱上自己并受孕,一方面朱庇特在放弃神的特权后,还必须拥有人的特征,或者说成为一个人,在进入阿尔克墨涅的房间之前,墨丘利就将他调整为完全人的模样,而那一夜之欢后朱庇特的脸上多了一道皱纹,朱庇特称之为人的皱纹,这是他从神到人的标志。而另一方面,朱庇特必须要让阿尔克墨涅的丈夫安菲特律翁离开,所以他利用神的权力让“化身”索希亚点燃战火,安菲特律翁便率兵出征。在这里朱庇特制造了两样东西,一样是成为人的爱,一样则是战争。战争是什么?季洛杜让“战士”阐述了战争,战争是平等,是自由,是博爱,因为穷人被不公平地对待,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打倒敌人报仇雪恨,富人通过战争可以让国家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欢乐,渎神者可以在战争中为所欲为,懒惰者奔赴战壕可以战胜懒惰……“把分散人员团结起来,用战争取代决斗,这是祖国的伟大成就所在。啊!让和平自惭形秽吧!和平只会接受老人、病人和残疾人的死亡,战争把死亡带给代表最强壮水平的人类……”
无疑,在这里季洛杜讽刺了战争的美好,实际上也讽刺了神的特权。但是在朱庇特和阿尔克墨涅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神权受到了一个女人的挑战和质疑。当安菲特律翁征战,朱庇特化身为安菲特律翁,阿尔克墨涅即使不能认出眼前的丈夫是朱庇特假扮的,她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除了我丈夫,没有哪个男人能走进我的房间。就算他本人掩饰身份前来,我也不欢迎他。”这是一种爱的忠贞;“因为情人离爱情永远比离被爱的女人近。因为我只能忍受没有边际的欢乐,没有保留的乐趣,没有限度的从容。”这是对背叛的痛斥;“这美短暂即逝。朱庇特太严肃,不可能愿意创造短暂即逝的东西。”这是对神力的否定;“我不会特别对朱庇特心怀感恩,因为他创造出四大元素而不是我们原本可能需要的二十种元素,那是他在永生中的职责,反过来,我心中会洋溢对我亲爱的丈夫安菲特律翁的谢意,因为你在战斗的间歇发明了一套窗户滑轮装置和一种新葡萄嫁接法。”这更是在神和丈夫的对比中对人的尊敬。
而已经放下了神权的朱庇特发现了人类之美,他对阿尔克墨涅说:“因为你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真正合乎人性的人类……”朱庇特甚至对墨丘利说自己体验到了真正的爱情。而当朱庇特终于现出真身,面对眼前的神,阿尔克墨涅更是毫不惧怕,一方面她说自己爱诸神,被朱庇特这样的神爱着是“无比幸福”的事,但这是对神的一种爱,而不是属人的爱;另一方面,她要求“从我身上移走朱庇特的恩宠吧”,甚至她知道这就是渎神,“我不敬神。我常在爱情中渎神。”面对墨丘利的威胁,阿尔克墨涅和安菲特律翁丝毫不害怕,而阿尔克墨涅直接指出了神和人之间的差异:“他会把我们变成不一样的生物。又一对以爱情著称的夫妻彼此分离,原因不是仇恨,而是种族差异:夜莺与癞蛤蟆、柳树与鱼……”神和人之间的差异是种族的差异,而爱属于同一个种族,属于“在场的种族”。
人类对神表现出抗争,阿尔克墨涅和安菲特律翁甚至想好了以死抗争,这是神人之间的战争,但是当战争即将爆发时,季洛杜却安排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结局,它不是通向悲剧,而是神人的对话,这就是针对种族差异而出现的平等,这个平等就是友情,“它给最不相像的造物配对,使之互相平等。”阿尔克墨涅对朱庇特说,而朱庇特也第一次理解了这种平等,“一个部长每天去看望一个园丁,笼中的狮子寻找卷毛狗,水手与教授,豹猫与野猪。他们看上去完全相互平等,共同面对日常烦恼,面对死亡。”除了平等,还有发自内心的信仰,还有不再是仪式的“示意”,当然还有朱庇特和阿尔克墨涅生下的赫拉克勒斯,神人结合的赫拉克勒斯,“他会是温柔听话的小男孩。”
从《厄勒克拉特》纯粹和顽强导致的悲剧,到《特罗亚战争不会爆发》对美和爱的争取,再到《安菲特律翁三十八世》平等之友情的诞生,季洛杜在“重述”中创作了新的文本,围绕着人和神的不同战争,阐述了女人代表的人性和爱,从命运的否定句到最后的肯定句,悲剧的黑夜也终于被翻了过去,“还有高处的帷幕,你们在暗夜中忍耐了一小时,用天鹅绒禁闭这片名曰忠诚的林中空地吧!幕落吧!”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8094]
顾后:《移民》:自由是应许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