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27《电影与伦理》:一个动物怎么能够正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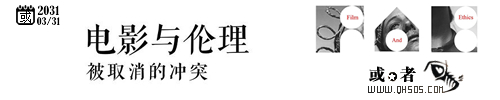
面对被描绘的生物,在判断它们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的地位时,知识、猜测和文化共鸣对我们的反应带来了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是后伦理的会怎样?后现代主义的伦理与美学》
一只保存在酒精中的蝾螈,正露出神秘而怪异的微笑,它已经死去并作为标本而存在,但是它的微笑分明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使自己成为胜利者?观看,或者说是凝视,而且不只是“看见”本身,是在“看见”中把被凝视的对象当成是客体,那么,一只被保存在酒精中的蝾螈,凝视人类时,它作为凝视者这一主体,是不是意味着人类成为了客体?或者更残忍地说法,它已经变成了具有人类主体的存在,而被凝视的人类是不是就成了非人类?
这是卡尔·格里姆保存着的一只会凝视的蝾螈,而诺琳·吉弗内和迈拉·赫德编著的文集《古怪的非人类》就是用美西蝾螈作为封面图——当我们看见文集,是把美西蝾螈当做了“非人类”的存在,是在凝视“非人类”,这是不是和卡尔·格里姆面带微笑的蝾螈构成了一种对立,这似乎引出了德里达的一个问题:“一个动物怎么能够正视你?”你作为人类凝视作为非人类的美西蝾螈,酒精中的蝾螈一样可以凝视作为人类的我们,“一个动物怎么能够正视你?”并不是一个德里达的疑问,而是成为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背后的关系涉及的是德里达所暗示的伦理相对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电影《异形》系列中得以影像化展开:《异形》四部曲呈现的伦理冲突就是人类与异形之间的冲突,即人类包括其中与人类相像的“人造人”和完全不同于人类的另类生物之间的冲突,如果按照传统的伦理学理解,人类中心论是基于一种保护人类自身理想的伦理学,那么异形就是他者的存在,伦理冲突的结果“必然是杀他性的”,但是正如酒精中的蝾螈一样保持着神秘而怪异的微笑“正视你”,它也在一中“忠诚于同类”的伦理学中,把人类视为一种他者,凝视也必然是“杀他性”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传统的伦理学受到了挑战,甚至,“它们围绕着物种忠诚的概念运转,并且对人类本位说表示怀疑。”
人类与非人类,人类与异形,表征着伦理学的冲突,同样,非人类对人类,异形对人类,也在解构着人类本体,也在质疑物种的忠诚——一种凝视,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关系,它的伦理学指向必然导致的是一种冲突,而《异形》系列电影作为丽莎·唐宁和莉比·萨克斯顿观念中的“后现代电影”的代表,它所具有的意义便是将先前隐藏的针线暴露出来,“以前,正是这些针线,将类型化的、性别化的叙事缝合起来,并且支撑起这些叙事的逻辑必然性的自然主义观念。”自我和他者的冲突,杀他性的伦理学已经越过了人类本位的自然主义观念,以一种对主体甚至本体的颠覆、解构为目的,以多元化的观念形成了具有当代性的伦理语境。丽莎·唐宁和莉比·萨克斯顿将这种变化称之为“伦理学的转向”,它在“二战后”出现,而具体的哲学思想则体现在列维纳斯的批评标准、雅克·德里达的责任理论、拉康的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思想、后殖民研究和酷儿理论等,那么,在“伦理学转向”中,伦理学的自我和他者的冲突又如何在电影中被呈现?
本书的副标题:被取消的冲突,“电影和伦理”这一组合关系中伦理学的表现为什么是一种“被取消的冲突”?一方面,丽莎·唐宁和莉比·萨克斯顿认为,在一个图像日益饱和的社会中,非书写文字的视觉语言是伦理探索的核心所在,用伦理学来关照电影的状况,就是揭示图像世界中受挫折、被轻视、被压抑的伦理学冲突,电影充分表现了同一性、差异性以及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而且电影实践中的观看行为也成为了伦理学冲突的关照所在,它所凸显的就是“伦理的凝视理论”:观众观看,通过影像观看,既是电影内部表现主题有关的观看行为,同时电影之外的观看也是在观众和影像之间建立的凝视;但是另一方面,伦理学具有的对义务的道德实践问题,在电影世界中也意味着某种新的质问:在既定的情境中我应该做什么?我的责任范围是什么?在道德方面我的行为对集体有何影响?它并非表现为一种完全实证性的道德训练,而是和自然主义的凝视区别开来,甚至是像蝾螈一样在对人类本位的怀疑中让“人类”成为一种凝视的客体,“思考伦理学可以做什么和伦理学的定位在哪里,而不要纠缠伦理学是什么。”
将伦理学的现代质问引入到电影中,或者从电影中发掘伦理学的转向,丽莎·唐宁和莉比·萨克斯顿的目的很明显,“我们不是要设计一个价值体系,将电影分成伦理的和非伦理的,而是把伦理作为电影活动的语境,因为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接受总会涉及欲望和责任(对艺术家和观众都不例外)。”电影世界呈现了伦理所涉及的欲望和责任主题,而这本身也是伦理学冲突的关键所在,所以电影只是一个表现伦理冲突更充分也更具有凝视意义的样本,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涉及欲望和责任的关系,我们就置身于伦理的场域。”那么,电影中的伦理表现如何涉及欲望和责任?在冲突被取消和被表现中,凝视的忠诚性和杀他性有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从电影本身的“表现”来看,首先涉及的往往是美学范畴,而美学本身也具有道德性,是一种伦理学,考察对于美的阐述,康德认为美的客体看起来美好和谐是通过主观的自由想象构成的,也就是说美不是客体本身固有的属性,这是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但是在席勒看来,仅仅靠抽象的形式经验并不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善”,所以美作为道德的象征,改善的内容就和同意的形式一样重要;黑格尔认同席勒的观点,他认为美学的核心在于理念和形态之间的协调一致。而对于电影呈现的美和道德,戈达尔却有一个经典的观点:“跟拍镜头是个道德问题。”戈达尔所说的跟拍镜头的功能,就是电影形式和场面调度的提喻,他认为没可以成为道德性的象征,但必须在伦理的内容被塑造成合适、合理的形式之时,所以针对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他认为对大屠杀进行美化是不道德的。这是一种“价值图像学”的范畴,和戈达尔一样,尼科尔也认为,电影风格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它是一种“意义的载体”,密切依附于“道德视角”,尤其是纪录片,和虚构的剧情电影导演可以退出伦理立场不同,纪录片制作者所肩负的是义不容辞的特殊责任。
| 编号:Y22·2240108·2050 |
从纪录片的视角阐述美学和伦理学的同一性,阐述“跟拍镜头是个道德问题”,以费利贝尔导演的《是和有》为例,在最后的镜头里,齐头高的大麦在随风摇摆,画外音是:阿丽兹已找到了,但是摄影机依然对准不停涌动的麦田,既看不到孩子已经回来了,也不解释她走丢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正是在阿丽兹走失的影像后面出现了麦浪的画面,它在模糊性表现中让观众可以创造性地去理解,“通过拒绝启蒙说教、摈弃虚假的剧情、充分利用银幕外的声音空间,影片为自主的观影活动留有余地,让想像来助力思辨的价值评判。”麦浪传递的是一种美,但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美,而是具有明显的道德性,它是一种在凝视中完成的伦理学构筑,正如费利贝尔所阐述的:“我不拍“相关”的电影(about),只拍“相与”的电影(with)。”对于介词的选择表明了伦理学思想,在“相与”中,“我只是努力在观众和影片中的人物之间创造某种冲突。”
纪录片体现着导演“相与”的意图,这对于构建伦理学的凝视效果是明显的,但是在剧情电影中,电影和伦理的关系则趋于复杂,不过它也呈现了伦理学的多元性,这其中就必须解读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本书对女性主义的“肯定”的表现提出了质疑,这个从1970年代出现的女性主义批评学说概念,在对于女性的身份认同和政治驱动的性别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是作者认为在伦理意义上“它始终具有主观的,具有文化的特殊性”,在面对各种电影生产文化的意识形态上,它更多是“冒险地接受”而不是“批判地审视”,在这个意义上,“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以电影《末路狂花》为例,电影表现塞尔玛而露易丝的表现基本上是肯定的,它塑造了“自由的”女性角色,但是当电影最后她们以飞驰的方式冲入深渊,却只是表现了一种“言不由衷的乌托邦”,看起来是冲破了男性权力而完成最终极意义的自由,但是坠入深渊不是逃离而是一种惩罚,“它设计了一个看似批判的谎言,使悬而未决的伦理问题让步于虚无缥缈的胜利的奇观。”
另一种视角是关于殖民主义的,它和女性主义一样,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表现了伦理学的冲突,最后以一种杀他性的方式构建了自由,但是在电影《不朽的园丁》中,尽管导演是巴西人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摄影是乌拉圭摄影师塞萨尔·查尔洛内,场景选择在被殖民过的土地上,故事也是关于种族主题的,甚至明确批评西方的神话学,但是它的内在逻辑上依然是西方中心说,它把我们引诱进了“只有白人可以拯救非洲”的殖民主义圈套中,欧洲依然牢牢掌控着道德话语权,“影片对于西方电影主流视角和类型传统的坚持,泄露了它貌似真诚的伦理承诺:伸张正义和恢复公平,仅仅是为了白人的良心得到宽慰。”但是和基于白人视角的《不朽的园丁》不同,另一部电影《芭玛戈》则以非洲人自己肩负起调查责任为叙事线索,它发起了与西方电影及其殖民主义遗产的对话,质疑西方的“善良”和“正义”改变,挑战了它们与“美”的关系,“这样的电影不仅关心全球化的伦理,同时也涉及伦理的全球化”,真正提出了“伦理是什么”或“伦理应该怎么样”的理解。
女性主义构筑的伦理话语,殖民主义下的伦理视野,在不同的电影中成为一种“表现”,它的伦理学所凸显的冲突实际上从所谓的美学变成了伦理-政治学,电影中的主题便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伦理的凝视”。但是这些电影的伦理冲突仅仅是在“电影内部”表现的,而另一种凝视则来自观影行为。本书举例的三部电影分别是伯格曼的《假面》、安东尼奥尼的《过客》和迈克尔·哈内克的《影藏摄像机》,它们具有的观影都来自于“外部”,即以一种具有哲学意味观看行为构建起自我和他者的道德联系。《假面》中看见的是越南冲突中的自焚者、被纳粹士兵逮捕的华沙妇女和儿童,《过客》中通过荧幕内外的见证将纪录片和现实连接起来,《影藏摄像机》则通过电视播送的图像将后殖民暴力和现实生活重置,所以电影中的观看不再是旁观者的观看,而是在观看中激发伦理思想和行动,在“道德的困境”中赋予观看者一种责任,“这些影片坚持认为,我们看什么,以及我们怎么看,都是有影响的。”看的特权与他人的痛苦密切相关,从而引起主动地质询和反思。
从女性主义的“肯定”到殖民主义的道德,从电影内部的凝视到内部和外部并置的受难凝视,这些都是对电影之“表现”的伦理解读,而从第二部分开始,本书从实践转向理论,或者转向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伦理语境,通过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和后现代的哲学模式解析作为凝视理论之基础的客体化原理,试图发现伦理精神在电影经验中发挥的作用。这一部分虽然是和哲学阐述有关,但是本书侧重于各种观点的介绍,虽然和电影文本形成了一种连接,但偏重于知识的介绍,很多都是泛泛而谈,但是对具体电影的分析还是能看出另一种逻辑指向。比如在列维纳斯的伦理观点介绍中,本书分析了列维纳斯所说的“面貌”,即作为一种“不顺从图像”,他者的脸在逃避中并不能在图像中相遇,而朗茨曼的《浩劫》却用集中营见证人的脸,尤其是在镜头中那些脸的特写变成了奇观,它使得历史在场,这不是对列维纳斯“面貌”禁令的一种违背?
“由于缺乏关于过去的直接影像,这些幸存者的脸变成了呈现创伤的场所,进一步确认了对直接表现的禁令。”朗茨曼的脸超越了图像,它不再是简约为可视现象、知识源泉和审美思考对象,它敞开为一种可能性,而在敞开中“面貌”就变成了一种语言,一种历史的语言,伦理的语言,而这正符合列维纳斯所说的伦理关系中的表达:说话,“脸在说话。脸的表现已经在交谈”,不仅交谈还在质询和召唤,让他者处于“自己的异质性”中,从而唤起创伤性历史的他者,也就是按照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他者的他性作为自我的一部分而纳入到整体之中,它构成了这样的伦理学:“唤醒了主体对他者的责任”。同样,在德里达解构的伦理学和德莱叶的《圣女贞德受难记》和《词语》的解读中,构建起关于自由的共识的伦理学原则,“其价值在于它可能改变我们,让我们去关注电影实践与理论中过于踌躇满志的总体性话语所蕴含的象征性暴力。”聚焦于福柯的监视理论,从《易尔先生》这部电影中阐释了“关心性别化的凝视以及凝视者的霸权”,从拉康的欲望学说和死亡驱力阐释希区柯克电影中的病症性形象,从心理分析角度开辟了伦理学的另一种视野,“心理分析的理论和电影的伦理前景可能最好被理解为新型的模式——抵制和重新想像简单的时间观念以及相应的过于简单的主体性和相关性。”
种种伦理学的哲学理论和电影经验的分析,无疑是在审视不同的观看行为中质问这样的问题:观看行为是不是不直接将观看对象客观化?伦理学是不是可以打破凝视过程中的主体-客体关系?问题其实又回到了伦理学的现代意义上:一方面意味着一种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予以回应方式,另一方面悬置了主体-客体关系的含义及其内在的主从功态。而这恰恰是我们正处于后现代主义的“后伦理”问题,依然是从电影入手,本书解析了后现代主义电影的代表塔伦蒂诺的电影风格,以《杀死比尔》为例,塔伦蒂诺有意识地模仿表现的传统,“篡改”观众的快感和共谋,通过拼贴、杂烩,以“忠于自己”的方式将传统的“元叙事”对立起来,从而取消意义的“真理”,它甚至取消了道德原则,而是构建一种档案馆或者参考数据库——倒空了内容的艺术,就是在超越伦理学的类型传统、主题、修辞中带来快乐。
在后现代主义电影中,不仅仅是解构宏大主题,颠覆类型叙事,而是取消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真正悬置了主体-客体的二元论,这在《异形》四部曲中便完全建立了对人类本位的怀疑,人类不是凝视异形的主体,异形也不是人类凝视的“怪物”客体,而是像酒精里的蝾螈一样,被描述他者却以自我的方式将描述者变成了他者,“一个动物怎么能够正视你?”德里达这个关于伦理相对性的问题也彻底变成了:你被一个动物正视,因为你也是一个被正视的动物。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712]
思前:【欧也·2024】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