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24《十四行集》: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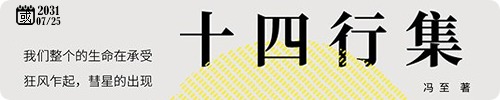
是一个旧日的梦想,
眼前的人世太纷杂,
想依附着鹏鸟飞翔
去和宁静的星辰谈话。
——《一个旧日的梦想》
《十四行集》中的第八首,是冯至在行走中萌生写作十四行诗的一个契机,也正从这这个起点开始,1941年的他接连写下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当时的冯至是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教书和翻译是他最主要的两件事,那时的他每周要从昆明附近的山里进城两次,来回有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当一个人在山径上,在田埂中,当一个人看见一些东西,思考一些东西,于是有些称为诗意的存在就慢慢涌进了脑子里。
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于那个冬天的下午,冯至抬头看见了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于是就想到了古人的鹏鸟梦,这个鹏鸟之梦便带着冯至进入了诗歌的世界。他说,在1941年之前的十年里,他写作的诗歌不过十来首:从留学德国接触德国文学,到回到中国随西南联大西迁,对于冯至来说,写作的时间的确不多,而在昆明的这段日子,忽然就从这银色的飞机和蓝色如结晶体的天空中发现了鹏鸟之梦,也看见了自己的诗歌梦,于是回来之后写在纸上,成为了《十四行集》中的第一首。诗人看见了古时的鹏鸟梦,飞翔当然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去和宁静的星辰谈话”,这种自由也是冯至在现实困境之中展开的想象,它无拘无束,它自由自在,但是古时的梦想只是梦想,和星辰说话需要后人来实现,“他们常常为了学习/怎样运行,怎样降落,/好把星秩序排在人间,//便光一般投身空际。”
梦想虽然美好,自由令人向往,但是后人的学习,后人的实现,却是另一个梦的开始,那就是“忘不了人世的纷纭”,这人世的纷纭有时候是与星辰对话的动力,有时候却又是一种束缚,所以旧梦可能醒来,那只不过是“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旧梦坠落而下,也是对于人世纷纭的一种无奈。从获得灵感提笔写下的第一首,到《十四行集》中的第八首,这首冯至称为“最早也是最生涩”的诗歌,也是从旧梦到现实的一次排序,而从天空中的飞翔到陨石的坠落,从鹏鸟的自由到人世的纷纭,似乎也在主题表达上契合着十四行诗的一个写作特点。在1948年的《序》中,冯至说到了自己采用十四行这种诗体来写作的缘由,不是为了要把西方诗歌的这种体例移植到中国来,“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按照李广田的论述,十四行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层层上升而又下降”,就是“渐渐集中而又解开”,在形式的错综而又整齐中,在韵法的穿来而又插曲中制造变化,而这不正是这首诗的行文和抒情特点?旧日的梦想就是在鹏鸟的飞翔中和星辰对话,这是一种脱离束缚层层上升的状态,是渐渐集中的过程,但是当旧梦变成现实,最后是远水荒山的陨石,这就形成了下降和解开的状态,也就是在旧梦上升而下降成陨石,抒情集中又解开的过程中,冯至穿越古今和天地,重新回到站立的这片天地,这个时代。
“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从这首旧梦开始,冯至开始了《十四行集》的创作,很明显,冯至在这首诗中的情绪一方面表现为坠落为陨石后面对现实遭遇而抒发的情感,这里有在《威尼斯》中出现的“寂寞”,“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西方的那座水城在冯至看来就是寂寞的象征,它被水而隔开,即使有桥的连接,即使有开窗的人,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楼上的窗儿关闭,/桥上也断了人迹。”这里有《原野的哭声》里传达的“绝望”,村童和农妇为什么向着无语的晴空啼哭,“是为了一个惩罚,可是//为了一个玩具的毁弃?/是为了丈夫的死亡,/可是为了儿子的病创?”没有停息的哭泣把整个生命都嵌在了绝望中,而在啼哭之外已经没有了人生和世界,宇宙也成为了“一个绝望的宇宙”;这里有《我们来到郊外》感受到的“危险”,这是敌机空袭警报拉向之后,市民们躲到郊外的情景,“要爱惜这个警醒,/要爱惜这个运命”的背后,其实依然是摆脱不了的危险,这种危险意味着:“那些分歧的街衢/又把我们吸回,/海水分成河水。”这里更有《给一个战士》所提到的牺牲,在战场中他们是不朽的英雄,但是,在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苍穹中,或许他们也是“一支断线的纸鸢”,即使如此,在冯至看来,这种纸鸢的存在是对现实的超越,因为,“他们已不能/维系住你的向上,你的旷远。”
寂寞、绝望、危险和牺牲,这些构筑了冯至《十四行集》中一种哀怨的情绪,而这种哀怨的背后则是目睹了苍生的苦难,因为面对着现实的困境,但是正如牺牲的战士那样,他的死亡也是奔向另一种自由的开始,也是向上和旷远的存在。所以在《十四行集》中,冯至更是看见了那种上升的力量,它指向的是生命的意义。诗集中的第一首《我们准备着》就是通过小昆虫表达一种生命意识:当昆虫们经过交媾、抵御危险,意味着一生的结束,虽然短暂但是美妙,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冯至借物抒情都是在回答生命的意义问题,他在《有加利树》中看见了调零之后生长的动力,“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他在《鼠曲草》中想到了渺小生命的伟大:“不辜负高贵和洁白,/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不管是喧闹还是静默,不管是绽放还是凋落,鼠曲草总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完成人生的定义,“这是你伟大的骄傲/却在你的否定里完成。/我向你祈祷,为了人生。”他在《几只初生的小狗》中听到了吠叫,刚出生的小狗,母亲将阳光和温暖带给他们,而到了黑夜,母亲将它们又带回去,似乎白天已远,光和暖也被遗忘,但是这这不过是生命中的考验,因为对于将来的它们来说,吠叫才是它们应有的态度,“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这是小狗的使命,更是冯至对经历苦难的所有人的宣言。
冯至留学德国,接触了德国文学,他更是在阅读、翻译里尔克的诗歌中汲取了营养,他翻译的《豹》也成为里尔克诗歌汉化的最好版本。当然里尔克的“物诗”对冯至产生了影响,或者可以说《有加利树》《鼠曲草》《几只初生的小狗》这些借物抒情的诗歌体现的也是“物诗”的风格,但是在《十四行集》中,冯至更多是将诗人的主观感受直接抒发出来,而诗歌的主题也并不晦涩地得到了表达,那就是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新生的责任以及时代的使命等宏大主题。“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在一切都指向新生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是首先要解决的,只有脱落了才能迎来新的绽放:像秋日的树木那样,树叶和花朵交给秋风,然后将树身“伸入严冬”,这是一种死亡,如蜕化的蝉蛾那样吧残壳丢在泥土里,而死亡不是终结,它是另一首歌的歌唱,“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这是冯至抒情的一种心路历程,在死亡之后才是新生,在静默之后才是爆发,不经历这一切就难以获得生命的荣光,所以在和亲密的夜告别之后,从窗外的原野出发,认出“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那些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和年轻的男女、死去的朋友,都给我们踏出了道路,而我们就应该沿着他们的足迹,“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原野的小路》)”在原野中,在道路上,一定会有狂风暴雨,“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其实就是“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前行……在踏上他人开辟的路上,当和亲密的夜告别,当听着狂风暴雨前行,生命在历练中向着明天的方向出发,而旧梦也重新发芽,“看那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新生。(《这里几千年前》)”于是第八首的那个旧梦,在生命秩序的重新编排中,变成了另一声呐喊:“用迫切的声音:/“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深夜又是深山》)”
| 编号:S28·2240516·2117 |
从旧梦里看见生命的荣光,看见未来的方向,看见“一个大的宇宙”,冯至也从另外一方面重构了这个世界,那就是对人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十四行集》中有一部分诗歌是纪念那些立在他面前的伟大人物,他们是诗人杜甫,“你的贫穷在闪烁发光/像一件圣者的烂衣裳,/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他们是洞察了“死和变”的歌德,“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蛇为什么蜕去旧皮才能生长”,是用画笔创造另一个世界的梵高,“这中间你画了吊桥,/画了轻盈的船:你可要/把些不幸者迎接过来?”当然,他们更是同时代的蔡元培,“多少青年人/赖你宁静的启示才得到/正当的死生。”在蔡元培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冯至正是通过“你死了”来寄托重塑的希望,“
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复活,/歪扭的事能够重新调整。”还有对鲁迅的怀念,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而冯至则“永远怀着感谢的神情”,这种深情不是纯粹个人的情感,而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你走完了你艰苦的行程,/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曾经引出你希望的微笑。”被愚蠢的时代摒弃,却永远有一株挺立的小草在朝着伟大的灵魂微笑——冯至何尝不是那株读懂了鲁迅的小草?
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只不过是冯至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发出的声音,引出的思考,对苦难的感同身受,对生命的高歌礼赞,以及对时代的方向的思考,在这些十四行诗中得到体现,当然,这些诗歌无论是题材还是写作风格,都有同一化趋向,即使在层层上升中下降,在渐渐集中中解开,其实也并无让人惊艳的那种错落感,但是当1948年诗集再版时,已经回到北平的冯至回首这些诗作,有了另外的认识,“如今距离我起始写十四行时已经整整七年,北平的天空和昆明的是同样蓝得像结晶体一般,天空里仍然时常看见银色的飞机飞过,但对着这景象再也不能想到古人的鹏鸟梦,而想到的却是银色飞机在地上造成的苦难。”一样有银色的飞机,一样是“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但这里已经不是昆明,鹏鸟梦也早已破灭,仿佛一下子变成了落入远水荒山的陨石,看不见未来,世界只留下了战争造成的苦难。
而实际上,这种将时间轴线延长、以回首的方式来看待写作所走过的路,更能发现“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的错落感,《十四行集》中收录了冯至不同时代的一些杂诗,最早的是写于1926年——比《十四行集》早了15年,在这些诗歌里,冯至更多了一些迷惘,“我也能演奏,/演奏这夜半的音乐——/拉琴的是窗外的寒风,/独唱的是心头的微跳,/没有一个听众,/除了我自己的魂灵”,虽然在死沉沉没有爱情、没有生命的1926年,冯至也想让自己看到欢腾腾的爱情和生命,但终归是“我只能”的哀愁。同年的《湖滨》更是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是“日日夜夜高筑我的狱墙”,束缚自己终究无法逃出,而即使生命之火燃烧,最后的结局也无非是一种自灭的“烧焚”,《迟迟》则是将一切的希望吞灭,“泪从我的眼内苦苦地流;/夜已经赶过了,赶过我的眉头。/它把我面前的一切都淹没了”。
孤独和迷失,是这一时期冯至抒情的主要内容,1928年的《北游》似乎是情绪的一个转折,这首长诗分成十三个章节,题辞引用的是荷兰作家望蔼覃《小约翰》里的一句话,“他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北游”是当时冯至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人生的游历,但更是心情的游离和游荡,“我是一个远方的行客,/走入一座北方都市的中心。”听不到鸟声,看不见树林,天空中是浓雾,街上是噪音,“人人裹在黑色的外套里,/看他们的面色吧,阴沉,阴沉……”这是《前言》,交代了行客的我所面对的世界,那就是“阴沉”,之后几乎都是对“阴沉”的重复,在《别》中感受到的是火车上寂寞的面孔带来的“阴沉”,《车中》则是从满车的客人望向窗外看见的“阴沉”,《哈尔滨》是整个过天空的“阴沉”,《雨》更是在泪眼中加深了“阴沉”,《公园》里是对生命旅途走向“阴沉”的喟叹,《中秋》是孤独者的“阴沉”,《礼拜堂》是找不到归宿的“阴沉”……如此“阴沉”的北游生活,哪里是一个出口?但是冯至的抒情在最后的“尾声”中突然闪现出一种力量,“我不能这样长久地睡死,/这里不能长久埋葬着我的青春,/我要打开这阴暗的坟墓,/我不能长此忍受着这里的阴沉。”
这种力量的爆发的确显得突然,但似乎也是冯至情感的一个必然转折点,在之后的诗作中,这种向上的力量渐渐集聚起来,1928年的《听——》中冯至说:“那么,风雨雷霆你便不难听见,/听出来一片新鲜的宇宙的呼声。”1929年的《月下欢歌》更是喊出了“我的感谢”:感谢无边的月色、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祖国的语言、温带的气候,在层层递进中,最后冯至在灵魂的跳动中,在脚步的奔跑中喊出了:“宇宙的一切,/请你们接受吧,/我的感谢!”1933年的《无眠的夜半》表达了一往无前的决心,“我不自主地跟随他走上征途,/永离了这无限的深夜,/像秋蝉把它的皮壳脱开。”1943年的《我们的时代》,更是冯至对时代使命的一种阐述,“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当然,在这段经历中他也感受到了死亡,1937年的《给秋心》四首,是献给作家梁遇春的,对于“几个死去的朋友”,冯至感受到了特殊的静默,“你的死竟是这般静默/静默得像我远方的故乡。”朋友的死呈现的静默,是一种个人情感的抒发,而在1945冯至写下的《招魂》,则是对“一二·一”遇难同胞的缅怀,“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这一种死才是激励我们向生的力量,于是在静默之后,在消失之后,冯至的“招魂”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唱响了诗人的生命之歌:
“正义,快快地到来!
自由,快快地到来!
光明,快快地到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