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24《马可波罗行纪》:广历世界之所见所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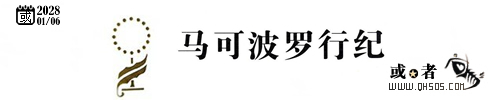
马可奉使归来,谒见大汗,详细报告其奉使之事。言其如何处理一切,复次详述其奉使中之见闻。大汗及其左右闻之咸惊异不已,皆说此青年人将必为博识大才之人。
——《第一卷》
大汉忽必烈之惊异,其实已经是马可归来第二阶段了,他和父亲尼古剌、叔叔玛窦从物搦齐亚回到大汉驻城上都可以视为第一阶段,在第一阶段时,大汗之所以对马可感兴趣,就在于他对所见所闻详述,满足了大汗的某种欲求,于是留下他让马可执行使命,马可奉使出使各地,在17年间带回来关于各地的风俗民情,再一次使得大汗惊叹,于是马可被称为博识大才之人,并被称为“马可波罗阁下”,由此马可波罗达到了人生之顶峰,“待遇优渥,置之左右”,甚至招致侍臣的嫉妒。
一个嗜好听闻各地风情,另一个则将所见所闻变成听闻的故事,在君与臣之间建立了“行纪”书写的必然性意义,这似乎就变成了一种“投其所好”的行为,而这种完全建立在君主喜好基础上的文本,是不是客观性会受到损害?这或者也是《马可波罗行纪》被质疑的原因之一,而“马可波罗”是否确有其人,其经历是否具有真实性,也成为了历史学的最大争议。对于此种疑问,卷首中的一段叙述似乎是一种回答:“欲知世界各地之真相,可取此书读之”,从大阿美尼亚到波斯,到鞑靼,到印度,到世界各地,书中所叙“秩次井然,明了易解”,这一切都是马可波罗亲眼目睹,即使不是亲眼目睹,也是“闻之于确实可信之人”,“所以吾人之所征引,所见者著明所见,所闻者著明所闻,庶使本书确实,毫无虚伪。”
所见和所闻,构成了《马可波罗行纪》的第一首资料,而所见所闻的重要标志便是在场性,所见者即所见之物,所闻者即所闻之事,所以书中一切为“确实”之人和事,如此构建“毫无虚伪”的文本,甚至特意强调这是世界各地的真相,是不是反倒有了某种画蛇添足之嫌?实际上,不管是所见所闻,还是“秩次井然,明了易解”的风格,在整本《马可波罗行纪》中并非客观,大约正是抱着“投其所好”的目的,途中所记录之种种还是有其主观性的意图,而地名之不同意,线路之错乱,也成为后世研究的一大难点,这也使得这一文本本身具有了歧义性——不妨从文中所记的过程和线路来还原马可波罗行纪,并检索其可能的错舛。
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录的过程,如果按照和当时大汗的存在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马可波罗还没有出现,他的父亲尼古剌和叔叔玛窦从意大利的物搦尼亚,即威尼斯出发开展商货活动,他们从物搦齐亚出发,经过黑海达到孔士但丁堡,然后离开孔士但丁堡,经过速达克、波斯的不花刺城,最后来到了大汗所。这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大汗所,他们向大汗忽必烈报告了“拉丁人一切事情之后”,“甚喜”的大汗于是命他们为使臣,遣往教皇所,并派了男爵豁哈塔勒一同前往,忽必烈还赐给兄弟金牌,于是马可兄弟从大汗所返回欧洲。回到了物搦齐亚之后,当时的马可已经十五岁,于是马可兄弟带上了马可波罗,本来他们想等待新教皇即位,但是恐怕耽误了时日,所以三人出发又从物搦齐亚出发,开始了马可的“首途”,“骑行久之,经冬及夏,抵大汗所。”
马可的首途,对于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就已经表现了对沿途事物记录的强烈兴趣,在朝见大汉忽必烈之后,马可汇报了沿途所见之风俗,“以及他们的书法,同他们的战术,精练至不可思议。”这让大汗极为惊讶,“所以大汗见他学问精进,仪态端方之时,命他奉使至一程途距离有六个月之地。”如果说马可首途所记录之事物是一种自我兴趣所致,那么当大汗让他出使各地,马可的记录就变成了一种任务,甚至成为了一种使命,大约马可聪明之处也在这里,“于是他颇习知大汗乐闻之事。每次奉使归来,报告详明。所以大汗颇宠爱之。凡有大命,常派之前往远地,他每次皆能尽职。”由此而得宠,也由此在中国十七年。
这是第二阶段,之后尼古剌和玛窦返回物搦齐亚,而马可留在了中国,在十七年间,“马可波罗阁下因是习知世界各地之事尤力。尤专事访询,以备向大汗陈述。”这便构成了主动为大汗记录的第三阶段。从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马可父亲和叔叔之行完全是商货行为,而第二阶段马可的加入有了完整的记录,到了第三阶段变成了一种君命,这种君命的形成,一方面是大汗有着对各地风俗和人物的强烈兴趣,“大汗既喜闻异事”,性格使然,也是为壮大帝国事业所准备,而一方面也显露了马可之聪明,他不仅知道大汗喜欢各地风情的记录,更知道大汗喜欢的是对自己有力的一切,所以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经历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就完全变成了大汗案头的参考书。
| 编号:W57·2220618·1846 |
那么在马可波罗的行纪中,到底记录了什么让大汗感兴趣的东西?从行进的路线上说,马可波罗似乎将两次的线路糅合在了一起:从小阿美尼亚到突厥蛮州,从大阿美尼亚到阿美尼亚东南界之毛夕里国,一直经过报达大城、帖必力思城、波斯大州、耶恩德大城、起儿漫国等地方,似乎就是尼古剌、玛窦带着马可波罗从物搦齐亚到大汗所所穿行的路线,但是在这里并没有说及尼古剌和玛窦,“马可波罗阁下在阴暗之中,曾为若辈所擒。赖天之佑,得脱走,入一名哥那撒勒迷之村中。然同伴尽没,仅有七人获免。”只有同伴而没有父亲和叔叔,那么这一段就是马可波罗奉使的经历,直到最后回到大汗所,但是很明显,这一线路是从西往东,符合和尼古剌、玛窦带着马可波罗的“首途”。
回到大汗所之后,马可波罗又奉使至西方诸州,这一段从八里城发足历经四个月的行程,马可波罗“述其在此道上往来见闻之事”:从八里城到普里桑干河,从涿州到太原府,经过平阳府、哈刺木逢、阿黑八里、成都府、建都州、哈剌章州、金齿州,再从缅国之都城、交趾国州、阿木州、秃落蛮州、叙州,再回到涿州,“再从涿州起行,复行四日,经过环墙之城村不少。”接着又记述了经过中定府城、新州马头、临州城、邳州城、西州城、淮安州城高邮城泰州城、扬州城、南京城、襄阳城,还有“蛮子国都行在城”……本来这是一段奉使出行的路程,但是在襄阳城记述了“城下炮机夺取之事”,因为这是一座蛮子之城,大汗军队猛攻三年不下,正在为难之际,尼古剌和玛窦以及马可挺身而出,他们献计了一种独特的器械“茫贡诺”,“形甚美,而甚可怖,发机投石于城中,石甚大,所击无不摧陷。”于是大汗命他们建造这一器械,三人命人运来材木,又从随从中挑选了两名基督徒进行建造,之后运用这一设备攻下了襄阳城,“此皆尼古刺阁下,其弟玛窦阁下,及其子马可阁下之功也。”攻破襄阳成为三人之战功,这是在整本《马可波罗行纪》中唯一是自己主动参与大汗功业的叙述,这里的疑点并非马可波罗自己成为主角,而是在马可波罗奉使的过程中,怎么又记述了尼古剌和玛窦在场的故事?
这是本书第二卷所记的过程,这一段主要是在中国,民国二十四年冯承钧为书注释中写到:“行纪诸本皆著录有波罗等在大都造机试机及在襄阳发炮等事,其事诚无可疑,且与波罗等留居十七年余之时间相符,盖彼等之还欧洲在一二九〇年也。”这里的关键是“其事诚无可疑”,也就是说他认为制造器械在襄阳城发炮而攻下是事实,而且是在马可波罗居留在中国的十七年间,但因为尼古剌和玛窦在场,所以是第二阶段的故事,也就是说,马可波罗在华十七年是两个阶段时间的总和。但是在指出这一件事“诚无可疑”的同时,冯承钧也对这里所记述的经过产生了疑问,在第二卷的《译后语》中,冯承钧提出了文本的四难:这一卷专记中国事,地名应为中国名,但是,“此书不过是大德年间之一部撰述,在中国人视之,不能算为古本,但因传本太多,写法不一,其难一。”第二,便是马可波罗的路线不明,“如自涿州至西安,又自涿州至淮安,中间究竟经行何地,别无他书可以参考”,尤其是在记述“契丹州之开始及桑干河石桥”时,马可波罗说,“自汗八里城发足,西行亘四月程。”冯承钧分析认为,“马可波罗所循之道途,似非北京西安间之官道,此道南通开封武昌桂林,而抵于童直之堕垡。其在长江以北,每五里有墩台,每一里有窝铺,城中有馆舍。正定有道通山西,马可波罗未取此道,盖其由涿州西行,遵当时上都经大同太原而赴西安之邮道也。”而从成都府出发七十日后回到涿州,然后从涿州起行,冯承钧认为,这是“第二道”,“即东南遁篮子地域或江南之道”,但是马可波罗在这里所说的方向并不严格,“未可以为准也。”而在时间上也存在疑问,“波罗经行大平原中,此处所言四日不误,盖三十年前乘骡车由涿州赴正定者,即须此时间也。”
这是第二个难点,第三则是因为这是法国人沙海昂做的注,“沙氏个人考订,颇多附会穿凿,往往妄改原书地名”,比如把行在说成是杭州府,如果这还有说法吗,那么,“写镇巢军作常州府,写塔皮州作绍兴府,未免过于武断,由是于地名错杂之中,更加紊乱”,这是版本注解的问题,而第四点也是关于译名的,从意大利文到发文,读法有异,自然影响了路线的确定。这里就涉及到《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和翻译问题,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之物搦齐亚人,当然用的是意大利文,但是他把第一抄本献给了法兰西的谢波哇藩主,“适在谢波哇藩主奉伐罗洼殿下及其妻皇后陛下之命,为孔士坦丁堡帝国各部之总代理人,行抵物搦齐亚之时。”而把此书献给他的原因就在于:“愿由此富有经验的贤明之人携归法国,出示各地。”而对本书做注的沙海昂原为法国籍,清末时归化中国,“他将颇节本革新,使人能通其读,又将各方面的注释采摭甚繁,虽然不免有珠玉沙砾杂陈之病,可能辑诸注释家众说之长,使后来研究的人检寻便利,这是他本所未有的。”这是他的功绩,但是在版本的翻译中,在通读的注释中,不免穿凿附会,也使得马可波罗的原路线逐渐成谜。
但不管如何,马可波罗在文本中“投其所好”的风格还是没有改变,而这也间接地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史料。第六十三章是“哈刺和林城”,哈刺和林城是“昔日鞑靼人离其本地以后所据之第一城”,之所以成为第一城,和忽必烈的祖先成吉思汗有密切关系,于是马可波罗记述了成吉思汗建立哈刺和林的功业:那时这里都是鞑靼人的散地,成吉思汗将其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占据其地以后,不扰居民,亦不损其财物,仅留部将数人统率一部分之部众镇守,尽驱余众侵略他州。”于是这里的人归顺于他,并且对他效忠。之后,成吉思汗又击败了长老约翰,在这场“世人从来未见之大战”中,成吉思汗取胜并且君临六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开始记述鞑靼,从他们的生活习惯、造房、妇女之地位,拜神等方面进行详细叙述;等抵达上都城,则描述其为“甚美”之宫殿,“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而一切只是铺垫,马可波罗的真正意图则是叙述忽必烈大汗之“伟迹异事”,在他看来,大汗是“极尊极强之君主”,“忽必烈汗,犹言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彼实有权被此名号,盖其为人类元祖阿聃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他所创下的便是伟业,“今特述其伟业,及其朝廷一切可以注意之事实,并其如何保持土地治理人民之方法。”他从大汗大战鞑靼大君主乃颜开始,乃颜“自恃为君,国土甚大,幼年骄傲,盖其战土有三十万骑也。然在名分上彼实为其侄大汗忽必烈之臣,理应属之”,于是大汗对其进行了讨伐,这一过程和成吉思汗大战长老约翰相似,“是战也,为现代从未见之剧战,从未见疆场之上战士骑兵有如是之众者。”最后大汗获胜。在记述了大汗开创伟业之战之后,马可波罗描绘了见到大汗时的容貌,参观大汗的宫殿,介绍大汗的诸子、禁卫、诞节等,接着技术了汗八里城贸易发达的盛况,“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人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然后介绍了大汗用树皮所造的纸币,“此币用树皮三之,树即蚕食其叶作丝之桑树。此树甚众,诸地皆满。人取树干及外面粗皮间之白细皮,旋以此薄如纸之皮制成黑色,纸既造成,裁为下式。”以及货币制度;然后再记述了大汗赈恤贫民的举措,“每年赈给每户麦粮,俾其能供全年之食。年年如此。此外凡欲逐日至宫廷领取散施者,每人得大热面包一块,从无被拒者。盖君主命令如是散给,由是每日领取赈物之人,数逾三万。”正是大汗体恤民情,“所以人爱戴之,崇拜如同上帝。”
当然,马可波罗治理扬州三年,在行纪中也记述了“蛮子之地”的情况,以供大汗参考。淮安州城是“蛮子地界入境之处”,这里“有货物甚众,辐辏于此”;宝应县城、高邮城则是“生活必须之物皆甚丰饶”,泰州城“在制盐甚夥,盖其地有最良之盐池也”;而自己治理的扬州城,“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恃工商为活。制造骑尉战士之武装甚多,盖在此城及其附近属地之中,驻有君主之戍兵甚众也。”南京城则是“富足之州”。马可波罗最多的笔墨当然是“蛮子国都行在城”,大约就是当时南宋都城临安。“既抵此处,请言其极灿烂华丽之状,盖其状实足言也,谓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良非伪语。”所谓“行在”,就是法兰西语之“天城”,所以行在便是“天堂”,这里城甚大,这是石桥巨多,这里商贾甚众,这里还有城中大湖:
周围广有三十哩,沿湖有极美之宫殿,同壮丽之邸舍,并为城中贵人所有。亦有偶像教徒之庙宇甚多。湖之中央有二岛,各岛上有一壮丽宫室,形类帝宫,城中居民遇有大庆之事,则在此宫举行。中有银制器皿,乐器,举凡必要之物皆备,国王贮此以供人民之用。凡欲在此宫举行大庆者,皆任其为之。
当然这里还有“蛮子国王之宫殿”,作为当时世界最大之宫,“内有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世界良果充满其中,并有喷泉及湖沼,湖中充满鱼类。”这宛如人间天堂之存在,怎不令大汗向往?而在马可波罗笔下,大汗要得到行在城及蛮子地方九部,是为了安居乐业,“大汗在此第九部地所征课额,既如是之巨,其他八部收入之多,从可知也。然此部实为最大而获利最多之一部,大汗取之既多,故爱此地甚切,防守甚密,而以维持居民安宁。”而这或者就是马可波罗所认为大汗之伟业。当然,从西方而来见识了大汗之伟业,对于马可波罗来说,也并非仅仅是“投其所好”,东西方之间的交通也是马可波罗为世界的开放所做的贡献之一,“盖据本书卷首引言所云,世人不论为基督教徒或回教徒,鞑靼人或偶像教徒,经历世界之广,无有逾此物搦齐亚城之名贵市民尼古刺阁下之子马可阁下者也。恩宠的上帝。阿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