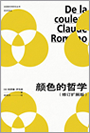2025-08-24《颜色的哲学》:呈现于“生活世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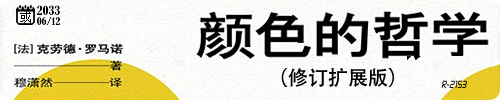
颜色在这个为了我们的世界中扩散,在我们居住的世界中,在我们行动的世界中,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也就是这个唯一值得被称为世界的世界。
——《对主观主义的批判:生态学的色彩观》
我们每天看见颜色,我们每天表达颜色,我们每天用颜色构筑我们的生活,的确,颜色就在我们的世界中,在我们居住的世界、行动的世界、生活的世界中,但是当克劳德·罗马诺提出这是“世界的世界”,已经把颜色纳入到了哲学的框架中,已经在思考一个关于颜色的“哲学问题”,而这个“颜色的哲学”也必须从最基本的——经验感知——层面为出发点提出问题:我们能感知到相同的颜色吗?我们所命名、言说和表达的“红色”就是在客观意义上属于同一种颜色吗?就比如这本书的封面上那些几何图形的颜色是一种“黄色”吗?内页都是我们所看见的“白色”吗?
不管是看到还是表达,我们首先一定是从经验出发的感知,那么这种感知是纯粹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还是基于神经学、生理学以及心理学的主观主义?罗马诺首先从这个问题入手,他把对颜色的认识看成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德谟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是最早对颜色进行哲学思考的思想家,而到了近代,出现了以牛顿和洛克为代表的古典颜色观,而理解洛克和牛顿对于颜色的阐述则要回到笛卡尔的认识论。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提出,每种物质都有一个首要的属性,要么是思想,要么是广延,广延的物质具有可延展性的属性,他以著名的蜂房蜡块分析指出,物质的广延并不随着形状的改变而改变,但是颜色并不是一个屋里属性,在他看来,当颜色投射到事物之上时,我们才会感知到“颜色”,所以颜色不是广延物,而是思维物,它是一个单纯的“观念”。1666年罗伯特·波义耳发表了《根据主体哲学的形式和性质的起源》,在文章中他认为那些存在于物体中的秉性或导致感知的体验的秉性是十分重要的,它构成了感性的性质,在他看来,颜色是一种秉性的属性,也是一种关系的属性,只有在主体感知中雪才是白色的,否则就不是白色,只有当雪与视觉器官联系在一起时,它才是雪,所以秉性在于雪本身,雪只有与具有视觉能力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并且将其抽象化之后,才是白色。
笛卡尔对物质属性的分析和波义耳关于秉性和关系的阐述,构成了洛克的颜色观,他认为,颜色是一种观念,“我把心灵在自身中感知的任何东西称为观念,当大脑思考时,任何感知都蕴含于精神之中。”但是他又指出,观念是对某一事物的内部感知,它源于两个方面,感知和反思,颜色源自观念中感官的一部分,但它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物体的性质,也就是说,颜色既包括灵魂中的一种观念,也包括物体本身的一种性质,这就是洛克所论述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第一性质是物体的内在属性,它独立于它们与感知主体的关系但从属于感知主体,第二性质不是内在的属性,是既是秉性也是关系的属性,只有与感知器官建立关系才属于物体的力量,而第二性质又是基于主要性质的,也就是说秉性和关系属性是给予内在的属性,这就导致了洛克的一种矛盾性,罗马诺认为洛克的立场表现了一种基本的犹豫不决:他把颜色定义为一种观念或感觉,又认为它是一种属于秉性的属性,既是一种主观的存在,也是一种客观的属性。
同样,牛顿的自然哲学在颜色问题上也表现出某种矛盾性,在牛顿看来,颜色是一种光谱,当白光被两种透明介质所拦截时,就会分解成光谱,他描述这种光谱由七种颜色组成。牛顿把颜色说成是光的一种属性,那么颜色是不是就是光?牛顿从实验中得出的颜色定律并不适用于化学的颜料,比如把牛顿提到的七种颜色混合根本得不到白色,而画家调制颜料得到的颜色也并非和牛顿的说法相一致,所以后来牛顿承认,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自然或光线中都没有颜色,颜色之存在于感知者的感官或灵魂中。无论是洛克的观点还是牛顿的看法,他们都陷入到一种矛盾中,这种矛盾既把颜色看成是一种客观的属性,又归结为和主体的感知有关。在洛克和牛顿之后,出现了对颜色的另一种阐述方向,诺瓦利斯认为,自然就是无意识下的精神本身,是“通向内在自我的神秘道路”;席勒抱怨牛顿的自然理论是“时钟的死循环”;歌德和谢林认为自然界中的精神就是光,歌德还以象征的方式将我们对色彩的感知类比为对道德领域中的善与恶;而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提出:“光,就像自我,或纯粹的自我意识一样,被分成一束束的射线。”
叔本华在《论视觉和颜色》中,提出了从生理学的角度来探讨颜色,他用神经生理学的分析取代了康德的超验分析,在他看来,视网膜和大脑活动为颜色的感知提供了基础的解释,由此他提出了“颜色极性”的观念,“对我们来说,颜色只是眼睛本身活动中产生出的极性对立的一种表现”,所以他得出结论,“颜色在本质完全是主观的”,罗马诺由此从“世界是我的表象”出发,将叔本华的这一观点表述为:“颜色是我的表象。”当颜色成为精神、成为纯粹自我意识,成为“我的表象”,也就意味着颜色完全变成了一种主观主义:成为什么样的颜色,取决于看它的人,取决于一种感知,那么它就陷入了一种相对主义,甚至是一种唯我论,“我们将永远无法与他人分享我们的彩色世界;我们将永远无法确定,当我们使用‘青色’或‘品红色’这些词时,我们谈论的是相同的色调。”
| 编号:B83·2250705·2322 |
在陷入物质主义的客观主义和唯我论的主观主义矛盾中,罗马诺提出了另一种理论,那就是吉布森的“生态学”:感知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检测到我们环境中一定数量的物理的不变量。也就是说,对颜色的感知既在一种环境的物理属性上,也在一种主体的心理属性中,“将具有生命需求的生物与环境结合起来的那种关系的一种可见的表现”。具体分析来说,当动物进行感知时,就是从光学环境中“捡”到了视觉信息,也就是说,感知是一种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它在大脑里构建了一个“内在的模型”或现实的表述,这就是吉布森感知理论的出发点。虽然吉布森的“生态学”通过感知行为将外部信息和内部模型建立了关系,既避免了主观主义,也不再是客观主义,但是他又否定了感知在经验和现象层面的讨论:吉布森把“经验”理解为观察者主观的、内部的体验,把“现象”理解为事物在我们头脑中的表现,所以他的“直观”不是经验的范畴,也不具有现象学的意义。
“一个以信息定义的世界不可能包含类似于颜色的东西。”这是罗马诺对吉布森“生态学”的一种驳斥,很明显,罗马诺要将对于颜色的阐述回到“现象学”层面,而且是胡塞尔现象学层面,在他看来,经验并不是“主观”的东西,它是我们与世界本身的接触——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中介,即梅洛-庞蒂所说“对身体的把握”,让经验回到“世界本身”,这个世界就是胡塞尔称为现象世界的“生活世界”,“颜色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不是因为它由简单的信息集合组成,而是因为它属于现象世界。”颜色是现象,但不是主观的、精神的现象,而是事物呈现给我们的方式本身;它不是对次要属性的描述,而是以观察者为参照进行描述并且是位于主要属性“旁边”的某处,所以,颜色构成了“生活世界”,“颜色在这个为了我们的世界中扩散,在我们居住的世界中,在我们行动的世界中,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也就是这个唯一值得被称为世界的世界。”
生活世界就是现象世界,就是为了我们的世界,它是在表述中不断返回的世界,它构成了科学认知前的实践“土壤”,也构成了实践本身,“它都是以生命世界的这种直观的‘土壤’为前提,并在其本质上依赖于它。”这就是现象所具有的朴素的客观性,“这种朴素的客观性概念是先于科学的理想化的:只有我体验到在生活世界中那些表现独立于我自己的意义,我才能通过通往数学理想化的极限,从而得以推进绝对独立于任何视角和主体的理念,从世界‘本身’存在的属性的角度来定位自己。”而罗马诺在歌德对颜色的阐述中就发现了现象学的向度,歌德在《颜色理论》的导言中就写到,“我们相信我们应该得到哲学家的感谢,因为我们试图将现象追溯到源头,它们只是在那里出现和存在,而其余的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解释。”回到现象的源头,就是回到朴素的、前科学的直觉之中,就是胡塞尔对于现象学的阐述:“回到事物本身。”也由此关于颜色的理论既不会陷入客观主义也不会落入主观主义。
但是,这种关于颜色的“现象”是不是就有一种必然性和普遍性?对于这个问题所要寻找的答案就是要建立颜色的“逻辑”,将颜色从视觉器官的偶然性中感知变成必然性秩序,从而决定颜色的本质,但实际上,从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原则出发就是建立这种颜色逻辑的必由之路,但是罗马诺却又奇怪地引入了分析哲学的“逻辑”,这似乎也成为了毫无意义的“分支”:虽然分析哲学也说逻辑,也是追求必然性和普遍性,但是“逻辑”更多是一种语言,甚至是语法,维特根斯坦就认为,颜色几何学所表达的必然性根本不是关于颜色的本质,而是我们对颜色的描述,我们在语言中如何使用,即使有必然性也是纯粹的约定俗成。罗马诺对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进行阐述之后,才进入到“从语法到现象学”的本质探究中,而关于颜色本质的探究灵感就来自胡塞尔对本质的定义:对于唯一的对象来说,本质就是“它的成分常驻着一种本质的谓词,这些谓词必须归属于它”。
胡塞尔的这个本质定义看起来是一种循环论证,本质就是一组本质的谓词,但是本质谓词具有的明确性就是:是他所是,“这个谓词只要它是它所是的,它们就必然发生在这个对象上。”本质就是一种先验存在,不是“先于所有可能得经验”,而是“从它有效性的角度看,它先于所有事实”,也就是在认识论意义之前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就是一种前科学的直觉,就是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描述,“现象学声称它是哲学中的一种具体方法,它放弃了伟大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放弃了意图涵盖现实的全部的系统的构建,从而栖居于一个更温和的住所中,远离伟大的形而上学的争论,并通过简单描述我们的经验的方式去接近问题,它在第一时间向我们以一种充满质朴的形态呈现。”对于颜色的逻辑来说,就是“世界的逻辑”,在这样一种呈现其本质的逻辑中,颜色就是世界本身。
如果说第一部分罗马诺探讨的是颜色哲学的“认识论”,第二部分则是指明了颜色哲学的逻辑,那么第三部分就变成了关于颜色的艺术哲学部分,即颜色的“美学”,它处理的是感受,它以理解为中介,但是罗马诺似乎一反常规不是在惯例中探讨美,而是寻找色彩关系背后的无限可能性,“绘画是通过布局颜色的力量来建立一个关系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来重新激发颜色间的协调与不协调;可以说,绘画是用每一种颜色来重构色环。”歌德的彩色阴影理论被印象派用来画出与客观化和物化视觉相反的光线,塞尚说:“颜色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就在和新生的世界重新建立联系;象征主义在对比、互补和对立中寻找色彩的新语法,模仿变成构图;野兽派抛弃了色彩的真实性,马蒂斯说:“一幅画就是控制节奏的协调。”对于颜色之美学的探索、发现,正如梅洛-庞蒂所说:“这是一种轻轻接触,使颜色或可见的世界的多个区域产生共鸣的东西,是一种特定的差异,是这个世界的短暂调制,因此,它更多的是物和颜色之间的差异,是颜色或可见性存在瞬间的结晶。”
主体和客体,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和超验主义,物理主义和心理主义,这些二元论都不是对颜色哲学的真正阐述,只有克服二元论,颠覆古典科学的形而上学框架,才能让颜色进入“生活世界”:它与我们的肉身不可分割,它是我们的世界,回到事物本身的颜色就是“存在的色调”,“我们可以说,颜色是一个世界:因为它有自己的深度,有自己的振动和光芒,有自己的节奏,有处理我们的情绪色调的方法;因为颜色可以与其他模式的知觉交流,所以它有着一个整体的属性;也许可以这样说,颜色是整体本身的呈现模式。”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