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4《诗的复活》:首先在万物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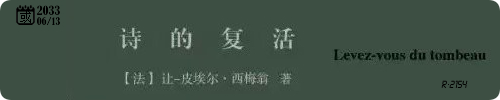
想到,有些嘴唇
在弥留之际,
正在等待,我们的脸颊
去亲吻它
——《我们当中,有谁不曾在某天醒来时》
弥留,是走向死亡的开始,但是他却在等待,等待有人去亲吻脸颊,等待仿佛放大了亲吻的时间,等待也推迟了死亡到来的时间,就在这弥留和等待之中,亲吻实现了一种叫做“重生”的时刻。《从墓中,站起来吧》中最后一首诗,仿佛也指向了生命的终点,但是它却在弥留而等待中“重生”——西梅翁诗集中唯一有“重生”的一首诗,它直接提出的就是“何谓重生”的问题:在爱的时刻仅仅有丁香的颜色显得微不足道,而是想到在某个地方,还有“世上唯一的树”,不仅只有颜色,只有香味,它正等待着我们“去拥抱它”,依然是等待,依然是真正爱的时刻,像嘴唇亲吻脸颊,这就是所谓的重生。
重生,就是“诗的复活”,在一半是法文一半是中文的诗集中,西梅翁所呈现的“诗的复活”只有60多首诗,诗的复活首先是一种死亡,然后是死亡后的等待,然后是等待中的亲吻,最后是醒来,那么,“何谓重生”就指向了“何谓诗歌”这一问题,未被命名的第一首诗可以看做是“何谓诗歌”的序言,而第一句话就指出了诗歌的使命,“诗歌最终应成为主宰”,但是在诗歌成为主宰之前,它又经历了什么?诗歌没有权力,诗歌的思想像马像风一样,这就是诗歌的“无序”,而诗歌的无序又是一种“高度渴求无序的秩序”,在无序和有序的张力中,在否定和肯定的关系里,诗歌真正要达到的境界就是自由,“唯有自由,不会溶解在歉意里”。那么,什么是“无序的秩序”之自由?自由就是从树木、岩石、雨水、蜜蜂和河流之中找到它们的理念,将理念解放出来“识别出/我们所不知道的歌曲的女主人”;自由就是从历史上凶猛的人们的虚荣中找到爱情的力量,“我们所做的,只有把握,却不拥抱”。西梅翁把诗歌的自由归结为自然和爱,归结为理念的解放和爱的拥抱,但是真正要达到自由的则需要诗人的参与:诗人给予但无所求,诗人用双手、眼睛和嘴唇去战斗,诗人抵抗丑陋和虚空,诗人是恋爱的反叛,“他甚至不是他的敌人们的敌人/因为他不会吃他们的苦面包”。诗人是给予的诗人,诗人是战斗的诗人,诗人是反叛的诗人,当然诗人也是重生的诗人,“杀死诗人,噢,洛尔卡/诗歌却会在追随它的阳光下重生”。序诗中的“重生”从诗歌之自由到诗人的使命,最终确立了“诗歌的治理”,“但生活,就是为每个人准备的/他的欲望的唯一的对象”,那就是生命,欲望的生命,爱的生命,自然的生命,重生的生命。
“诗歌最终应成为主宰”的序诗其实将“诗的复活”归结为两部分:何谓诗歌?何为诗人?而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按照自然分辑而进行了阐述,第一部分的《七弦琴》可以看做是西梅翁对于自然之诗的抒情,“七弦琴”是和自然相关的鸟之弦、树之弦、寂静之弦、河流之弦、风之弦、时间之弦,阴影之弦,它们奏出了复合式的自然之声,它们构成是诗歌即万物的理念:在《鸟之弦》中,西梅翁让诗歌化身为鸟,“在这飞升的话语中/有人的内在飞跃,/升腾在自身之上”,最终活在“枯萎的树叶与太阳的火焰之间”;在《树之弦》中,树木挺立在疯狂暴雨和雷电之中,它在吟唱中静默,在静默中隐藏,并为人们指明方向,“向迷路的恋人们/向流浪的动物们,迷失的灵魂们/招手示意”;世界是寂静的,肉身是寂静的,但是世界的寂静让欢乐变得遥远,而肉身的寂静却为灵魂留下了空间,“在人声的喧嚣里,寂静经过,/如游蛇,滑过草丛”;河流穿越我们,河流“一直走在我们前面”,河流撞击石头发出郎朗的笑声,而《河流之弦》所响起的就是生命之声:它的清澈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纯净又清新的意味,我们的身上也携带着河流,脸庞浸润在喝水中,疲劳的眼睛被洗净,欲望中蛰伏着河流的光泽,河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在场”的,“未来将有的,和过去有过的,/完全都在这当下的秩序里”,所谓“生生不息”,就是让我们携带着“我们还未能拥抱的美”;风是真正的诗人,在习习微风或狂风暴雨中找到诗歌素材,给所有的词语穿上衣服或者解开衣服;《时间之弦》里生命在丈量,生命在抚摸,“在嘴唇上,放上一丛叶片,/而鸟儿的歌声,从那里,/袅袅地升起”;阴影无处不在,但阴影不是吞噬,不是埋没,而是“将人延展”,将身躯、姿势和欲望延伸到自身之外,而且阴影绝对不会背叛,“阴影,向你致敬/不会包含在死亡里的同伴/你是所有活生生的万物/沉默而温柔、含蓄的朋友”。
| 编号:S38·2250720·2329 |
西梅翁奏响了“七弦琴”,是在大自然中发出了声音,更是让自然之声融入了生命,多声部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多重演绎,而西梅翁所引用的题辞就来自于荷尔德林的《乡下的散步》:“因为这无关力量,而关涉生命,/我们的欲望:要快乐与方便同在。”诗歌来自荷尔德林,翻译来自诗人雅各泰,这是荷尔德林“散步”时敞开的心弦,这也是雅各泰“瞬间一代”中感受到的生命心弦:他站在文明的废墟上希望用诗歌与世界重建感性的联系,“真正的生活是可能的”的伦理观就是生命观,而比雅各泰小25岁的西梅翁也在召唤着成为生命主宰的诗歌,它是世界的栖居,是自然的发现,是生命的出发:第一部分《七弦琴》是对自然之歌颂,第二部分《从墓中,站起来吧》则从自然走向了生命之美、生命之真、生命之本,“从墓中,站起来吧”的呼喊和宣告,就是“诗的复活”,从死亡开始的复活,由死亡必然的复活——援引的就是梭罗《自画像》中的那句诗:“那个人,无论是谁,/假如生命和他的气息/没有同样的年纪,/只会有心灵的死亡”。
其实,不管是第一部分还是第二部分,西梅翁似乎都没有从死亡先行开始,死亡是他的一种预设,但是这种预设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死亡的不安、恐惧和悲伤,而是直接从死亡的墓地站起来,欣喜而跃,御风而行,这就回到了何谓诗歌的一种阐述中,“您称作情绪的那种无声的涌动,/首先在万物之中”,诗歌之声就是万物之声,诗歌在万物之中,在自然之中:这是一种美的存在,“任何美,皆有/它所揭示的奥秘的形态”,所以万物的神秘早就了持续常在的美;这是寻觅思想之路,思想从身体里诞生却又超出万物,“她是在万物之间的一具躯体,/会敏感于青草与苦痛的肉身”,然后通过火焰去构想,然后牵连生命的思念;这也是万物之灵的哲学,蛇和石头发出笑声,黑夜在歌唱,沙漠中的哲学就是用欢乐和痛苦的回响震动灵魂。所以当我们与事物交流,当我们从事物中发现美、思想和哲学,它们自然成了生命的象征,“噢,静默的事物/让我们,以坦然的姿态/栖居,在生命里”(《经过道路和山顶,噢,愿它赐予我们》)
而在生命之中,我们总是不可避免的遇见死亡,那么在死亡和生命之间,又有怎样的人生百态?“那个人,在死前,永生,/畅饮天下/如青春的美酒”(《我们渴求,我告诉你,我们渴求》)这是一种对于死亡的态度,在死亡到来之前带着生命、呐喊和光,走向永生,这是人类的一种渴求;“去死,还是不去死”这是一种生命的提问,每时每刻都发出拷问,而有的人选择的是:“活着,却似死去”,把生活隔离,道路上充满灰尘,站着死去成为生命的敌人,所以活着就像死去了一般;甚至还有我们制造的死亡,“在古老太阳的金发下/每天,人们屠杀成千上万的躯体/亲手掐死青梅竹马的恋人/老人们的善良/扼住年轻的情人们的咽喉”(《如此充满不可抗拒的爱》),人类是死亡悲剧的始作俑者,对于自己,那些愤怒,那些烦恼,是不是也构成了我们死亡的牢笼?或者“在死前,永生”,或者“活着,却似死去”,或者人类制造了死亡,活着和死亡之间的不同选择传递出生命的姿态,而它们最需要的就是对于生命的理解,一种美、思想和灵魂之哲学,只有在生命的意义上,才能从死亡的弥留状态中找寻到亲吻我们的嘴唇。
“死亡,是我们的面包:/是它,让河流,充满渴望/和歌唱,/也是在话语中的记忆”(《就算疲惫,我们下一回,再抱怨吧》),死亡是面包,所以对于生命来说,活着是需要,把握死亡也是一种需要,只有在死亡中挺立、寻找天空,生命才会昂然有力凌空起舞,由此西梅翁构筑了一种生命的“他者哲学”:从对立面诞生,“如同水,从岩石中流出,/如同鸟,从枝头诞生,/如同在绝望的理解中,获得的希望”(《生命,只能从他者中,诞生》),诗歌从万物中诞生,“在词语之前,诗就产生”,而生命就是从他者之死亡而诞生,活着的典范是如同狂草的“疯狂的想法”,如同野蕨的“欲望的执意”,如同树皮“无穷无尽”,如同无意的歌曲在空中飘散,如果这些是万物之中的生命写意,那么我们也需要创造一个生命世界,“如此忠实于:/生生之道,秘密的勇气/灵魂之叶,莽撞的新生,/在骤雨中,瑟瑟发抖,/如根茎,沉思着,梦想/直攀上那山顶”(《有一天,走过一片杂乱无章的森林》)
从活着的典范,到创造生命的世界,西梅翁从自然之诗歌走向了自由之诗歌,而从这里开始,诗人便承担起了创造生命和自由的重任,《致安德烈·维尔泰》可以视作西梅翁对“诗人何为”的一种宣言:诗人会懂得与石头的沉默交谈,会在沙漠中找到充实的东西,会用双手和双脚去领会,会从鸟儿的叹息中学习,“最终,用这一切,他用他的竖琴,/造就了诗歌,/走出枯死的沼泽/和闪闪发光的群山”。第三部分《热烈的理论》是西梅翁向诗人的致敬,也是和诗人的对话,更是在阐述“诗人何为”:他在致拉斯洛·霍瓦特的《在多瑙河水中的希望》中把诗人看作是“用蓝色的字迹/像烟斗的烟雾,一样坚持/在过于平滑的空气里/加进一股刺鼻的匪气”的变化不定者;在致让·马里·巴尔诺《献给大海归还的人》中,西梅翁把诗人形容为历经磨难的智者,只有像尤利西斯完成奥德赛之旅才能抵达真理,“兄弟,从滚滚的波涛中,归来/当我们从诗中勾勒的死亡中,返归时/将万物从一体之中分离,无尽地重生”;诗人是培育“语言绝对之花”的科学家,诗人把呐喊和沉默献给诗歌,诗人的嘴巴里是不妥协的味道……
诗歌在万物之中呈现其思想和美感,诗人在生命之死亡中创造重生的世界,无论是对于诗歌体现自然本质的属性,还是诗人寻求自由的秩序,对于西梅翁来说,也许真正找到诗歌之“重生”和诗人之创造的意义的就是《后记》中那首献给“黑人性”思想奠基人、政治领袖艾梅·塞泽尔的诗,“向你致敬,艾梅·塞泽尔/向你致敬!/我们需要你,/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你”,从塞泽尔这位诗人身上,我们需要的是从受伤的思想里淌出鲜血,需要在狂风中连根拔起的美,需要用反叛的语言迸发出树木、残阳和忧愁的风,更需要回到诗歌找寻和发现解放奴役灵魂的力量,这就是塞泽尔所说的“人民与诗歌一起诞生”,这才是西梅翁赋予“诗歌的复活”的全部诞生意义:
你为我们指明了“隐喻之路”,
你说,要让我们去走那条路,
让我们一次再一次,与你一起,
成为火山之子,
我们会像你一样叫喊,直到翩翩起舞,
欢笑,径直流到我们的血管里
反叛,“在紫罗兰和银莲花中,崛起,
在我们沾着血液的每一步里”,
向艾梅·塞泽尔致敬,向他感恩!
一次又一次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