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2-09《想象动物志》:几乎包括整个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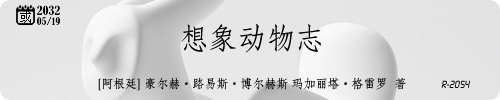
多少个世纪过去了,阿宝阿库只有一次达到完美身形。
——《阿宝阿库》
完美就是一次重生,或者说,重生对于阿宝阿库来说,就是一次达到完美的过程:在奇陶加尔胜利塔的第一级台阶上,阿宝阿库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当有人经过它上塔时,颤动便会赋予它生命,清醒过来之后它的体内会透出一种光,然后身体开始移动,它会跟着向上走的人一级一级攀登,每上一级台阶,它的肤色就会变深一点,它的身形会更完美一点,它发出的光会更明亮一点,直到那人登上胜利塔的塔顶,阿宝阿库也会在攀上最后一级台阶后获得完美身形。
阿宝阿库之所以能走向完美,就在于唤醒它的人,而且必须是精神上进化了的圣灵,必须最后登上胜利塔的塔顶。也就是说,阿宝阿库能否抵达完美是和它所跟随的人是不是在精神上是一个完美者——许多个世纪以来,阿宝阿库只有一次达到了完美。也就是说,它只有一次遇到了在精神上进化到了最高层次的人,这个人就是真正的朝圣者,仿佛胜利塔就是为他而建造的。这个唤醒它并将它带向完美的朝圣者是谁?这个问题也许不是关键,关键是属于阿宝阿库的命运:如果不能登顶,那么阿宝阿库就像是瘫痪了一样,身体是残缺的,颜色是模糊的,发出的光是飘忽的;更为关键的是,当朝圣者走下胜利塔时,阿宝阿库就会跟着滚下来,直到最后跌落到第一级台阶上,也就是回到了起点:它体内的光便熄灭了。
对于阿宝阿库来说,它还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但是只有一次达到完美身形意味着它不再有机会遇见朝圣者,从塔顶回到第一级台阶,从第一级台阶再往上,只有一次的完美也意味着阿宝阿库就像是西西弗斯一样,不停地推动石头向上,又会从最高处滚下来,然后再往上推动石头,如此周而复始,完美就成为了一种再也无法实现的愿望。阿宝阿库的故事,并非来自于《一千零一夜》,而是英国军官、探险家、东方学家和人类学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记录在《一千零一夜》的译本注释中,注释中的阿宝阿库是伯顿根据另外的传说辑录而成的,它其实就是对“完美”的阐释:阿宝阿库需要从底层走向最高处才能达到完美,朝圣者也只有从最低一级台阶到最高层,才能欣赏世上最美妙的风景。但是最美妙的风景在奇陶加尔胜利塔的塔顶,“只有不相信下面这个传说的人才敢登塔”,而这也成为了朝圣者的命运写照,他们正像阿宝阿库一样,只有唯一的一次达到了完美。
一次的完美是建立在无数次的不完美基础之上的,阿宝阿库类似西西弗斯的命运就是这个“想象的动物”具有的象征意义。《想象动物志》开卷的第一个故事,是不是就像是昏昏沉沉的阿宝阿库一样,在第一个台阶等待朝圣者将它唤醒?这是标注着“博尔赫斯全集”的一本书,在此之前已经阅读了“博尔赫斯全集”的第一辑、第二辑的所有作品,以为博尔赫斯的作品已经被全部收录其中,但是之后又出版了“博尔赫斯全集”的第三辑共12册,这其中除了《文稿拾零》之外,似乎其他图书都是博尔赫斯和其他人合著的幻想故事、游戏文章、电影脚本、文学评论、演讲实录,包括《英国文学入门》《美国文学入门》《市郊人·信徒天堂》《布斯托斯·多梅克纪事》《布斯托斯·多梅克故事新编》《伊西德罗·帕罗迪的六个谜题》《两个值得回忆的幻象》《死亡的样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语言》《关于〈马丁·菲耶罗〉》《日耳曼中世纪文学》等。在购买了第一和第二辑的28册之后,并没有急于购置第三辑,因为对这些被纳入“博尔赫斯全集”的图书还是有着太多的存疑:它们真的是博尔赫斯的作品?
也许是和博尔赫斯有关,也许博尔赫斯写作了其中的几篇,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博尔赫斯所乐意尝试的事,所以在存疑中最后拒绝将它们纳入博尔赫斯的文学世界,而“本体论”中对博尔赫斯作品的阅读也止于前两辑,30册图书构成了“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它就是一种完美的体现——甚至图书所组成的5*6方阵也完全是一种形式上的完美。但是当这本《想象动物志》变成第31本阅读的文本,这个迷宫的完美形式是不是由此被打破?被阅读的博尔赫斯世界是不是会像已经到了胜利塔最高处的阿宝阿库一样,也因此而滚落到最初一级台阶?但愿这是一个读者的想象,但是“想象的动物”并没有真正打开想象的世界,它反而关闭了想象的世界,关闭了博尔赫斯的迷宫,反而以直接的、平面的、单一的方式变成了动物集的汇编。
文本来源有神话、传说、历史、典籍、文献、文学作品,想象的动物或存在于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或出现在典籍文献、文学作品里,或流传于道听途说、野史逸闻,或出现在人类的梦境里,这116篇文章里的动物的确是“想象的动物”,但是这个想象不是一种动词,而是一种静态的名词,是已成其形的物,在这个意义上取消了动物被书写的可能——也许这些动物的书写和博尔赫斯有关,仅仅在于博尔赫斯有过记录和整理,但是它们并没有成为博尔赫斯的“想象”,合作者玛加丽塔·格雷罗反而是另一个“写作者”?无从考证在这本书里两个人的书写到底占了多少比例,也无从知道博尔赫斯对这些笔记的态度,以如此似是而非的方式将其列为博尔赫斯的代表作品,也许是出版社的一种想象,而在这想象中,“博尔赫斯”只是一个被命名的符号,一个吸引眼球的标签,那么,这就成为了“另一个”博尔赫斯。
的确,“想象动物志”的很多动物只限于“想象”本身,或者就在想象得以展开时戛然而止,很多甚至还保留在作者自己的文本里,比如《卡夫卡幻想的动物》《C.S·刘易斯幻想的动物》《爱伦·坡幻想的动物》《C.S·刘易斯幻想的爬行动物》,都直接引用《乡村婚礼筹备》《皮尔兰德拉星》《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等文本,从文本到文本,从想象到想象,并没有提供可能性,文本依然被束缚在文本之中。但是唯一可以感受到博尔赫斯“想象”的文字只有《序言》了,它其实言说了真正的想象,“本书的书名完全可以囊括哈姆雷特王子、点、线、面、超级立方体以及所有同类的词,甚至也许可以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和神祇。”想象是什么?是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延伸,甚至是对它们最后的取消,所以以“想象的动物”这个意象言说的是一种无限,“总之,几乎包括整个宇宙。”在这里,一方面是它形式的无限性,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有来自于罗伯特·伯顿、弗雷泽、老普林尼等人难以穷尽的著作,所以这是一本“万宝全书”,另一方面,无限性意味着可能性,想象就是赋予可能性一双翅膀,所以从这本书开启的整个宇宙包含着无限未来,而且在每一个我们到达的点都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一本书必然是不完整的,每出一个版本都是未来版本的核心,可以不断再版直到永远。”正是这种不完整具有了完整的可能,动物如此,宇宙如此,作者和读者的世界也是如此——它们所组成的都是阿宝阿库的世界,从第一级台阶往上爬,从高处回到第一级台阶,如此循环,不是命运的反复,而是不断抵达可能的完美,发现宇宙的秘密。
| 编号:C63·2241213·2216 |
“几乎包括整个宇宙”是博尔赫斯对于“想象”本质的阐述,不完整的文本是完整之路必然开启的第一步,这就是“想象动物志”在读者意义上真正具有的想象意义,所以沿着这个需要读者自构的宇宙第一级台阶出发,不如让自己也成为阿宝阿库。里面的动物中有一类就指向了人类无限的宇宙:它们是《球形动物》,因为球体表面每一点到球心都是等距的,所以球体是所有固体物中最匀称的,球形动物就是“完美”的象征,柏拉图认为造物主把世界造成了球形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这就是生命体具有的完美性;五百年后在亚历山大成,奥利金认为享有天福的人将会复活成球形,然后滚动着进入永恒的天堂;在文艺复兴时期,瓦尼尼重提了把天视作动物的观念,新柏拉图派的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提出了地球的毛发、牙齿和骨骼;布鲁诺认为,行星是巨大的、安静的动物,有热血、有理智,也有规律的习性;开普敦和英国神秘主义者罗伯特·弗拉德对谁先提出地球是一个活生物的观念发生过争执,开普敦把地球上的涨潮和落潮看成是睡眠和清醒的不同状态……
地球是生命体,生命体具有球形的完整形式,这是想象所赋予完美宇宙。还有《两个形而上学动物》中是关于思想起源的力量,孔狄亚克针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想象出了一座大理石雕像,它的结构和人体一样,这座雕像从感觉到思维的过程就是人的认识:先有了嗅觉,之后有了注意力,然后有了记忆,又产生了比较、判断和思考,之后就有了想象、意志、爱恨,经历了这些之后雕像有了数的抽象概念,最后从概念出发有了自我,这就是孔狄亚克“想象”出的形而上学动物。而另一个形而上学的动物则是洛采的“假象动物”,它的皮肤上有一个可移动的感知点,感觉的接受和发射使他不再与世隔绝,而是发现了外部世界,由此区别了静态物体和动态物体。动物凭感觉发现外部世界并不求助康德的“范畴”,而是通过自身的认知产生了造物。和“球形动物”对人类完整性的指涉一样,形而上学的动物指涉的是人类的认识论,此外,还有《柯罗诺斯或赫拉克勒斯》中柯罗诺斯或赫拉克勒斯的结合意味着必然性,“柯罗诺斯,那条龙,从身体里排出一卵三胎:潮湿的太空:无限的混沌和晦暗的阴阳界,在卵之下它产下一个蛋,从蛋里生出了世界。最后一个本原是一位神,男女同体,背上长有金翅膀,两侧长出牛头,头顶是一条巨龙,堪比各类猛兽……”“凤凰”是斯多葛派认为宇宙灭亡和新生这种无始无终过程的一面镜子;“海马”在宇宙学家卡兹维尼的专著《创造的奥妙》中认为,和陆马是一样的,而不是海中的海马,十八世纪的旅行家王大海在《中国杂记》中更是将海马想象成“宜远离江河,一旦见水,则旧性复发,遁水而远去矣”;“泥人戈仑”的制造秘方和“二百二十一个门道的字母标号”有关,额头上的“真理”字样,如果不小心将首字母擦点,就变成了“死亡”……
动物是宇宙,宇宙也是动物,想象可以将不同的两者结合在一起,形而下的物也在想象中变成了形而上的思想。在《想象动物志》中提到了王大海和他的《中国杂记》,而更多提到的则是和中国有关的“想象的动物”,比如收录在杰·威洛比-米德《中国的食尸鬼和妖精》中的天鹿,“如果天鹿冒出来见了光,就会化成有恶臭的液体,毁掉整个国家。”还有打三次鸣的“神鸡”,“神鸡是‘阳’的祖先,是天地间阳性的起始。”河图洛书中的“神龟”,“有人说,这只爬行动物,天下龟之母,是由水和火构成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由一种极不寻常的物质构成的:那就是形成人马座的星光。”还有和孔子有关的“会造雨的商羊鸟”,“ 据说,实际上此鸟先是汲江河之水,然后将水洒向地面。”中国的凤凰是大恩浩荡的明证,是神兽,和中国龙一样,和西方的龙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西方的龙,充其量就是吓人,说到底也就是个可笑的形象;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具有神性,好比一位天使,同时又是一头狮子。”
其实对于中国文化中的那些“想象的动物”,它们明显区别了西方的动物,《中国动物志》中的动物是虎头人面的“强良”,是长着两个头的“䟣踢”,是与天帝争斗的刑天……所辑录的15种动物标注的处处是《太平广记》,但很多来自于《山海经》。和《中国动物志》相对的是《美国动物志》,收录的是像茶壶一样发出咕噜声的“茶壶精”,是头像虎头却专吃斧柄的“斧柄犬”,是在树上筑巢善飞怕水的“高地鳟鱼”……和《中国动物志》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各种想象的动物都和人有关,或者都是人的某种变形,但是《美国动物志》中的动物都是大自然奇异的一部分,和人类没有特别的关系,只是自我的变异——和龙、凤凰等想象的动物在不同文化中具有的象征意义一样,“万宝全书”就是对种种可能性的辑录,它启发着完全不同的想象世界。
实际上,想象之所以不是现实的,不是规定的,就在于它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可能性解构了必然性和唯一性,在这本书里,就出现了很多“双面”的象征。《斯威登堡的天使》中的天使是被天国选中的灵魂,“它们可以摒弃语言,一个天使只需想着另一个天使,就可以把它召唤到身边。两个在人世间相爱过的人合为一个天使。”合二为一被爱只配,就构成了天国,而天使就成为了完美人类的形象;《神鱼阿卜杜和阿内特》中说到根据埃及人的神话,阿卜杜和阿内特是模样相同的两条神鱼,它们一直在太阳神拉的船前游弋,以提醒后者防备任何不测,“白天,船在天空航行,由东向西;晚上,船在地下航行,方向相反。”还有《双头蛇安菲斯比纳》中的“安菲斯比纳”就是“朝两个方向走”的意思,“据说是蚂蚁供养它。也有说把它切成两段,它自己会重新接起来。”两个相同的动物构成了完整的一个,这个完整就是“双面”所蕴含的完美。
但是还有一种叫做“分身”,《霍奇根》里说到了笛卡尔的说法,猴子本来会说话但是为了避免被人类强迫劳动于是保持了沉默,南非的布须曼人则认为动物都会说话,那个霍奇根的因为憎恨动物,有一天他把动物的说话能力都带走了;《女飞人尤娃吉》的故事来自《英国文学简史》中,森茨伯里认为尤娃吉是英国文学中最有意思的女主人公之一,“她一半是女人、一半是鸟,或者就像诗人勃朗宁:描写他的亡妻伊丽莎白·巴雷特那样,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鸟。”分身是将完整的一个一分为二,它造成的是剥夺,是占有,甚至是战争,《镜子中的动物》引用了中国黄帝的故事说,本来镜中世界和人间世界并不隔绝而是和睦相处,但是有一天镜中人侵入了人间,黄帝打败了镜中人,并把他们囚禁在镜子中,“黄帝剥夺了他们的力量和外形,把他们变成唯命是从的映象。”但是镜中世界并没有永远被囚禁,当法术消失之后它们终于醒来,“第一个醒来的将是鱼。”所有的东西都慢慢醒来,它们不再模仿人类,最终冲破了镜子的束缚,“水中的生物会跟它们并肩作战。”
从双面的完美到分身的战争,从合二为一的爱到一分为二的恨,“想象的动物”具有的意义当然超越了动物,对于人类来说它就变成了博尔赫斯的一个迷宫,“受到镜子、水面、孪生子的暗示或启发,许多民族都有分身这个概念。”它们就构成了毕达哥拉斯的“另一个自己”,柏拉图的“认识你自己”,在爱伦·坡的小说里,当主人公把良知杀死自己也死了,而在叶芝的诗歌里,分身是我们的对立面,“与我们是互补的,但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我们。”普鲁塔认为国王的代表就是“另一个我”……同一个也是另一个,而当《想象动物志》在完美的形式中变成新的开始,在阿宝阿库的登顶和滚落中不断开始,“博尔赫斯”是这一个,也一定是“另一个”。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8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