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09《论自由意志》:仍然要赞美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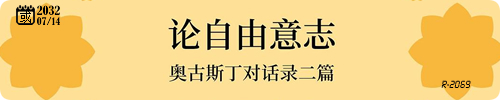
假使我能发现这原因,那么,难道我们还要去找这原因的原因吗?什么才是这探寻的极限呢?我们的问题和讨论到哪里才能停止?你所寻求的本不应超过这问题的根本。
埃伏第乌斯问奥古斯丁,上帝不是恶的原因吗?奥古斯丁做了回答;埃伏第乌斯问他,恶行是不是来自恶的学问?奥古斯丁对此进行了否定;埃伏第乌斯再问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是一种善吗?奥古斯丁也耐心进行了解答;埃伏第乌斯再问,恶是一直的一种运动,那么运动的原因是什么?意志是罪的原因,上帝难道不能预知吗?上帝的预知为什么要使人在意志面前有不同的选择?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奥古斯丁终于对埃伏第乌斯寻找“原因的原因”表达了某种不满:意志已经是罪的原因,为什么还要寻找意志本身的原因?埃伏第乌斯寻找原因的原因,也许是一种对知识无止境的探寻,但是在奥古斯丁看来,这已经陷入了无解的循环,“真不明白为什么你还想继续寻找。”
埃伏第乌斯是奥古斯丁的同乡,本来是政府大员的他反而比奥古斯丁先信了上帝,受洗之后辞去了职位,所以奥古斯丁和他常在一起,甚至在拿定神圣的主意后“要终身聚在一起”,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也讲到“你使一心一德的人住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两人在讨论自由意志时,在埃伏第乌斯提出不同问题时,在论及意志本身的原因时,为什么奥古斯丁“强制”让埃伏第乌斯停止对原因的原因的探寻?这种“强制”停止甚至也是对于问答这一方式的否定,那么奥古斯丁是不是在自由意志问题上走上了一条决然之路?是不是在说出了人类万恶之根上选择了对话的取消?那么,这是不是标志着奥古斯丁的论述走向了自我陈述?
《论自由意志》是奥古斯丁著作中不多的对话体文本,另一个对话录则是《独语录》,和《论自由意志》中最后对对话的取消不同,之前的《独语录》奥古斯丁甚至虚设了一个对话者:理性,“因为我们正在独自同我们自己说话,所以我选择了‘独语’这个名字,它肯定很新鲜,也许还很笨拙,但却颇为适当地指明了它的目的。”在奥古斯丁看来,自问自答的方式是对真理讨论的最好方式,因为如果有人在争论中失败了也不会觉得羞愧,也不会在发生观点冲突时带来伤害,“因为这些原因,我乐于依靠上帝的帮助,在平静和宜的气氛中,通过自问自答来探寻真理。”但是奥古斯丁也知道,形式上是问答式的对话,但是在理性和自己之间的自问自答“其实只有我自己”,所以它依然是“独语录”——奥古斯丁虚设了理性和自己进行问答探讨真理问题,但为什么又在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中和埃伏第乌斯取消了对话?
当然,奥古斯丁关于对话的不同方式也许不是对话体本身的缘故,他在《独语录》和《论自由意志》中所讨论的也是不同的问题,甚至这两部对话体也是奥古斯丁不同时期的著作。《独语录》写作于386年11月至次年1月之间,而386年正好是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的那一年,在此之前,结束了学业的奥古斯丁前后讲文法三年、讲修辞学八年,在雄辩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皈依基督教后,对于上帝的信仰当然也希望通过对话这一方式进行阐述,而这些阐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皈依之路的梳理。开篇第一句便是:“当很多事情在我心里翻腾,当一连好些天我孜孜探寻我的自我、我的善,以及那该摒弃的恶,总有一个声音突然对我说话——它是我自己,还是内在或外在于我的别的某物,我尚不知道,因为它正是我要力图发现的。”而《独语录》首先的做法就是在理性面前向上帝祷告:“宇宙的缔造者,我恰当地向你祈求的一切,请都賜予我;然后我要照那样行,使我配听你的话语;最后我还要乞求你予我自由。”这一切也都显示了初步跨入基督教门槛的奥古斯丁的虔诚。
但是,对于上帝的疑问也依然存在,所以他也必须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向自我和上帝敞开心怀进行“独语”,“看顾你的浪子吧,我恳求你,主啊,最仁慈的父,我已经被惩罚够了,我服侍你踩在脚下的仇敌已经够久,我作为欺骗的玩偶已经够久,在我逃离他们的时刻,请接纳你的仆人吧,当我逃离你时他们只把我当作陌路人。”奥古斯丁的祈祷其实围绕着上帝和灵魂这些问题,而对上帝的信仰就集中在信、望、爱上,“如果只是凭信仰,求救于你的人找到了你,赐予我信仰吧;如果是通过德行,赐予我德行吧;如果是靠知识,赐予我知识吧。请赐予我更多的信、望、爱吧。”他通过和理性的对话,以理性的名义建立起对上帝的信望爱——为什么他虚设的对话者是“理性”?因为奥古斯丁认为,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人拥有理性的灵魂,“我爱这理性灵魂”,甚至理性用在盗贼身上,“我可以爱每个人都拥有的理性,即便他利用它作恶时我正当地恨他。”——而这似乎也可以看做是几年后《论自由意志》的萌芽。
由此,通过理性奥古斯丁阐述了“上帝的知识”:首先是信,当心灵渴望除去肉体的污秽,它需要一双健康的眼睛以达到洁净,这就是“信”,“假如心灵不健康,被邪恶玷污,事物便不能向它显现(因为除非是健康的,它不能看见),而它也不会关注自己的健康,除非它相信否则便不能看见。”除了信还要“望”,“望”就是在相信中的希望,;第三则是必需的“爱”,信望爱是通向上帝的必由之路,“没有这三者,灵魂不能被治愈,它不能看见,也就是不能知道它的上帝。”而在这条道路上,“理性”具有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灵魂的凝视”,灵魂的凝视带来的是美德,而美德是正确的完满的理性,“即使有健康的双眼,凝视自身并不能使它们朝向光,除非这三者持存”——理性更为详细、形象地阐述了信望爱的凝视意义:
通过信,它相信被凝视的事物具有如此本性,被看见便引起幸福;通过望,它相信只要专心凝视就会看见;通过爱,它渴望看见和享有。说得详细一点,随凝视而至的正是上帝的形象,而上帝正是我们凝视的最终目的,不是因为到此凝视不再存在了,而是因为它顺着努力的方向无可进展了,理性达到它的目的,这是真正完善的美德,它带来的是有福的生命。
这是理性所设置的目标,也正是信望爱将奥古斯丁从以前对财富、荣誉和妻子的渴望中挣脱出来,继而走向了对上帝的皈依。但是奥古斯丁还需要一种对上帝的知识的“知道”,“上帝啊,你是永远的同一者,愿我知道我自己,愿我知道你。这就是我的祈祷。”他通过理性揭开了自己的困惑:理性问:“你知道你存在吗?”奥古斯丁说“知道”,理性又问:“你如何知道的?”奥古斯丁却说“不知道”,知道而不知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奥古斯丁要通过理性想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真理的问题,探讨真理如何知道上帝和灵魂,这也是奥古斯丁在哲学体系上的最早努力。真理问题就是要回答“什么是真?”按照理性的说法,“若所有事物因之而成真者,乃是由其自身、在其自身的真实真理,谁会觉得奇怪呢?”理性认为,人类灵魂之于学问就像东西之于主体,它是不朽的,而如果学问是真,那么真就会永远居留,灵魂就会持久永存,“如果它有死,我们就不叫它灵魂。”但是奥古斯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的死亡可能不会杀死灵魂,但是是不是会带来对真理的遗忘?
这一问题也是关于灵魂持久和真理永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理性让奥古斯丁“打起精神来”,“上帝会佑助我们探寻,而且在这肉身之后,他应许我们的乃是至福,且有丰富的真理,并得免所有欺骗。”但是《独语录》并没有在这条路上继续,按照奥古斯丁在427年对自己著作进行回顾的《订正》所说,《独语录》是“未完成的”,尤其是在第二卷开始讨论灵魂的不朽性问题后并没有继续讨论如何得到上帝的佑助,“但是还不完备。”仿佛一开始奥古斯丁所说的“很多事情在我心里翻腾”,在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中,依然在翻腾,依然无法走向宁静之地——而仿佛多年后的《论自由意志》在讨论上帝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上变成了一个“续篇”。
| 编号:B55·2250113·2226 |
“请告诉我:难道上帝不是恶的原因吗?”埃伏第乌斯是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中的对话者,他不再是虚设的对话者,而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埃伏第乌斯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犀利的,甚至面向的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诸多争论。埃伏第乌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恶的原因:人会作恶,而人是上帝的受造者,那么上帝是不是恶的原因?对于这个问题,奥古斯丁反问他是哪种恶:一种是作恶的恶,另一种则是遭受恶的恶?奥古斯丁认为,这两种恶当然不同,上帝不作恶,所以要说恶是上帝的原因只能是第二种恶,也就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而让人遭受的恶,但是这种恶是上帝为了惩罚恶事,所以它是公义的。但是埃伏第乌斯却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延伸的问题,恶在第一种意义上是行恶,当人行恶就是人学会了做恶事,那么是不是人首先要学会做恶事?奥古斯丁回答说,恶不是学问,而且恶是背离了学问,奥古斯丁也知道埃伏第乌斯之所以要提出恶和学问的关系,正是指向了上帝,或者说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的另外说法:不是上帝教给了我们恶的学问而让我们行恶吗?奥古斯丁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将使我们理解我们所信的,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正处在先知所描述的境地,‘除非相信,你们不能理解’。”
这也是在《独语录》中理性所说的“信”,要相信一切的事物都是从上帝而来,也要相信上帝不是罪的原因:“上帝是全能的,而且在最小的方面都是不可变的;他是一切好事物的创造者,但他自己比所有这些事物更完善;他是他所造万物的至上公义的主宰;他不借助任何存在进行创造(好像他自己没有充分的权能似的),而是从无中创造万有。”奥古斯丁接着阐述了上帝的权能、全善和全知,他认为上帝的律法是永恒的律法,“根据它万物得以完美地安排”,这就是公义,而人所追求这种完美,就需要理性,理性指向的是智慧,是秩序,“当理性、心灵,或灵控制着灵魂非理性的冲动,人就正是由那应该进行掌管的东西,依据我们已发现为永恒的法律掌管着。”在这里,奥古斯丁将这种理性的看做是一种意愿的能力,当意愿追求公义、智慧、真理,那么这种意愿所体现的就是善良意志。但是在永恒的律法之外,还存在着“属世的”律法,它是暂时的,它追求的是属世之物,而这些属世之物是靠肉体知觉的,是“人之最少价值的部分,且永远不会是确实的”——或者奥古斯丁直接将恶事的产生,即罪恶归于此类:恶行就是忽视了永恒之物,就是靠自身而知觉享有的。
区别了永恒的律法和属世的律法,奥古斯丁也就区分了善和罪,“我想那些因热爱永恒事物而幸福的人,生活在永恒的法律之下,而那些不幸的人则服从于属世的法律。”实际上也就出了意志的自由选择问题:选择永恒还是属世?对于这个阐述,埃伏第乌斯又提出了问题,或者又让对话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上帝是人类的造物主,那么一定是他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上帝还是我们行恶的原因。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确给了人自由意志,上帝给人类自由意志是为了“行正当”,自由意志对于人类来说,也是为了行正当,“人不可能无自由意志而正当地生活,这是上帝之所以赐予它的充分理由。”而且人自己借自由意志而犯罪,也是“正当”地体现,因为犯罪了就会被惩罚,惩罚是为了公义,所以它也是正当的。再次,奥古斯丁进行了关于正当性的论证:“假若人类没有意志的自由选择,我们如此渴慕的在上帝之正义中的善,即他之惩恶扬善,怎么可能存在呢?如果我们行事不靠意志,那就无所谓罪恶或善事了,而如果人类没有自由意志,奖惩就都会是不义的了。但是奖惩之中恰恰有正义,既然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善。因此,上帝赐予人自由意志是正当的。”
而人类运用自由意志,在奥古斯丁看来需要一种理性心灵,只有在理性之下,人类的自由意志才能行善事,但是那些人靠着自由意志为什么会行恶事呢?奥古斯丁在这里把善分成了三大等级,第一类是大善,人借着正当生活的德行就是大善;其次就是中等之善,中等之善是灵魂具有正当生活的能力;还有最低之善,上帝之所以创造了不同的善,体现的就是他的仁慈、慷慨和丰富,“更让他的仁慈值得赞美”——为什么善会有等级?为什么即使创造了会被错用的中等之善和最低之善,上帝仍然需要被赞美?这其实就是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的全部预设。他认为,自由意志就是一种中等之善,之所以是中等之善,就在于它不是不会错用的大善,就在于它会带来恶行:当意志忠于公共、不变的善,那么他就会得到属人最大、最重要的善;但是,意志如果转回它自己的私善,那么它就犯罪了,“它想作自己的主,便会转向自己的私善;热衷于别人的事或与己无关的事,便会转向外物;以身体快乐为乐,便会转向低下的事。”
所以,自由意志本身是中等之善,但是当自由意志为了私善而行事,那么就变成了一种罪,为什么自由意志既是善又是罪?奥古斯丁认为这不是一种悖论,自由意志就是一种善,当它转向私善的时候,变成了罪,这不是自由意志本身的原因,而是自由意志“运动”的原因,他不来自上帝,而来自自由意志本身。在这里埃伏第乌斯就问奥古斯丁,这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奥古斯丁说,意志的这种运动属于意志本身,它是灵魂志愿产生的。埃伏第乌斯又进而问道:既然上帝预知一切未来之事,他也一定知道人类凭借自由意志犯罪,那么,上帝预知人类犯罪,这就是一种必然,而在这种必然之中,人类的意志还是自由选择的吗?奥古斯丁回答说,上帝预知任何事情都必然发生,但是不是因人类的意志而发生,因为人类的自由意志来自于人类的权能,一方面,在人类的权能之下意志就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他的预知并不取消我的权能,实际上使我有权能这一点更为确实,因他预知我会有,而他的预知永不会错。”所以上帝的预知的必然性和意志的自由不存在矛盾。
埃伏第乌斯有继续问道:“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上帝预知不会犯罪的本性不犯罪,而上帝预知会犯罪的本性则犯罪。我再不认为是上帝的预知本身迫使一个人犯罪,另一个不犯罪。但如果没有原因,理性造物就不会分为永不犯罪的、怙恶不悛的,以及有时犯罪有时行正当的。”也就是说,同样是人类,同样拥有自由意志,为什么有人犯罪有人不犯罪,这些难道上帝不会预知吗?也就是在这里,奥古斯丁把意志看成是一切罪的根本原因,但这是意志本身造成的,但是埃伏第乌斯想要知道意志本身的原因,奥古斯丁便只好拒绝了回答,终止了追问,“请你相信这教训的不可逾越的真理:贪婪是万恶之根。”在这句话被讲出之前,是埃伏第乌斯的关于三种意志的原因问题,但是从这里开始,埃伏第乌斯再没有发声,当奥古斯丁终止了对原因的原因的探寻,也取消了对话,他终于将一切变成了自我阐述。
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是为了行正当,但是人却利用自由意志为私善,这就是自由意志的滥用,这是意志自身引起的恶,和上帝无关,但是当人滥用自由意志有了罪行,上帝必然要对他进行惩罚——人类第一次犯下的罪就变成了原罪,而上帝的惩罚是为了拯救,是为了医治,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它是白白赐予的,“上帝创造不爱他的灵魂,完善发他的灵魂;赋不存在的以存在,赐爱他的以有福。”之所以有上帝的恩典,就在于创造秩序,因为,人不论选择善还是恶,都是参与了受造的秩序,也正因为这是永恒的秩序,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便是:赞美上帝。埃伏第乌斯早就没有了声音,而奥古斯丁走向最后终结的时候,却又对“你”说:“我已经按照主许我的,尽可能回答了你的问题,不知是否遗漏了什么。不过,即使你又想到什么了,这卷的篇幅也迫使我们就此结束讨论,休息一会儿。”
“你”也许是已经不发声的埃伏第乌斯,也许是每一个对自由意志感到困惑的人——埃伏第乌斯的几个问题其实真正切中了自由意志的关键:如果自由意志会作恶,上帝为什么要给人类这样的能力?如果人类没有自由意志岂不是更加完美?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却在伊甸园里滥用了人类意志从此有了原罪,那么如果伊甸园里人类始祖永远不滥用自由意志,还会有真正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延续下去?如果上帝给了人类自由意志,又规定必然行正当,滥用了自由意志也必须接受惩罚接受上帝的恩典,诸多的必然性是不是反而架空了自由意识?而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是不是在预设了恩典论之后提出来的:只有对上帝的恩典才能证明人类的原罪,而他人类的原罪又证明了自由意志的滥用——从结果制造原因,从而回到上帝的公义,回到对上帝的赞美,“那么我说,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从公正地加给罪人的痛苦中得自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