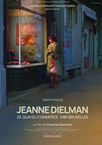2025-04-07《让娜 ·迪尔曼》:杀人者的沉默独白

坐着,就这样坐着,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外面的光影投射在背后柜子的玻璃上上,光洁的桌面反射着光线,在光影变化中让娜·迪尔曼保持着唯一的坐姿:她的手搁在桌子上,手上沾着血迹,微微低下头,或者头歪向一边,接着又抬起来,在隐约的光线中,脸上似乎显出了某种微笑的表情……这是最后的场景,几分钟的长镜头之后便是字幕,便是结束,当关于一个中年寡妇的三天故事以纪实的方式落下帷幕,似乎对于观众来说闪现出几个疑问:她为什么会面露诡异的微笑?她为什么不逃避而在等待什么?当儿子西尔万按响门铃她如何对他讲述发生的事?而这几个问题都归于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她会以猝不及防的方式用剪刀刺死了嫖客?
可以说这是一种爆发,接客完成之后,她坐在镜子前然后穿上了衣服,之后走出了镜头,但是突然闯入了镜头——只不过是在镜子里,她用刚才拆开从加拿大寄来的包裹的剪刀刺向了正坐在床上的男人,男人没有喊叫甚至没有挣扎便一命呜呼。杀人干脆利落,这是让娜·迪尔曼爆发之后的力量所致,但是无论是爆发时的杀人还是坐在那里的寂静,都归于一种沉默,沉默是命运落幕的一种状态,也是导演香特尔·阿克曼拒绝提供答案的态度:她似乎很自然地结束了这场谋杀和三天的生活,她似乎不想呈现“接下来”发生的事,她似乎要将让娜·迪尔曼的故事搁置在这永远的沉默之中——沉默不正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常态?沉默不正是她面对命运的回击态度?沉默不正是一个杀人者的独白方式?
电影片名其实是《让娜·迪尔曼,布鲁塞尔1080商业街23号》,一个女人的名字,一个女人生活世界的门牌地址,当香特尔·阿克曼用201分钟的时长记录三天的生活,“漫长”就变成了一种没有真正出口的生活,固定的地址、固定的时间,和固定名字的女人构成了一种封闭状态,当然还有固定的镜头——香特尔·阿克曼几乎就是以固定长镜头记录了一个女人三天的生活,从厨房到卫生间,从客厅到卧室,从通道到外面的电梯,除了在厨房和客厅有变化的机位之外,基本上就是以最简单的固定机位进行最简单的记录。“固定”成为解读让娜·迪尔曼生活的一个关键词,在这三天中,她的生活几乎就是在这种固定状态中打开和合拢的:一早醒来,穿好衣服,打开窗户,然后在儿子睡觉的客厅里点起暖气;准备好儿子要穿的衣服之后,来到厨房,磨好咖啡,就给儿子的皮鞋认真擦拭;泡好咖啡,叫醒儿子,在儿子吃好早饭之后,为上中学的儿子送行;回来将儿子的床重新变成沙发,然后在厨房洗碗,收拾好自己的房间之后从罐子里拿钱出门;去邮局发电报、拿着坏掉的鞋去修理、去商店买东西,然后回家;在账单上记号账,给邻居照看一下孩子,然后再出门;去固定的咖啡店喝一杯咖啡,买一些给儿子编织毛衣的毛线,然后再回家;门铃响起,开门,和男人一起进入房间,关好门;门打开,送走男人,男人拿出钱给她,“下周再见”或者“周四见”;然后开始准备晚餐,等儿子回来之后两个人吃晚餐,接着打开收音机,为儿子编织毛衣;两个人出门散一会儿步,回家,儿子入睡,自己也结束了一天。
从醒来到入睡,从早晨到晚上,从出门到回家,让娜·迪尔曼的生活就在这样固定的节奏中进行,甚至这样的固定节奏变成了一种重复:几乎每天都是一样的步骤,几乎每天都是相同的状态,甚至都会在餐桌上对儿子说“不能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但是香特尔·阿克曼将一个女人的生活浓缩在看起来固定不变的三天时,恰好是在三天的生活中寻找一种变化,或者说从这个封闭的世界里发现潜伏着的可能。“第一天结束”“第二天结束”,这是香特尔·阿克曼故意标注的时间,而实际上,这并不是完整的三天,因为故事是从第一天下午开始的:在厨房间开始煮东西,然后脱下外套整理衣服,门铃响起,和外面进来的男人打招呼,然后带他进入自己的房间,关门和开门之后送走了男人,之后则是儿子回家,两人共进晚餐、一起散步,直到最后入睡。从第一天的下午开启让娜·迪尔曼的故事,那么这个半天的生活便是局部的呈现;而第二天完整记录让娜·迪尔曼的生活,则是一种还原;当第三天的最后让娜·迪尔曼用剪刀刺死了男人,则意味着破坏。
| 导演: 香特尔·阿克曼 |
局部的第一天,完整的第二天和破坏的第三天,这就是香特尔·阿克曼记录三天的意义所在,而从局部到完整再到破坏,这本身就构建了一种对固定规律的解构,它以杀人为极端展现方式结束了一成不变的状态,而回过头来,第一天的局部和第二天的完整,正是为第三天的破坏设下伏笔,为最后的爆发创造条件。第一天从下午开始,就直接从厨房的劳作变成了“接客”的过程,但是在男人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很客气地打招呼的方式以为进来的是让娜·迪尔曼的丈夫;当他们进去关门,之后又开门出来,让娜·迪尔曼给他外套和礼貌,男人给他钱并说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当然这个男人一定不是丈夫,也许是朋友,或者熟人,或者同事,或者亲人——无论如何,在一种礼貌的问候中,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嫖客,而这正是让娜·迪尔曼生活被“装饰”的部分。在第二天完整生活的展示中,下午还是开门迎来了男人,还是在开门关门、关门和开门中完成了叙事,只是男人并不是前一天同一个男人,约好的时间也不是同一个时间,故事就慢慢切开了口子:让娜·迪尔曼在送走男人之后,将那块小的床单扔进了卫生间的篮子里,然后洗了澡——从开门迎来男人,到送走男人之后收拾、整理以及洗干净身体,这已经预示了和她应有的生活形成了不同的面向。而当第三天继续开门迎来男人,带着男人进入房间,香特尔·阿克曼却以完全不同的开放方式让观众进入到了“内部”:在床上,男人压着让娜·迪尔曼,让娜·迪尔曼现出难过的表情,她想推开男人,她想离开床铺,或者无能为力,或者说服自己,最终在痛苦中完成了,而痛苦的代价则是最后的爆发,用剪刀刺死嫖客,既把让娜·迪尔曼隐藏的身份完全揭露出来,其实也在这种爆发中推向了命运的未知。
三天,是从局部展示到完整呈现再到破坏和爆发的三天,它是一个渐进式酝酿的过程,除了男人的身份从误解到隐秘再到揭秘,让娜·迪尔曼看起来固定不变的生活也出现了很多细小的变化:第二天当送走了男人,让娜·迪尔曼在厨房煮东西时发现有什么不对,她把锅子里的东西都倒掉了,然后打开了厨房的窗户,又出门去买土豆,儿子回来之后她便解释说自己把土豆煮过头了,而西尔万则发现母亲的头发乱了,他也提醒了她;吃好饭,让娜·迪尔曼开始编织毛衣,儿子问她:“今天不开收音机吗?”让娜·迪尔曼便起身打开了收音机;想给加拿大的婶婶写信,但是不知道写什么,一张信纸又被揉成了团……这些细小的变化在第三天更加明显:早上西尔万在用早餐的时候,提醒母亲“纽扣开了”;西尔万出门,让娜·迪尔曼开窗似乎提醒他什么;在厨房间擦拭刀叉的时候勺子不小心掉了,喝咖啡又感觉味道不对,重新磨制了咖啡豆,又将牛奶喝咖啡混合在一起,却始终觉得味道不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似乎有些手足无措,接着第一次拿起抹布擦拭柜子里陈列的物品;出门去咖啡馆,吉赛尔不在,要了一杯咖啡旁边却坐着一个抽着烟的女人;回来走到门口发现从加拿大寄来的礼物到了,于是拿到房间里用剪刀拆开了包裹,是一件漂亮的裙子……
从第一天的局部,到第二天完整呈现中出现的细微变化,再到第三天这种细微变化又以莫名的方式影响了让娜·迪尔曼的情绪,似乎最后的爆发就变得顺理成章。但是从重复到变化,香特尔·阿克曼用客观记录的方式讲述三天的故事,更在于一步步揭开让娜·迪尔曼作为一个女人的命运,三天所对应的其实是她作为女人的三重身份:第一天在和儿子吃完晚餐之后讲起了加拿大婶婶寄来的信,让娜·迪尔曼便读了这份信,这份信其实就交代了让娜·迪尔曼的生活,她的丈夫乔治六年前就去世了,这六年来她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婶婶费尔南德斯在信中问她,是不是会考虑再婚?在西尔万即将睡觉的时候,他问母亲和父亲的故事,让娜·迪尔曼说起他们是在美军撤离之后相识的,自己父母去世了,和婶婶生活在一起,后来就和乔治结了婚,“我不太喜欢结婚,我想拥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很明显,当婶婶问她是否考虑再婚,让娜·迪尔曼其实已经做了否定的回答,甚至在西尔万提到父亲很丑,“他那么丑,你会和他做爱吗?”让娜·迪尔曼的回答是:“丑不丑并不重要,做爱只是次要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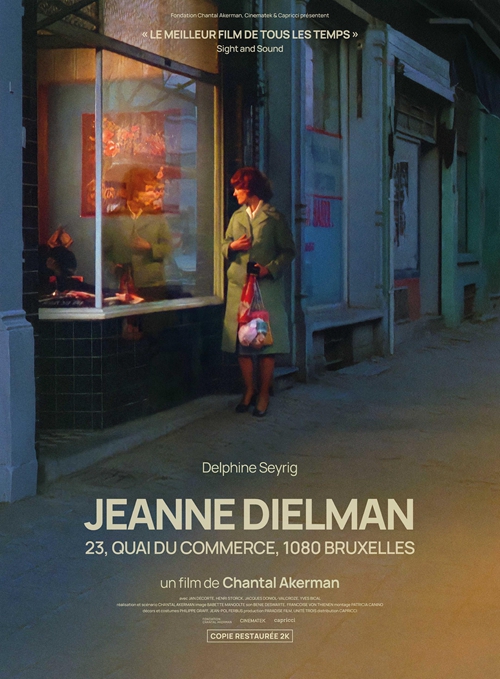
《让娜·迪尔曼》电影海报
交代了让娜·迪尔曼的过去,这些过去和她作为妻子的身份相关,但是在自己不适喜欢结婚的态度、丈夫六年前去世的现实,都折射出妻子这一身份是缺席的;而第二天的生活以完整的方式被呈现,这种完整其实是身为母亲生活的完整:给儿子做早餐,为儿子擦拭皮鞋,给儿子每天的生活费,出门和儿子的吻别,以及晚上等儿子回来一起用餐、散步等等,都展现了一个维持家庭生活的母亲形象;但是在第二天入睡的时候,母子的对话又凸显了另一种缺席,西尔万说起自己的同学杨喜欢上了护士,杨把男人的性器形容为“一把剑”,“越深入越痛快”,让娜·迪尔曼对此的态度是:“这有什么意义?”然后西尔万回忆起了小时候父亲对他说起的那些事,“我恨他了好几个月,甚至想死,后来他死了,我觉得那是上帝对他的惩罚,现在我也不信上帝了。”父亲对儿子说起了男女之事,就像杨说起一把剑的痛快,但是西尔万却因此恨父亲,还希望上帝对他惩罚,更为关键的是,他成为了父母性生活的秘密破坏者,“后来我假装喊你,这样爸爸就无法刺入你的身体了。”西尔万对性的排斥,对父母性生活的破坏,看起来是隐秘的保护,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母子的畸形关系。
第一天让娜·迪尔曼被还原的身份是妻子,第二天她的身份则主要表现为母亲,那么第三天则变成了妓女,当开门进来的男人身份被揭秘,让娜·迪尔曼的身份也走向了最后一种,而妻子的缺失、母亲的畸形,也从另一个意义上完成了对“妓女”合理性的定义,当让娜·迪尔曼不喜欢结婚成为妻子,让西尔万不让父亲的剑刺入母亲的身体,那么,解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而成为妓女,是不是就是让娜·迪尔曼的一种真实写照?但是让娜·迪尔曼为什么要成为妓女?妓女出卖肉体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有收入,男人交给她钱,钱被放进罐子,第二天又拿出来给儿子作为零用钱,或者生活的各种开销,也就是说,让娜·迪尔曼用身体赚钱是为了维持失去丈夫的日常开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带电梯公寓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没有其他收入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在三天生活的记录中,让娜·迪尔曼最常见的一个动作便是随手开关电灯,开电灯是为了照亮,那么及时关电灯是不是意味着开源节流?
在开源节流之外,随手关灯似乎更体现一个女人对秩序的遵从,而这也是的这三天的生活呈现出另一个维度的意义:第一天所展示的是不变,第二天则是一种变的开始,一直到第三天爆发后的杀人,这是变走向的极端,但是这个违背了道德、突破了法律底线的变却又是一种不变:还是在这开门关门的空间里,还是在这不断重复的生活里,还是在这布鲁塞尔1080商业街23号的家中,还是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机位演绎的现实里,变是不变之变,更是变之不变。但是当1975年只有25岁的香尔特·阿克曼聚焦一个女人的三天,探讨局部、完整和破坏的生活,展现妻子、母亲和妓女的现实,呈现变之不变和不变之变的转折,其实是将真正囚禁她的一切看成是“仇敌”,它们是一扇扇开启必须关上的门,是被一道一道铁栏围起来的电梯,更是约束女人的社会规则,是带着剑压在身上的男人,让娜·迪尔曼用沉默的独白讲述了一个女人被“仇敌”囿于三天封闭世界的生活,就像他和西尔万朗读的那首波德莱尔的诗歌《仇敌》:
我的青春是黑暗的暴风雨
耀眼的光闪现;
雷电和暴雨浸漫大地
红色的果实还留在我的花园
我求助铁锹和铁耙
重新翻耕大水淹没的土地
它冲击的深坑犹如墓穴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