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17《心灵与形式》:它是生活的最高法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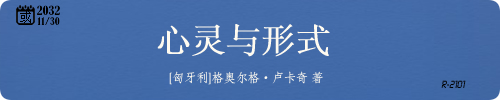
克尔凯郭尔的英雄主义就在于:他希望从生活中创造出形式。他的真诚就在于:他看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并走到了他所选择的道路的尽头。他的悲剧就是:他想要体验不可能体验的生活。
——《生活中被撞碎的形式》
1840年9月,克尔凯郭尔与国务顾问的女儿蕾金娜·奥尔森订婚,婚约履行无疑指向了婚姻的必然性,但是仅仅一年后,克尔凯郭尔就解除了婚姻并前往柏林,婚姻在他身后,未婚妻在他身后,必然性在他身后。为什么已经订婚的克尔凯郭尔会反悔?他从来没有爱过奥尔森,这是一种否定的必然性,但是他却宣示了某种信心,“没有哪一个已婚男人对妻子的忠诚能超过我对蕾金娜的忠诚。”宣示这一信心,克尔凯郭尔无疑也是真诚的,而且他的真诚就在于通过一种“决断的义务”让自己活在自己的原则下,按照卡塞纳尔的解释,克尔凯郭尔的信心和忠诚不是为了掩盖真相,“而在于揭示它。”
克尔凯郭尔所要揭示的真相是什么?是爱的本质?是决断的义务?“克尔凯郭尔哲学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他在生活之不间断地摇摆的过道的下方设定了几个固足的支点,并在细微差别的融化着的混沌中得出了绝对的质的区别。”在卢卡奇看来,克尔凯郭尔超越了大部分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彼此截然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了明确地、深刻地界限,“在细微差别的融化着的混沌中得出了绝对的质的区别”,这或者也是克尔凯郭尔的敏感之处,但是这在另一个意义上则形成了一种真诚的悖谬:那些先前存在差别的东西,当被遮掩而尚未成长为新的统一体的时候,必定保持着永远的“被分离”。在克尔凯郭尔与奥尔森的婚约中,他所害怕的也许就是幸福的不可得,因为幸福就是一种可能成为新的统一体,永远被分离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就成了他的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是不是解构的是那个具体的、真实的个体?
“爱是我所唯一擅长的事情。”当克尔凯郭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想要那种具有唯一性而没有任何问题的爱,已经不是真实个体纯粹主观的感受,而是趋向于上帝的保证。从现实生活到伦理生活,再到宗教生活,克尔凯郭尔的确是在个体意义上谈论的,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个体的和具体之物的生活,主观性具有一种真理性,但是,婚姻具有的伦理性只能在纯粹的诗世界和信仰世界之间,诗人生活是可能的,伦理世界是安稳的,宗教世界则是绝对的,所以他会解除婚约而走向上帝的绝对信仰,“抛弃蕾金娜,这也仅仅是克尔凯郭尔追寻自己梦寐以求、永不可及的目标过程中的一步,不过,这一步是他登顶的最可靠的一步。”但是这样的真诚难道不正是基于个体的一种英雄主义?所谓的“决断的义务”不正是带来个体的烦恼和悲剧?卢卡奇把克尔凯郭尔的英雄主义看做是一种创造形式的努力:想要要在选择中保持真诚,想要在不可能中体验生活,但是这所有的努力却并没有真正创造形式,最后,“死亡追赶上了他”,“克尔凯郭尔的死就获得了一千种的意义,充满偶然性,而没有实际的宿命性质。”
卢卡奇把克尔凯郭尔的英雄主义看作是一种“姿态”,即使他最后的徒劳的努力也依旧不是最终的姿态,这里就有了一种区别,渴望创造形式却变成了一种姿态,克尔凯郭尔的姿态和卢卡奇所说的形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姿态或者说克尔凯郭尔的姿态就是“对一种并不含混的事物的运动的清晰表达”,无论是解除婚约也好,还是唯一擅长的爱,克尔凯郭尔都在构建一种姿态,姿态是完整的事物,是唯一的现实,是非常纯粹的可能性,甚至姿态不假外物就可以表达生活,但是正是因为姿态只是对现实可能性的努力,所以表达生活变成了生活的艺术,甚至用“心灵之非实在的可能性去伪造现实”,那么姿态就变成了生活的佯谬,“他的每一篇作品、他的每一次抗争与历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那个姿态的背景”,而在卢卡奇看来,生活只有在它的必然性之中每一个瞬间才有自己的依稀之地,“也只有在它之中,每一个这样的瞬间才变成了真实的现实。”
姿态是纯粹的可能性,形式才是表达生活之绝对者的唯一方式,姿态和形式的区别或者是诗歌和生活、可能性和绝对者之间的不同,所以他把克尔凯郭尔和奥尔森之间的故事看作是“生活中被撞碎的形式”——一种英雄主义在个体的样本分析中反而具有了一种必然性的形式。那么当生活不被克尔凯郭尔的英雄主义撞碎,该有怎样的形式?在致列奥·普波的《论说文的本质和形式》中,卢卡奇通过对论说文这一体裁表达了对“形式”的界定。论说文的标准当然是写得好,但是它不是文学作品,不是艺术品,更不是一种科学形式之呈现,而是不需要中介“直接地对生活发问”,也就是说,论说文就是一种直接面对生活的形式,它指向的是生活这样一种心灵现实,它将表象和意义的二元结构在分离中重新照亮,所以形式并不是和所谓的本质完全分离的存在,形式就是命运,形式还创造了命运,“这个形式,从生活象征的一个象征沉思中诞生,借助这个体验的力量得到了它自己的生命。”
| 编号:H48·2250306·2260 |
所以形式在卢卡奇那里具有了现实性、创造性、直接性,而论说文这种形式的表现方式就是柏拉图的对话、蒙田的随笔、克尔凯郭尔的小说和散文——不是克尔凯郭尔充满英雄主义“决断的义务”,“论说文是一种艺术形式,是对自己的完整的生活进行独有的无保留的塑造活动。”卡塞纳尔评价克尔凯郭尔时认为他的忠诚和信息是为了揭示真相,这一评价本身就是和克尔凯郭尔的英雄主义姿态不同的一种形式,而在卢卡奇看来,卡塞纳尔作为一个艺术家正是实践着形式具有对心灵生活的创造性意义。他区别了创造型诗人和柏拉图主义者,一个用韵文写作,一个用散文写作,一个在坚固而安全的工事里,一个在漩涡和危险中,一个展开翅膀一飞冲天,一个则不断贴近事物,一个永远是悲剧性人物,一个则在相信和怀疑中远离悲剧,卡塞纳尔就是将两者联合起来“创造出优势来”,这种联合不是机械式的,而是在卢卡奇看来是一种正反之后的合题,这个合题就成为了具有创造性的形式,“只有假道于形式,才能从每个反题中、从每个趋同中生成音乐和必然性。”艺术家就是在形式中诗人和柏拉图主义者的“一人两名”,也只有这个反题式的形式,“才能在柏拉图主义者沉重的蹒跚步履与诗人轻灵的失去分量的羽箭飞翔之间创造出一种平衡;通过艺术家的形式,从诗艺中产生柏拉图主义者永恒期盼(对确定性和对信条的期盼)的持久隐匿的主题,柏拉图主义者将生命的多色调载入了诗人齐声一致的圣歌之中。”
也许在这个卢卡奇推崇的平衡之中,诺瓦利斯也提供了一种失去形式反题的证明,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表现出了最纯粹的泛诗主义:一切是诗,诗是“一和一切”,连同道德在根本上就是诗,而诺瓦利斯这个体弱多病的诗人也把自己变成了追求终极目标和绝对意义的诗,当然,死亡无疑也是他一生最后的诗,“他的危险是死亡。他自己的死亡和与他心灵最为亲近的人的死亡。”所以卢卡奇认为诺瓦利斯是浪漫主义中唯一真正的诗人,唯一将精神化作了诗的人,而其余的人,只能称作“浪漫主义诗人”。对诺瓦利斯评价如此之高,也只是在卡塞纳尔所说的一种人身上,或者说只是他创造型合题的单一部分,“尽管如此,他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回答:他向生活提出疑问,死亡给了他答案。”或者在另一个意义上,诺瓦利斯的浪漫主义也是一种在死亡中收获了答案的英雄主义,也是被生活撞碎了的形式。
形式对心灵、生活的揭示体现了它的现实性、创造性和直接性,在论泰奥多·施笃姆的《市民阶级的生话方式和为艺术而艺术》中,卢卡奇分析了德国市民阶级的生活方式,文学和艺术如何寻找到它如光线照进心灵和现实的形式?“它在生活形式与典型的生活体验两者神秘的交互作用之下,深入地渗透进了一切创造性的活动中去。”施笃姆作为德国审美者中最纯粹、最真实的艺术家,用一种融合的方式创造了形式,这就是“神圣的日常的诗学”,它表现为悲剧和田园诗:一种表现为生活在其一切外部的绝对不安全感,另一种则只关涉了灵魂之处不可动摇的稳固性,只有将两者结合才具有市民本质的深度,“产生不安全感是市民阶级的生命情绪所致;在如此的生命情绪下,正在消失中的老旧而庞大的市民性在其最后的、内在的、未被压垮的诗人作品里变得具有了历史性和深刻的诗性。”而施笃姆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创造了融合的形式,“在施笃姆的世界里,一个人的灵魂里充满矛盾的各种强力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争斗。”
施笃姆的争斗、施蒂芬·格奥尔格的冷峻,夏尔-路易·菲利普的“眷望”,都构成了卢卡奇所阐述的“形式”,而在“关于劳伦斯·斯特恩的一场对话”中,卢卡奇创造性地通过戏剧评价了斯特恩“生活的富矿、混沌和形式”,无疑这篇文章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形式:现代语文学专业的文岑茨正热恋着一位少女,他们在一起阅读,此时敲门声响起,另一位同学约阿希姆到访,于是三个人尤其是都暗恋着少女的文岑茨和约阿希姆展开了对斯特恩的争论。约阿希姆认为斯特恩无论是《项狄传》还是《感伤的旅行》,都是“一锅乱炖的杂碎”,“您的这位作者把感情依原样写进书里,完全是粗糙的、未经加工的原材料,而根本没有努力地把它们统一起来并赋予它们以形式,哪怕是非常廉价的形式!”在他看来,斯特恩就像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就是无序,无序就是死亡,“因此我反感无序,以生活的名义与无序抗争,以生活的富矿的名义与之抗争。”但是文岑茨讽刺他所谓的富矿只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理想国,斯特恩才是拥有无法夺去的一切:丰沛、充实、生活,他深入到人性的观察中,不用所谓合乎逻辑的方式捕捉,却洞察到了生活的问题、现实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这种“无限的旋律”就是真正的形式,“形式是一切等待被言说的东西的浓缩的实质,我们感受得更多的只是浓缩后的东西,而几乎不知道它是由什么浓缩而成的。”而且形式体现了心灵强大的包含力量,混沌和秩序、生活与抽象、人和人的命运、情绪和伦理,最终形成一体,而这就是世界的总体性。在文岑茨的咄咄逼问下,约阿希姆只能无奈离开,而文岑茨也获得了热恋少女的热吻,这一场争论式对话也完成了赋形的意义。
“只有当它们共在的时候,只有当它们每时每刻都在长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生生的统一体的时候,人才是真正的人,他的作品才是真实的总体性,才是世界的象征。”通过文岑茨的阐述,卢卡奇界定了形式的重要意义,“形式是最后的、以最大力量进行体验的感情向着自足意义的升华。”但是这场讨论中所提及的无政府主义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当时还没有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直面现实的一种“姿态”,所以关于形式问题实际上已经转向了社会学意义,在论保尔·恩斯特的《悲剧的形而上学》中,卢卡奇在阐述了恩斯特的悲剧时,对于形式有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当生活成为光明与黑暗的交织,它呈现的是无序混乱,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得以全部完成的,没有什么是真正走到结束的,这个未完成、持续的过程并不是表现为一个大杂烩,而是指向了心灵的现实:生命和活着,它们构成的就是生活,让生活成为其所是而具有现实性、创造性和直接性的形式,也不只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之上,而是变成了一种伦理学,“形式是生活的最高法官,赋形的能力就是一种裁决的力量,一种伦理。”
伦理学就是被赋形的生活,就是在形式中包含了价值判断,就是不再在英雄主义、泛诗主义中仅仅成为一种姿态,就是在直面命运中揭示心灵现实,“每一种赋形,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是生活可能性等级秩序里的一级:一旦决定了采取何种形式来表达一个人的生命显现,何种形式是他的生命最高时刻所必需,那么关于他及其命运的决定一切的语词就能够被说出来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