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30《失窃的孩子》:“记得”的童年间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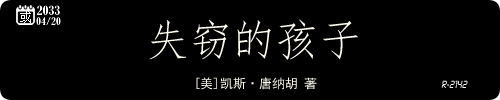
在奋斗多年《寻找失窃的孩子》的音乐后,我终于完成了。
——《16》
孩子,是《失窃的孩子》中的人类孩子,是《寻找失窃的孩子》中的换灵生,他们是不同的孩子,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完成自我的不同定义,这正如音乐中的间奏曲,以一种对位法演绎着关于生命的节奏,当凯斯·唐纳胡用音乐创作完成这个故事的讲述,它自然在“同时叙述”中构建起了内在的世界和外在的世界,实现了“一体两面”的人生解读。但是正如《寻找失窃的孩子》的乐谱,是对《失窃的孩子》的一种回应,“失窃的孩子”是事件的起因的话,那么“寻找失窃的孩子”是不是变成了对这种时间后果的某种解救?
“失窃”是一次事故,“寻找”是一种努力,因为寻找正是对“失窃的孩子”的寻找,那么,这个一体两面的对位法故事是不是有一个世界是主动的,而另一个世界则是被动的?的确,从变成人类的换生灵开始讲述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把时间回溯到了发生的起点,而换生灵也变成对位法中的主动者:“三十年前,我就从一个换生灵重新变成了人类。”在那个名叫亨利·戴七岁的时候,由于他离家出走躲在了栗树的树洞里,于是在森林里的换灵生抓住了他,然后让其中一个人溜进树洞交换了生活,由此两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换生灵变成了亨利·戴,成为了家族成员,开始了人类生活,而曾经的亨利·戴在昏迷醒来之后,就变成了安尼戴,成为了森林中和其他换生灵在一起的非人类。
换生灵成为了人类,人类变成了换生灵,看起来他们都变换了原来的身份,进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是一种平等的互换,但是成为人类的换生灵就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且在换生灵说起事情的起因时也介绍了换生灵这种独特存在:从词源学上看,这是一种“仙灵”,是和水泉女神或水仙女有关的生物,仙灵这个词来自古老的法语,而古老法语又起源于拉丁词“命运女神”,它们生活在天国和人世之间,是比天国的神仙地位低但是比人类更厉害的一种存在;从现实的操作来看,“这个词指明了我们要做的事和想做的事。”并不是所有小孩都能交换,只有少之又少的人才有这个资格,这就是“对他们年幼的生命感到困扰”,或者“与世上的悲愁心有戚戚”的才有可能;而且挑选对象很严格、很仔细,这种机会只有大概十年左右才有一次,而已经成为了换生灵的孩子,要等待一个世纪才能轮到他获得换生的机会,才能再次进入人类世界;不仅如此,选择人类的孩子一般要在他们六七岁这个年龄最合适,因为超过这个年龄,自我意识会得到充分的发展,无论是变成换生灵还是人类,都将面对人类世界的规则影响,尤其是孩子父母、朋友容易发现背后换生的真相。
这是互换背后的诸种真相,但是当互换完成,换圣灵成为了人类,人类又变成了换生灵,他们就在属于自己的独立世界里开始全新的生活,而一种完美的状态则是两者互不干扰,没有任何交集。当七岁的亨利·戴变成了换生灵生活在森林世界,当换生灵变成了亨利·戴开始自己的人类世界,他们就在这种完全独立的状态中开启了新生活——当唐纳胡在小说中用单数的篇章讲述成为人类的亨利·戴的生活,用双数描述在森林中换圣灵的经历,这种单数和偶数截然分开、互不影响的文本结构本身就是为了达至一种独立状态。成为人类的亨利·戴,从七岁开始生活,一方面他要虚构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七岁之前的所谓记忆,包括对两个妹妹的相认,包括和家里亲戚、朋友建立关系,包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虚构一个故事:我就是亨利·戴。”这些通过短期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被怀疑,让自己顺利成为真正的人类。而另一方面,他要在不断成长中适应人类的生活,他开始了对文字的认识,进入到读写世界,而且开始上学、结交新的朋友;他决心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每天晚上将身体拉伸一点,希望变得和其他孩子一样;他用弹琴来讨好母亲,却发现了自己的音乐天赋,除了被送去进行专门训练之外,他体会到了音乐的快乐,为修女们上台演奏之外,更是将组建乐队付诸实践。
当然成为人类并不是都是快乐的生活,第一次看见裸身的女孩,第一次萌生了性冲动,却在那个名叫莎莉的女孩面前尴尬无比,一心想着身体的其他部位被拉伸,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器官,太小的家伙被莎莉嘲笑,对于亨利来说似乎也有了某种阴影;父亲比尔有一天选择了自杀,人类的死亡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亨利的生活中,而失去了父亲的他,为了承担家庭的责任,不得不选择去工作。这是一个人类之子必须经历的成长,快乐和痛苦同在,而在另一个世界里,成为换生灵的安尼戴也不得不面对在森林里的日子,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只有七岁,正如换生灵所要求的那样,这个年纪没有成熟的自我意识,所以安尼戴在被绑架而成为换生灵之后,记不起让自己出走的琐事,只是懵懵懂懂带着午餐剩下的饼干出门,然后躲进了栗树洞里,等他醒来,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里他认识了第一个和他说话的帕斯克,第一次开始吃蒲公英叶、豆瓣、野蘑菇做喊的沙拉,“就这样,我受了洗礼,以前的身份开始磨灭,所剩下的不会比一个婴儿所能记得的他出生前的事情更多。”
| 编号:C55·2250616·2321 |
虽然已经成为了森林里的成员,但是安尼戴的潜意识中还有着对人类生活的依存,尤其是面对黑暗的森林时,想着逃离这个古怪的地方;还会想起圣诞节,还会在纸上写东西,还能够阅读故事,去图书馆偷书,甚至还能把莎士比亚的生日作为自己的生日,还制作了日历……可以说,虽然森林生活是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生存状态,但是在安尼戴的世界里,人类的印记并没有被抹除,它通过不同的暗示被唤醒,“我忘掉的比记得的更多,我忘了自己的名字、妹妹们的名字、我亲爱的床、我的学校、我的书本、我长大后想干什么。”但是比这个忘记更被铭记的时:总有一天这些东西还会回来。实际上,不管是已经成为人类的亨利·戴,还是在森林里的安尼戴,不管是开始人类生活的换生灵,还是呈现为换生灵的人类,他们在这个完全陌异的世界里,还和“前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意味着不管是“失窃的孩子”,还是“寻找失窃的孩子”,都将以奇妙的方式将再次发现不同命运的连接点。
这个连接点是“红衣女子”,亨利·戴和换生灵们偷去东西的那个晚上,在路上被人类的车灯照到,他看到了红衣女子,或者说红衣女子看到了和他,“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未来十几年间,她是我遇见的最后一个人类。”红衣女子的出现唤醒的正是亨利·戴作为人类的前世,“当我看到她的眼睛俯视我时,我想起那个红衣女子,想起我的同学,想起镇上的人、教堂里的人、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绑架、溺水、祈祷者、圣母玛利亚,还有我的妹妹们、父亲、母亲。”甚至差点解开了自己的身份之谜。而在安尼戴那里,红衣女子也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她认出了他——红衣女子认出的是在森林中的亨利·戴,却在错认中把安尼戴当成了他,于是两个独立的世界在这种相似性中建立了联系,它构成了一种汇聚的点。除了“红衣女子”,这个点还有麦克伊内斯,安尼戴还带着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正是麦克伊内斯的,他用这个本子记下了一些东西,当然他也会偶尔想起名字,而亨利·戴也遇见了麦克伊内斯,因为麦克伊内斯能够通过催眠发现人的潜意识,亨利·戴怀着好奇的心去麦克伊内斯那里,最后麦克伊内斯告诉他的是:“我觉得你是想起了前生。我想你也许以前是个德国孩子。”
从红衣女子的错认,到麦克伊内斯掌握潜意识,其实这两个汇聚点所建立的联系并不指向对两个世界的呼应,尤为关键的是,麦克伊内斯指出亨利·戴的前生是德国孩子,而他换生的亨利·戴并不是,也就是说从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叉,在这两个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一个德国孩子的世界,那么这个换生的故事就变成了三个嵌套世界的纠葛:换灵生变成了人类的亨利·戴,而他的前生是一个德国孩子,那么换灵生已经经历了一次换生,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一个人类,被换生之后成为了换灵生,之后再次换生而成为了亨利·戴,这是一个“换生的换生”的故事,那么按照这种层叠式的换生关系,已经在森林里成为换生灵的安尼戴也可以再次换生,回到人类世界——如果换生可以无休止进行,那么寻找前生就像是一个无底洞,那么它还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当奥斯卡被换生而失败的时候,就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按照换生灵的计划,奥斯卡成为他们的目标,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但是当换生灵将奥斯卡扒光了一副、裹入了蜘蛛网、扔进和河里,却发生了意外,人类动用了各种装备寻找失踪的奥斯卡,最后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是奥斯卡的尸体,而剖开尸体,发现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奥斯卡长着一个老人的身体,更为诡异的是,已经被换生成人类的奥斯卡再次回来了,死去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换生灵。
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这样的失败让换生灵从来都是换生事件的掌控者变得可疑,而人类和换生灵彼此完全独立的神话被打破,随着这种神话被打破,人类和换生灵都面临着一种危机,也面临着选择。亨利·戴和人类一样结婚、生孩子,但是当爱德华降生,既不像他,也不像妻子泰斯,他所像的是亨利·戴的前世,就是那个德国孩子安格鲁德,这种所谓的隔代“遗传”又回到了起点;而安尼戴作为换生灵对爱德华进行观察,几乎进入到了亨利·戴的生活中,这是人类和换生灵的一次最近距离的接触;换生灵的帕斯克离开了安尼戴,但是爱德华却遇到了她,说她是个“仙灵女孩”……人类世界和换生灵世界交错在一起,这是命运的间奏曲,这是人生的对位法,但是换生灵永无法回去的规则又必然将两个世界分开,于是在“失窃的孩子”之后“寻找失窃的孩子”,也只能以音乐的方式建立联系:对于亨利·戴来说,“我已尽力寻求他的原谅,但或许那孩子和我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再接近了。”他要在人类的世界中一直走下去,而选择权也从来不属于他,“现在我是亨利·戴。”而对于换生灵的安尼戴来说,也永远不会再成为人类的自己,“我们这些仙灵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消失在降临的黑暗中,飘过墓石,回返森林,好似从未处身于人类之中。”
“音乐将我们送往两个方向,好像—个在上,一个在下,在间奏曲中,在音符的空隙中,我觉得他也想说再见,作别双重生活。”这种作别看上去有着无限的哀伤,它无法被真正改变,但是在这种间奏曲中,唐纳胡赋予这个双重生活的寓言,真正的意义则是对人类的反思。一个问题是,既然换生灵拥有更高的本领掌握更大的主动,为什么他们要选择成为人类?因为在人类面前他们是弱势,森林不断被侵袭,世界不断被占据,换圣灵不断变少,这就是人类导致的生态失衡,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会选择成为人类,“要完全成为人类,我必须屈服于真正的本性,屈服于最初的冲动。”;第二个问题是,选择人类的孩子成为换生灵需要怎样的条件?亨利·戴仅仅是离家出走,而在《神话和社会》杂志中提到的“失窃的孩子”,其命运可谓多舛,从中世纪开始,如果一个家庭中有患有疾病的孩子,父母就会把他当做其他种类的生物,让魔鬼把他们偷走,甚至丢弃他们,这就是换圣灵,换圣灵的真正意义是取消活着的权力,失窃的真相就是被抛弃:“父母有权遗弃畸形儿,他们能把孩子丢在森林里过夜,如果精灵不把它领回去,那么这个可怜不幸的东西就会冻伤而死,或被野兽叼走。”
所以当面对“失窃的孩子”这个人类命运的主题,唐纳胡一方面通过寓言来批判,“现代世界中,孩子们的麻烦多得多,一想到真正潜伏着的危险,我就不寒而栗。”而另一方面让“寻找”成为希望之所在的人类母题,题辞中引用的是路易丝·格鲁克《返乡》中的一句话:“童年,我们曾向世界投以一瞥。余下的尽是回忆。”童年留下了回忆,人类的童年代表的是美好,当亨利·戴和安尼戴的双重生活永无回到一起的可能,间奏曲所连接的两个世界却是一种记得,那里有名字,有爱,有希望,就像安尼戴留给帕斯克的最后一句话:“我走了,不会再回来,但我记得一切。”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