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21《土地与憩息的遐想》:深在性就在我们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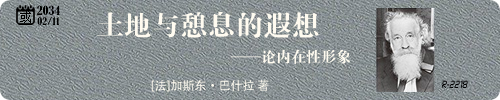
岩洞接纳着越来越属土的梦。处于岩洞内,就是开始了一段属土的冥想,就是参与到大地的生命中,就是投入到母性大地的怀抱中。
——《第六章 岩洞》
岩洞就在我们前面,岩洞就在我们面前,它是令人恐惧的岩洞,从里面传出地下的气息,仿佛它在呼吸,又仿佛是在嚎叫;它是令人欣喜的岩洞,那些深沉之音化作一种想想昂,在岩洞的入口处活跃着,会说话的岩洞似乎在邀请我们进入。岩洞被我们看见,被我们听见,岩洞让我们恐惧又让我们听见,当站在入口处,恐惧与欣喜、害怕进入又想要进入的混杂情绪又让这个入口“获得关键抉择的意义”。
实际上,当站在会说话的入口,当面临抉择,岩洞的意义已经被赋予了想象:它是一个可居住的乡间小屋,满足了我们对自然隐居想象的致敬?岩洞是一个庇护之地,满足了我们被保护憩息、宁静憩息的梦想?岩洞让我们拥有一颗温柔的心灵,那天然的窗帘不正是隔绝外部世界的梦想居所?岩洞是孤独劳作的地方,在暗处它让我们拥有劳作的力量?想象不仅是温馨的、美好的、温柔的,也是深邃的、混杂的、吓人的,甚至它放大了黑暗和死亡,仿佛秘处就有一头等待我们的怪兽。但是不管是带来何种想象,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进入”成为了被想象驱动的唯一行动,而当通过这个获得了抉择意义的入口,我们藉着岩洞也进入到了我们对于“土地与憩息的遐想”世界:它从地上部分进入属土部分,从看见部分进入看不见部分,从光亮部分进入隐秘部分,也从意识部分进入潜意识部分,也由此一个宇宙被打开,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居所被打开,“生命与死亡的辩证,窒息在综合状态中。被埋葬的英雄生活在大地的深处,过着缓慢的生活,他沉睡着,却永垂不朽。”
由想象打开的属土世界,是一个梦,是一种冥想,它和属土的意志成为两种不同的介质,而这也是加斯东·巴什拉继《土地与意志的遐想》之后开始了对于属土世界的“内在性”研究。《土地与意志的遐想》对于属土元素的研究,着重于“意志”对物质形象的形成,或者说是属土物质以能动恳求唤醒了人身上的能动感受,“属土质料一旦被勇敢好奇的手握住,希望劳作的意志就开始刺激我们。”它所表现的就是劳作的意志,劳作之人不是简单的配装工,他是塑型者,是熔炼工,是铁匠,当他的手在意志中寻找到了合适的质料,他便在预见质料的对抗中、对峙行为的发生中唤醒属土的遐想,这就是一种对立心理学的成立,“它从迅即、静滞、冷漠的对立感受转化为内在对立感受,带有多重防御,做着无尽反抗。”但是对对立心理学的研究只是巴什拉的初步研究,这种心理学如何在“憩息的遐想”中真正开启“深在形象”的研究,也就成为了这部续集的目标,在这里,巴什拉赋予这种“深在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想象不再是一种印象,不再是让形象带有主体印记,而是将物质形象实存化,“被想象、被沉思的质料如何立即就能成为内在形象。”从而完成可靠的主体性情的考察,也由此构建梦想的内在性,“我们才会梦想存在之憩息,扎根的憩息,有强度的憩息,而不只是控制着惰性之物的完全外在的静止。”
梦想的内在性是被唤醒的,它是一个从外到内深入的过程,但是从外到内还是要基于意志的作用:渴望透过外在形象看到内在之物,即希望摆脱视觉的消极性,这就需要“解剖意志”;通过好奇之眼发现具有内在结构的玩具,这就需要深究深在性的“凝视意志”;将视觉提供的全景主动与创造性想象结成联盟,这就需要“观望意志”……解剖意志、凝视意志和观望意志共建了这一从外部伸向内部的力量,“正是这种想看到所有物体内部的意志,为实存的物质形象带来了无穷价值。”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巴什拉给出了四个层面的讨论维度:首先是“被取缔的层面”,哲学家们总是指出内部的深在性就是一个错觉,他们切断了探往内部的所有好奇,所以“被取缔的层面”实际上就是以取缔的名义拒绝接受这样的态度,从而将好奇心重新回归到意志中,“隐藏是生命的第一本能。”在这里哲学家就变成了诗人和梦想者,他们走入内部,开启了“辩证的层面”,走入并不是物理性的,而是以想象构建新的维度:当走入内部,小小的世界、微细之物就变成大世界、大宇宙,“一旦我们想在微型世界中梦想或思考,一切就都变大了。”这是大小关系的辩证;从外面进入内部,而内部的一切又构成了外部的天然对立,但是如炼金士所说,物质被“翻过来”,内和外完成了倒置,这就是内外关系的辩证法;它也是“掀开又戴上”的双面辩证,是白色和黑色的辩证,是理性与想象的辩证……在这些辩证法面前,奇妙的另一个世界被展开,就如劳伦斯所说:“我们其实生活在世界的反面。火的真实世界阴暗悸动,比血还黑:我们生活的这个有光的世界,在另一面……”
这个奇妙的世界也在想象中进入到了“惊叹的层面”,它是脉石刚除掉之后的晶球,是晶球抛磨的水晶,是装饰,是面容,是内在的图画,这个精妙绝伦的世界让人惊叹,“深在的大美范畴激发出无数解释,引来无尽梦想。”但是这并不是深在性的终点,内在遐想所构建的第四个层面就是无尽的实存具有的物质密度层面,巴什拉从“颜色”和“染色”的区分阐述物质密度的深在性意义,“颜色是表面的诱惑,染色则是深层的真相。”颜色是天然的,也是无生命的,只有染色才能将颜色的质料排挤出去,升华为真正的物质根基,它是颜色的永恒存在,它让颜色浸染力量,“内在被征服,直至无尽深处,直至永恒。这正是物质想象的韧性想要的。”它将颜色的美呈现为深在的财富,它不再是色彩的唯名论而成为积极想象的物质力量,它让色彩与宇宙强力相比从而提升到“参与”的层次,“正是如此,物质梦想才有其独特的忠诚性。”
为什么从发现到参与,物质梦想体现了它具有的忠诚性?荣格对炼金术的研究中认为,炼金士就是将自己的潜意识投射到物质之上,让潜意识补充感性认识,巴什拉则提出,炼金士的潜意识不仅投射在物质至上,更投射在“自身的深处”,“人梦想深在,梦想的其实就是自我的深在。”这是一种同构,梦想物质实体的神秘品质就是梦想自身的神秘存在,存在本身的最大秘密就是隐藏在自我深处的秘密之中,所以从潜意识的投射中,巴什拉更是引申出这种深在性的本质,那就是“回归母性”,它是一种形象的压抑,是欲望退化的标志,但同时也是一种对沉睡的唤醒,是内在母性强力中的唤醒,也只有这种唤醒才能真正回到自身的深处,才能构建属土的遐想,才能召唤内在性形象,“内在性展示出这些形象的原初蕴意,那些在潜意识远处扎根的蕴意,超越了人们熟悉的形象,触摸到最远古的原始意象。”
对于这种潜意识的投射、“回归母性的唤醒,巴什拉认为这里有一个争斗的力量,这一争斗的力量体现在“糜集”形象的“喧嚣”之中,“糜集”在法语中是“fourmiller”,它的含义是发麻、挤满、充满、糜集、乱挤乱爬、挤动、万头蹿动,在巴什拉看来,这就是内在性的原始形象,“从住蛆奶酪到布满无垠夜空的群星,一切都糜集不安。”糜集不是静态的而是躁动不安,是数目繁多,这就是“动即多”,只有在细微之物的躁动之中,才能涌现高度活跃的形象,才能让强力意志与敌对意志完全投入其中,“二元性就是争斗。”它是反-自然和自然的争斗,是反-自我和自我的争斗,当内在化成为潜意识的投射,成为母性的回归,人也就成为了内在的动荡者,“追随这些形象的存在,能体会到一种鲜活状态,并非不让人陶醉:纯粹的激动。”而这也意味着巴拉什对想象的品质是基于主体的构筑,“想象领域之所以能覆盖一切,之所以能超越感知品质领域,是因为主体的重焕生机彰显为两个最辩证对立的层面:过度表现或凝神冥想——万分殷勤的人或沉浸于细微乐趣的人。”这种主体性是寻找,是想象,是激活,就是“参与”,它永远是情调化的主体,也永远在对立的张力中产生想象——想象的品质形容词不是名词,而是接近动词,“红( rouge),更接近变红(rougir),而不是红色( rougeur)。”
| 编号:B83·2251118·2393 |
潜意识投射、母性回归、二元性的争斗、主体化情调……巴什拉将想象力看成是主体生命律动和情调化,“或饱受争议,或纵情表现,文学形象都是活跃的辩证,它将主体辩证化,让主体从中体会到无比的热情。”他也正是在文学的意义上“深在性就在我们身上”的属土遐想。从第二部分开始,巴什拉走进了想象的入口,在“土地与憩息的遐想”中通过主体生命律动和情调化进行了物质想象品质的重构。故居是什么?是私密的居所,是被遗忘的住处,是勾起回忆的存在,但是当拥有遐想,故居就变成了“梦想之居”,“故居之所以能在我们心里扎根,是因为它满足了更深层(更隐秘)的潜意识暗示,远甚于简单的保护,甚于人生中第一道佑护的温暖和光芒。”它让我们进入,从地窖、根须出进入,甚至让我们迷失其中,这是一个隐居地、躲避处,更是梦想的中心:它是“地穴为根,屋檐为巢”的家;它的地窖下方藏着黑夜和清凉;它的阁楼让我们度过漫长的孤独时刻,读书、穿上祖父的衣服;夜晚它会亮起灯,“它抵御着夜晚,保护着我们。”它更是一个宇宙,“这处梦想之居是宇宙之居。”当然它在潜意识中让我们重新回来,在回归中重新钻入母亲的怀抱,“房屋之诗重拾起这项工作,它激活了内在性,重新找到憩息哲学的巨大安全感。”
梦想之居是隐秘之处、庇护之所、母性之家、宇宙之局,而实际上《白鲸》中的“约拿情结”也是想象力构筑的“梦想之居”:约拿在鲸鱼肚子里,它当然首先是一种“吞没”,也是精神层面的消化不良;但当肚子吞没约拿,它也是一个友好的腹腔,为他人提供乐然一个住所;约拿情结也可以看做是断奶情结的一个特例;阴性约拿和阳性约拿也是潜意识雌雄同体的象征,当“重见天日”就代表着进入了意识生活,这是一种重生……巴拉什将这个情结才子置于“回归母性”的分析之中,吞入和重见天日和出生神话有关,而鲸鱼肚子就变成了母亲的肚子,德普朗希说,佛的母亲“梦见自己吞下一头白象而受孕”,所以它回到了生命的情调化主题,“母亲的肚子和石棺,难道不是处于不同时段的同一个形象?”从死亡到重生,想象的世界打开了潜意识,打开了梦想,“一个被封的存在,一个被保护的存在,一个隐藏着的存在,一个把奥秘还给深层的存在。”
梦想之居和“约拿情结”在巴什拉的阐述中更多是作为一种从外部进入潜意识的入口,并没有涉及到属土的遐想,而接下去巴什拉从岩洞、迷宫、蛇、根和“酒与炼金士的葡萄树”中,深入到属土的地下世界,而且他完全放弃了地下世界的宗教性和神话领域,“我们只想考察梦想,考察被表述的梦想,具体来说,考察那些欲求文学表述的梦想……”而这种文学性梦想不正是契合着“内在性形象”?从岩洞入口进入到辩证世界,属土的遐想就是生命与死亡的辩证,它以参与的方式深入到大地的生命中,投入到母性的怀抱中,而“迷宫”更具有这样的性质,“所有迷宫都有一个潜意识维度”。迷宫是睡眠中经历的深度之梦,是迷失了方向的困境,它的潜意识就是对痛苦往昔的焦虑和对不幸未来的担忧;迷宫是延展、堆积、弯曲,是一场远处的苦难,它是出生时留下的噩梦;迷宫是细小的管子,它令人感到窒息,但是只有爬出来才能看见盛开的花,“花就在我眼前,这是对我辛劳的酬报。”迷宫有坚硬的迷宫和柔软的迷宫,它们辩证地具有象征意义:走进噩梦或走出噩梦,远离生活或回归生活,受到保护或成为囚徒,穷人场景或富人场景;更重要的是,迷宫作为城市的下面部分,总是对立与城市道路,所以它是肮脏的、污秽的、也更具有想象力。也正是在这里,巴什拉完全进入到属土世界的深在性之中,“土地提供了巢穴、岩洞、岩穴,还有需要勇气进入的水井和矿井;挖掘意志取代了憩息遐想,想在土中越挖越深。”内在性是危险的,内在性是噩梦,内在性也是庇护,是下降超验,是自我之下的意识,是地下的“我思故我在”,所以“土地与憩息的遐想”的真正意义是:“深在性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深在的存在,“伟大的深在形象,与我们垂直同构。”
蛇是一种入土的原始异象,但是它是我们的象征引擎,“一个没有将自己的引擎强力转移成外在器官或矫作方式,而是将之转化为自身运动的内在动力。”它是地下之恶的标志,是死亡有关的存在,是一个诱惑者,更是属土的生命,“世界之蛇巨大无比,岩石是它的鳞角,树木在鳞角间生长。告诉你们,你们用铲锹翻着的大地是活的,它是一条打着瞌睡的蛇。你们在这条大蛇身上走来走去,湖泊在它的褶皱间躺着,就像响尾蛇鳞角间的一滴雨水。可是它并不因此而减少生命力。土地活着。”劳伦斯这个样说,在想象的世界里,咬尾蛇象征着活着的永恒,在伊甸园里制造诱惑也成为食土为生的话语,它是欲望,是攻击,是爬行的意识,是弯曲中的诞生……“只有属土的地下想象,才能让富有如此超然遐想的叙述变得可读。”同样,根在地下,它也激发了属土的遐想:它是深埋着的潜意识,它是活着的死亡,它是漫长的睡眠,它是缓慢的死亡;它具有能动的力量,连接着空气和土地,连接着树和根须,甚至是阳具的象征,“土的行为,在根的内在生命里,把自己指定成一个原型。它主宰着我们的植物存在,人也想成为植物。”而在“酒与炼金士的葡萄树”中,巴什拉将酒的精神变成了葡萄的炼金术,“葡萄树是磁石。它吸着太阳之金,诱惑着星宿之金,来完成炼金的婚礼。”
从梦想之居、约拿情节打开潜意识和母性回归的入口,到在蛇、根和葡萄的原始意象中进入属土的世界,巴什拉越走越深,在下降超验中激活了更多的属土遐想,它是想象,它是冥想,它是我思故我在,它是充满危险的内在性,巴什拉就像是蛇是根是葡萄和酒,在完全释放潜意识中,在对生命的纯粹体验中,成为了独特的、地下的、深在性的品酒的哲人,“不知多少次,葡萄树这位药草女王,不仅获取了她的温柔侍女——覆盆子——的芬芳,还获得了她的粗暴侍女——火石——的芳香。”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625]
顾后:数九寒冬从“零度”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