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22《哑巴乐园》:我喜欢简单和粗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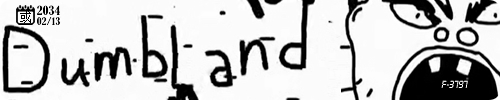
简单是形式,粗暴是内容,形式和内容组成简单粗暴的世界,是短片本身的预设,也是大卫·林奇的一种创作观体现:这是林奇从2001年至2002年5月创作的系列实验短片,那时的他对Flash这一现代制作技术手段深深迷恋,不仅在制作上简单易行,而且传播具有快速性,于是一连推出了以“哑巴”为主角的一系列短片,构成了集暴力与荒诞于一身的“哑巴乐园”。
动画的线条是粗粝甚至粗劣的,场景和人物设置也基本上是固定化和扁平化的,这种涂鸦式的形式表现就是简单和粗暴的。“哑巴乐园”的故事就是以暴力主义者“哑巴”为主角,他就生活在自我制造的暴力世界中:他看中了邻居的木棚,“那是我的木棚”,极强的占有欲在邻居卸下了胳膊表示抗议的时候,他爆出粗口:“你是干鸭子的。”妻子在跑步机上跑步,他忍受不了跑步机不断重复的机械式噪音,一把把妻子扔了出去,儿子在跑步机上,他也不由分说将他扔了出去;推销员像他推销“闻闻香”,他不分青红皂白,就痛揍了推销员;有人被木棍卡住了嘴巴,他去“帮忙”,木棍非但卡在那里没有拿下来,在他的暴力帮助下,那人甚至被木棍戳穿了眼睛,最后取了下来,又一把将那人踢出栅栏外,汽车驶过,那人被活活碾过……
大大的脸,不长头发的脑袋,两条浓黑的眉毛,两个奇大的鼻孔,上面两颗牙和下面一颗牙,这就是林奇设计的“哑巴”造型,在线条制造的抖动感中,一个暴力主义者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且每一次这张脸、这种表情就是即将爆发的状态,他对邻居下手,他对推销员下手,他对儿子下手,他对妻子下手,在狂揍中还不时爆出脏话,还总是撅起屁股放屁,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他施展暴力的对象。但是林奇所传达的暴力并非是“哑巴”一个人的表演,他将暴力泛化,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暴力的化身:妻子神神叨叨,不时发出惊叫;儿子啰啰嗦嗦,总是添油加醋;他因为灯泡触电,医生来诊治,对他进行疼痛测试,他毫无感觉,最后医生竟然将一把刀插进了他的脑袋,哑巴的疼痛感终于被唤醒,他以暴力反击了血腥,医生留下一句话:“你完全正常。”《一位好友来访》中,被塑造成牛仔的朋友在他面前抽烟、喝酒,说起钓鱼、打猎,“我把它们的头都砍了”,然后掏出内脏,然后烤肉吃,然后把标本挂在墙上,哑巴说自己也会这么做;彪形大汉带来了“鲍勃叔叔”,让哑巴照顾他,面对痴呆、呕吐的鲍勃叔叔,哑巴在彪形大汉面前认怂,又忍无可忍疼,在爆发的那一刻却被彪形大汉打到了树上……
| 导演: 大卫·林奇 |
他是暴力实施者,他也是暴力受害者,于是暴力的实施和受害互为因果,这就是“哑巴乐园”的隐喻,没有谁是真正的暴力主义者,当暴力成为对暴力的回应,暴力也就在林奇的世界里成为一种常态,而这种常态更成为“哑巴乐园”之外的社会性存在:“干鸭子”的邻居、医生面前的正常人、电视里的拳击比赛,都在传递着社会性的暴力现实,而当推销员被打倒的时候,口中念着的是“葛底斯堡演讲”:“四十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大路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在《我的牙齿流血》中,除了电视里的拳击比赛之外,外面不断响起救护车的声音,之后是警车、坦克,以及奔跑过的军警,这难道不是对暴力社会的一种讽刺?而哑巴在这样的压迫性环境里,面对飞来的苍蝇,啪的一声,发出“该死的苍蝇”的咒骂,这一声咒骂难道不是另有所指?
在社会性暴力面前,哑巴也许只能是一个渺小的暴力主义者,在这里他的位置进行了置换,也就是说他变成了“该死的苍蝇”,最后一集的标题就是《蚂蚁们》,家里出现了一只蚂蚁,然后是两只、三只,最后变成了密密麻麻的蚂蚁大军,哑巴挥拳向着蚂蚁大军进攻,但是在拍打、驱赶甚至消灭蚂蚁的过程中,他自己也被暴力伤害,他成了失败者,他似乎看到了蚂蚁在他面前跳舞、唱歌,骂他是混蛋、白痴和狗屎,而被送进医院之后他的手脚被打上了石膏,这是暴力的结束,但是在病床上望着无法动弹的双脚,他忽然发现了一只蚂蚁,然后是两只、三只蚂蚁,最后变成了密密麻麻的蚂蚁大军,他们爬上了他的身体,他们占有了他的身体,而哑巴再无法伸手去打他们了,暴力被暴力所结束,强大的暴力主义者却在渺小的蚂蚁面前成为了失败者,伤残的他被蚂蚁推向了真正崩溃的边缘。
“哑巴乐园”里有用拳脚解决一切问题的暴力主义者,“哑巴乐园”的外部是更多社会性的暴力主义者,暴力和暴力的对话是暴力,暴力消灭暴力也是暴力,当暴力主义者被触电、被插刀、被伤残,这是暴力的最终下场,但是暴力没有终止,更多的暴力正在涌现,更多的暴力主义者在更大的“哑巴乐园”里成为了牺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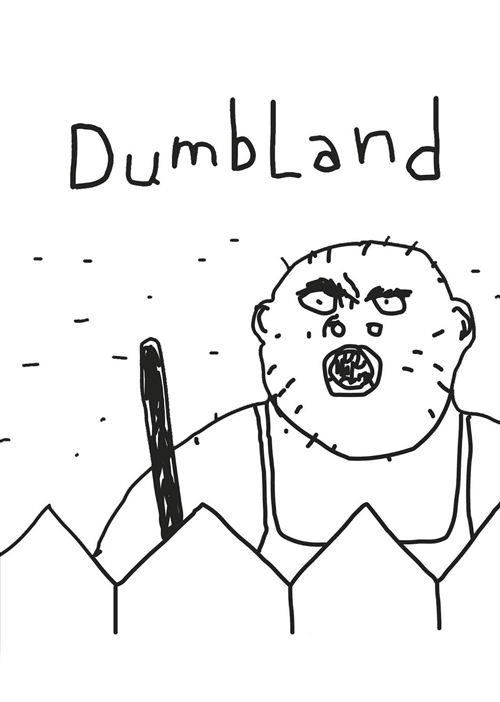
《哑巴乐园》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