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1《爱尔娜》: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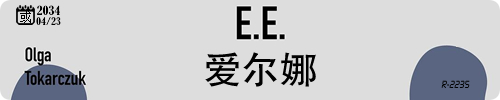
所有这一切背后的悲哀也是转瞬即逝的,阿尔杜尔坚信,“昨天”听起来就和“一百年前”一样,它的意义也是一样的:那就是都不存在了。
——《阿尔杜尔·莎茨曼》
《爱尔娜》,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打开小说就是进入托卡尔丘克创作的原点;而从阅读小说的第一天往前推两天,是1月29日的前天,这一天托卡尔丘克迎来了她64岁的生日,阅读也成为了一名普通读者对她生日的某种敬意。第一部小说和纪念出生的生日,构成了托卡尔丘克的“昨天”,在小说文本对“昨天”的揭示中,在阅读式的敬意中,当《爱尔娜》的故事回到了“一百年前”,到底什么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不存在”?
“不存在”是阿尔杜尔·莎茨曼面对新时代时发出的感慨,那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那时老洛韦医生和他散发着碳酸气味的药箱已经不在了,那时疯狂、凶恶的弗罗梅尔和他驼背的姐姐泰蕾莎也不见了,甚至连爱尔娜母亲爱尔茨内尔居住的住宅、住宅中带紫罗兰图案的玻璃杯也都不见了,它们都在转瞬即逝中告别了这个时代。但是当阿尔杜尔充满着信心去见开了裁缝店的爱尔娜,爱尔娜冷漠而麻木地看着他,然后说出了一句话:“很遗憾,我不认识你。”这对于阿尔杜尔来说是一次真正的“死亡”,为什么自己投入精力、对她进行实验和医治、并最终找出了病根让她“正常”,爱尔娜却不认识他了?阿尔杜尔无法用她假装不认识来消除怀疑,在他看来,的确已经走向了新的时代,“他走过城市,感觉这座城市越来越空了,看起来也越来越奇怪了,就像一个剧院原来的布景有人把它撤换了,现在换成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布景。”
时代变了?那是1914年8月,阿尔杜尔穿上制服向内务马尔克特区出发,他的口袋里是一封召唤他上前线的信,“在最后时刻,和亲人的坟墓告完别,和朋友们饮酒,和熟人们饮茶告了别,他就想到了小爱尔娜。”他是换下精神病医生的衣服而换上了军装,他是放弃了给人看病的工作而奔赴前线,那么,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在战争爆发中是不是和“昨天”一样,完全变成了“一百年前”,变成了完全陌生的场景,变成了转瞬即逝的存在,变成了“我不认识你”的冷漠和麻木?甚至阿尔杜尔用心理分析解决了爱尔娜的幽灵问题是不是也是这个新时代注定要失去的一部分?托卡尔丘克在她的第一部小说中,以如此悲观主义的方式注解了新时代到来时的悲哀,她是不是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心理分析何为?科学何为?人之为人何为?
在十五岁的爱尔娜·爱尔茨内尔身上,托卡尔丘克确实放置了一个进入新世纪的旧病例,这个病例如此典型又如此神秘,以至于在1908年10月那个寻常的午餐时刻,当爱尔娜突然在餐桌旁晕倒,她的脸色变得苍白,身子慢慢滑落到地板上,整个爱尔茨内尔家庭的秩序就被打破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少女的昏厥,而是整个时代精神困境的症候显现,爱尔娜在昏迷中声称看见桌子边站着一个人,一个鬼魂,而爱尔茨内尔夫人立即认出那是她十七年前就已死去的父亲,这一刻,肉体的脆弱与灵魂的躁动同时爆发,将一个家庭拖入了关于存在与虚无、科学与迷信、理性与疯狂的漫长争辩。这个病例的特殊性在于,爱尔娜的症状横跨了多个领域:她既有夜游症的症状,会在无意识中游荡;她又能在特定的“神志恍惚”状态下与“幽灵”对话,成为瓦尔特·弗罗梅尔眼中所谓的“灵媒”;她还做着那些预言性的梦境,梦见自己在结冰的池塘上行走,冰面破裂,她在水下看见太阳,感到幸福并想永远留在那里,而几天后厨娘路齐娜就讲述了奥得河上发生的冰面破裂事故,一个女人沉入水底,要到明年春天才能找到。这些梦境的真实性“就像可以触摸的现实”,让医学诊断陷入了困境。爱尔娜的病症因此成为了一个节点,不同的解释体系在这里交锋,每一种解释都代表着一种世界观,都试图用自己的话语定义这个少女的身体与灵魂到底发生了什么。
瓦尔特·弗罗梅尔作为死亡登记处的职员,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在青铜色的大门后记录生命的终结,这使他成为了死亡的专家,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超越死亡界限的事物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他代表着神秘主义者的路径,通过唯灵论和招魂术来解读爱尔娜,在他眼中,爱尔娜不是一种病理现象,而是一个“被唤醒了通灵天赋”的灵媒,是“灵魂的本质”能够通灵的媒介,弗罗梅尔给爱尔娜讲授那些著名灵媒的生平,将她们圣化为“圣洁的处女”,把怀疑者比作“异教徒或恶魔之龙”,他所构建的就是一套完整的宇宙观:人的躯体只是用来游过人生大河的木排,灵魂通过一生的流浪得到充实和净化,最终都要到上帝那里去。他甚至详细解释了灵魂的转世机制,认为一个人死后,灵魂要找到能够获得新生活经验的最佳生存环境,进入未来母亲的体内重新出生,但重新为人的他已经不记得以前是谁,因为过去的记忆只留在“星光体”中,这套理论体系赋予了爱尔娜的幻觉以神圣的意义,将她的痛苦转化为通灵的礼物,把她的身体变成了灵魂出入的通道。
| 编号:C38·2251213·2407 |
然而,弗罗梅尔的神秘主义并非纯粹的信仰,它充满了矛盾和欲望,他一方面将爱尔娜视为女儿、学生、作品,另一方面又对她母亲爱尔茨内尔夫人怀有隐秘的爱恋,这种情感的混杂使他的灵媒培养计划带上了一种占有欲和控制欲,更成为他所理解的宇宙生成论的概括——山崩地裂、河水流动、树木生长、城市拔地而起、新人诞生、老人死去,所有这些生生不息的过程都被他归结为女性的创造力。但这种归结同时也暗示着一种危险:当弗罗梅尔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一栋房子里”,与完全不理解自己的人“囚禁”在一起,当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无情地离他而去时,他平生第一次想到了自己的死。这个懂得死亡的专家,这个对死亡规律疯狂着迷的人,在面对新时代的冲击时,竟然只能想到用死亡来解决“这个可怕境况”,神秘主义在这里暴露出了它的无力:它或许能够解释幽灵的存在,却无法治愈灵魂的孤独;它或许能够构建宏大的宇宙叙事,却无法应对现代性的危机。
与弗罗梅尔相对的是洛韦医生,他代表着一种过渡状态:既属于旧时代的蒙昧,又试图拥抱新科学;他的诊断充满了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在“发明蒸汽机和使用铁器的那个时候开始学医”,坚信医学世界里“没有幽灵的位置”,用“歇斯底里”这个科学名词来解释许多精神疾病,另一方面,在他“有理智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他又隐约相信某种超越知识明灯照亮范围的存在,“不一定是幽灵,也不一定是什么鬼魂附身。”这种矛盾使他成为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一方面用鸡汤、甜菜、带血的猪肝、煎牛排这些营养食物来治疗爱尔娜的脸色苍白,试图用生理学的恢复来驱散那些幻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当爱尔娜在神志恍惚中说出那些预言和陌生的话语时,他“是这么相信”的,相信这确实是与幽灵世界的交往。洛韦医生的“歇斯底里”诊断看似科学,实则是一个收容一切不可解现象的垃圾桶,他既想从中寻找病理学的依据,又无法否认其中某种超验的力量。他的困境在于,他站在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就像弗罗梅尔所描述的那样,但他没有像弗罗梅尔那样选择完全投向神秘主义,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拥抱科学理性。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躺在憋闷的房间里等待死亡,他甚至希望自己“彻底地死去,躯体和灵魂都死去”,这种对虚无的渴望,这种“既不入地狱,也不进天堂”的状态,恰恰体现了一个旧时代医生面对新世界时的精神衰竭。
阿尔杜尔·莎茨曼的登场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人脑生理学的研究者,他代表着理性主义和科学实证精神,他接受的是康德到精神病病原学、到自然选择学说、再到研究大脑构造的现代科学训练,他把人的脑袋看成是一台内部结构完美无缺的机器,也看成是一个乐器,然而,阿尔杜尔并非简单的科学乐观主义者,他的身份充满了内在的撕裂:他是犹太人,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他持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这使他对现存秩序持批判态度;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过早地接受了怀疑主义。这些身份的重叠使他的理性主义带有一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当他第一次看到爱尔娜在招魂聚会中的表现,他并没有像弗罗梅尔那样立即皈依神秘主义,也没有像洛韦那样陷入矛盾,而是试图寻找一种“纯粹的心理学研究,真正的科学考察”。阿尔杜尔的科学方法在最初也是笨拙的,他在笔记中记录爱尔娜的“个性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就像一个变色龙”,试图从病理学角度解释她的思维紊乱和幻想习惯。然而,阿尔杜尔的这种生理学还原论在爱尔娜面前屡屡受挫,爱尔娜的症状太过于复杂,她的梦境太过于真实,她在恍惚状态下说出的那些关于地震的预言又太过于准确,简单的机械论解释无法涵盖她的精神世界。阿尔杜尔的困境在于,他的理性主义虽然坚定,但面对人的灵魂时,他感到了“神魂超脱般的狂喜”与深深的无力。
真正的转折来自于沃盖尔教授,他代表着托卡尔丘克所认可的那种科学工作者——既不排斥理性,又尊重未知的深度。沃盖尔将心理学分成了两个方向:一边是实验心理学,研究神经冲动的传导速度、大脑中精神功能定位,这在沃盖尔看来只是“舔口水的动作”;另一边是心理分析,关注“隐藏在无意识中的一种力量”,他认为无意识是“独立于我们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就像魔鬼,是一种界于神和鬼之间的力量”,它通过睡梦、象征或精神病症状进入到有意识中,这种对潜意识的尊重,使沃盖尔能够从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出发,理解爱尔娜的病症并非简单的生理失调,而是被压抑的欲望、恐惧和创伤的象征性表达。正是在沃盖尔的指导下,阿尔杜尔开始真正理解爱尔娜。他们通过催眠术进入她的潜意识,通过自由联想破解她的梦境密码,通过分析她在神志恍惚状态下的言行举止来触摸那个被理性意识压抑的“另一个自我”。这种治疗方法不是简单地否定幽灵的存在,而是理解这些幽灵乃是爱尔娜内心世界的投射,是她无法言说的欲望和恐惧的具象化。当爱尔娜在恍惚中说“在有生命的一切中,我们已经死了”,当她满脸苍白地说出“松鼠”这个词,当她的自动书写画出那些曲折的线条最终形成字母,心理分析揭示出这些都是被压抑的记忆和情感的变形,是少女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身份危机的象征。
然而,爱尔娜病症的真正揭示却源于一个偶然的生理事件:她的初潮,当贝尔塔发现爱尔娜内裤上的血迹,当“一条非常复杂的布料装置把她的臀部和会阴全都包住了”,当贝尔塔说“好了,现在你是个真正的女人了”,这个生理的转折点成为了整个治疗的关键。在此之前,爱尔娜症状中的那些鬼魂、那些预言、那些恍惚状态下的呓语,都可以被神秘主义解释为通灵,被生理学解释为歇斯底里,被心理学解释为潜意识的显现。但经血的到来将一切回溯到了最根本的维度:这是一个少女成为女人的过程,是身体性的、生理性的、无法被任何理论完全捕捉的生命庆典。托卡尔丘克在这里展现了她对女性经验的深刻理解,爱尔娜的病症,从根本上说,是成为女人的阵痛,她的身体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化,她的社会角色正在从女孩转变为女人,她的精神世界正在试图适应这种转变带来的动荡,那些所谓的幽灵,那些灵媒的预言,那些关于地震的警告,不过是她内心风暴的外在投射。弗罗梅尔试图用灵魂转世的理论来解释她的体验,洛韦试图用歇斯底里来概括她的症状,阿尔杜尔试图用大脑皮层兴奋度来定位她的病灶,但他们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爱尔娜首先是一个正在长大的女性身体,她的灵魂与肉体是不可分割的,她的疯狂与智慧都根植于这个正在绽放的女性躯体。
双胞胎姐妹卡塔利内和赫利斯迪内在这一揭示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她们“可以用一面小镜子探视到你的梦境”,这不仅是一种孩童的恶作剧,更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她们是那面照见真相的镜子,是揭示隐秘的媒介,当她们用小镜子的光反射照亮房间,当她们在天窗的光束中看见女教师吊死在大吊灯下,她们展现出了超越成人的直觉能力。而在爱尔娜的病例中,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的细节——双胞胎的恶作剧、镜子中的反射、那个“褐色的蠼螋"”共同构成了揭示真相的偶然网络。托卡尔丘克通过爱尔娜的病例,实际上是在诊断整个时代的病症,这种病症不仅体现在爱尔娜身上,也蔓延到了周围的每一个人:爱尔茨内尔夫人,这位曾经在柏林梦想成为演员的女性,如今被困在生育和家务的循环中,她在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具体的不可复制的存在”,却又感到“失望和受骗”,感到自己“和一个完全不理解她的人囚禁在一栋房子里”,她的购物狂行为,她对家里上上下下的大扫除,她对小女儿莉娜的偏爱,都是这种时代病症的表现,一种通过物质占有和母性投射来填补精神空虚的强迫行为。
瓦尔特·弗罗梅尔的病症则是另一种形态,作为死亡登记处的职员,他对死亡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生命的逃避;那个“像童话里守护地下宝藏的驼着背的小矮人幽灵”般的姐姐,那个言语不清、总是慢慢收拾厨房的姐姐,实际上也是时代病症的牺牲品。他们的母亲安娜玛莉娅;那个“很积极的妇女参政派”,后来沉迷于通灵术,带着孩子们在“大地的颜色像湿漉漉的灰尘”的广阔空间中感受“灵魂的苦痛”。弗罗梅尔姐弟的童年充满了“恶魔缠身和驱魔术”的阴影,这种背景使得瓦尔特对爱尔娜的培养既是一种救赎的尝试,也是一种创伤的重复,当他最终向爱尔茨内尔夫人表白“我爱你”,当他意识到“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女人’”却也明白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无情地离他而去”时,他的病症达到了顶点——他变成了自己研究的死亡本身,“死亡是解决这个可怕境况的最佳手段。”
甚至连阿尔杜尔·莎茨曼,这个理性的代表,也无法逃脱时代的病症,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犹太出身、他的无神论,使他在战前的欧洲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当他“大张旗鼓地表明他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时,当他感受到“精仰病大夫”式的自我怀疑时,他实际上也在经历着一种精神的流离失所。他的病症是理性的病症,他相信通过科学可以解释一切,可以治愈爱尔娜,可以找到真理,但当他最终被爱尔娜遗忘,当他身穿军装走向前线,当他把玫瑰花放在长椅上然后追赶开走的电车时,他明白了理性的局限:他可以治愈一个人的歇斯底里,却无法阻止整个时代的疯狂;他可以分析潜意识的秘密,却无法挽回“昨天”变成“一百年前”的必然流逝。
洛韦医生的死亡则是这种时代病症最悲凉的注脚,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既不入地狱,也不进天堂”,希望自己“彻底地死去,躯体和灵魂都死去”,这种对完全虚无的渴望,这种对上帝在大爆炸中就已经毁灭的认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他躯体中的一小块,就像他周围的一些,仍在不断地死亡”,体现了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面对新世纪时的彻底绝望,他的病症是信仰的病症——他曾经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相信某种超越性的存在,但最终他什么都不相信,包括他自己。双胞胎姐妹的病症则是童年的病症,是对成人世界虚伪性的直觉反应,她们翻找父亲的写字台,在橱柜抽屉里寻找旧物,用小镜子反射光线来窥探成人的秘密,这些行为都是对那个压抑的、充满谎言的世界的反抗,当她们告诉爱尔娜“我们知道你做的梦都是什么”,当她们通过镜子让爱尔娜看到自己“脑门上有一些红疹”、“鼻子太突出”、“嘴巴太小”,她们实际上是在执行一种残酷的启蒙:撕破幻想,直面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爱尔娜》中的人物构成了一个病症的群像,而爱尔娜本人则是这个群像的中心镜像。她的“治愈”并不意味着病症的消除,而是意味着一种转变,当她不再是“灵媒”,当她不再看见鬼魂,当她“再也不会听到奇怪的声音”,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在裁缝店里工作的普通女性。但这种“正常化”本身是否也是一种病症?当1914年8月,阿尔杜尔满怀期待地找到她,她却冷漠地说“很遗憾,我不认识你”,这种遗忘是否比她的通灵更加可怕?托卡尔丘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我们用科学治愈了那些“不正常”的症状,当我们将一个人从神秘主义的迷雾中解救出来,让她们变成“正常”的公民,我们是否真的治愈了她们,还是只是杀死了她们灵魂中那些独特的、超越性的部分?爱尔娜的遗忘,可以被理解为心理分析的成功,弗洛伊德式的治疗确实可以压抑那些创伤性的记忆,让病人重新适应现实。但这种成功同时也是悲剧:那个曾经能够与幽灵对话、能够预言地震、能够在水下看见太阳的爱尔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麻木的、冷漠的、“正常”的女人。
这种结局体现了托卡尔丘克对科学理性的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科学确实可以解释世界,可以诊断病症,可以消除幻觉,但它也可能消除诗意,消除神秘,消除那些使我们成为人的独特经验。当阿尔杜尔把玫瑰花放在长椅上,当他意识到“昨天”和“一百年前”一样都变成了“不存在”,他实际上是在哀悼这种科学的胜利所带来的失落,他成功地让爱尔娜“康复”了,但这种康复的代价是记忆、是联系、是曾经共同经历的那些神秘时刻。然而,托卡尔丘克的悲观主义并非简单的反科学立场,她通过沃盖尔教授所展示的那种心理分析——那种尊重无意识、尊重梦境、尊重象征的科学——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这种科学不是粗暴地否定神秘主义,而是试图理解它,将其转化为人类自我认识的资源。问题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运用科学,是否能够在理性和神秘之间找到平衡。
贝克莱的题辞“只有人是真切存在的”在小说的语境中获得了多重含义。首先,它反对了那种将精神与物质完全割裂的哲学,强调人的整体性。爱尔娜的灵魂与肉体是不可分的,她的病症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其次,它强调了人的具体性、个体性,不是抽象的“女人”或“灵媒”或“病人”,而是具体的、在此时此地受苦的、有血有肉的人。最后,当弗罗梅尔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女人’”时,他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对生命的肯定,对生成、创造、变化的肯定,而这种肯定根植于对女性经验的具体理解。爱尔娜的故事因此成为了关于“成为人,而且成为一个女人”的叙事,在20世纪初那个充满变革和动荡的时代,成为一个女人意味着要面对生理的突变、社会的期待、精神的危机;意味着要在科学和迷信、理性和疯狂、过去和未来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意味着要承受被遗忘的风险,要承担记忆的重负。
阿尔杜尔·莎茨曼最后把玫瑰花放在长椅上,这个姿态既是对爱尔娜的告别,也是对整个逝去时代的告别,更是对科学理性局限性的承认。他无法让爱尔娜记住他,就像他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无法挽回母亲的死亡,无法让洛韦医生重生。科学可以分析潜意识,可以治愈歇斯底里,但无法创造记忆,无法挽回时间,无法赋予生命以意义。但托卡尔丘克的深刻之处在于,她让这种“不存在”本身成为了一种存在方式,通过写作,通过将这个故事保存下来,托卡尔丘克在二十四岁时写下这部小说,她是否已经预感到,她日后的所有创作都将围绕这些主题展开:历史的重写、女性的身体、边缘人物的声音、科学与神秘的对话?这部处女作就像爱尔娜在恍惚中写下的那些字母,“开始显得很大,写得不工整,像孩子写的,后来就逐渐变小了,也更工整了”,它标志着一位伟大作家的诞生,也标志着一种独特的文学视角的形成。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7676]
下一篇:没有了,返回『读·者』 @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