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02 《鬼斧集》:被自己的经验与生活消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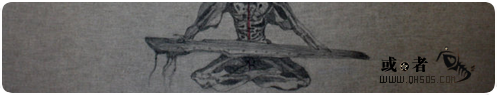
不,你已经没有机会了。说着,她张开嘴,一口把我的头咬了下来。因为没有了头,所以当我从梦中醒来时,便什么也不记得了。
——杨典《螳螂志异》
我确信这不是3009年,就像确信封面上的那个手持武器徐徐前行的影像不是那只食夫的雌螳螂,当然也不是被张嘴咬掉幻想、正在做爱的雄螳螂,那只是我的一个梦,如果返回100年前,回到2009年,那个梦也远没有开始进入场景,那时的一切都还在”摆架的花,自杀的鱼,咳嗽的钟表,一条昏厥在树林边的道路、长癣的民族、冷火、神仙、情种之间作如是观,而当所有的的幻想在跨越一百年后再次回来的时候,梦也已经掉落了那个看见一切的头。
宛如“惊醒”。是那个叫凌山的40岁的记者从火车上被风沙吹下来的感觉,有关自己的病源的“事件”却已经不在了,那火车里的所有对话和记忆就如梦境,呼啸而过,而最后剩下的也只有“疼痛的自己”,惊醒过来,是一个生命文明的戛然而止,凌山逃离的是时间,还是虚无的梦?他惊醒了自己,却原来是一个叫做敦煌的地方和一个童僧,“神,就是时间。”那么自己又在哪里?就像被扔进一个虚无之境,不管是螳螂之梦,还是被惊醒的自己,原来都是和时间的幻觉有关,就像2009对应于3009,无非是一个副本,当打开的时候,“你是谁”就会成为凌山被“事件”抛弃之后的一个最大疑问。
你是谁?他问不如自问。杨典不是凌山,也不是螳螂,在《后记》中,却也是一个被“惊醒”的自己:“而且还惊讶地觉得:原来这些年我也写了这许多小说。”这恍然如梦的感觉就直接变成了那个疯子思想家的“瘦子”:“如果没有具体的字迹作为证据,我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会是我写的。”难以想象是因为在里面太久了,没有惊醒,没有疼痛的自己,所以瘦子要“把自己搞成了聋子”,不想装聋,从而逃离他们的世界。装聋是一种技术,而真的聋了则是境界,成为思想家,成为记忆和印象之外的人,成为每个装聋作哑之外的人,或者就不再是那个被自己的经验与生活消灭的人,一句话,就是剩余的人。只有成为一个“敏捷的聋子”,才可能“彻底进入了自己对语言的想象中了”,才可能做一个100年之后的梦,才可能体验螳螂食夫之后的“惊醒者”。
“自己对语言的想象”是不是也是一个乌托邦?在《二毛子》里杨典似乎有着对于自己的解构和建构,“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岁闰中秋日,万川山人杨典诰论”。而据考证的结果是“杨典诰论”其实是杨典“诰论”,而不是“杨典诰”论,而《万川外史稿》作者之名,其实就是叫杨典。从“杨典诰”到“杨典”,是不是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惊醒,而且进入了自己对语言的想象中,回归自己,从一个姓氏的正名开始,而在自己的语言想象中,杨典所有的努力都在消除那种历史的、事件的歧义,不是“二毛子”,不是异教徒,那枪也没有把世界最后给解决掉,“我先是吓得目瞪口呆了,然后撒腿就跑,从此消失在1900年的夜色之中。”当1900年的夜色吞噬而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杨典对于乌托邦的那种向往和恐惧,正名总是伴随着逃避,时间总是伴随着幻觉,而那些“被自己的经验与生活消灭”的人并不是剩余的人,相反,他们正在制造着一场关于“异端小说、颓废故事与古史传奇”的语言狂欢。
或者说,为什么凌山要去寻找事件这一“病源”,螳螂为什么要把一个梦做到100年之后?“亲爱的内幕人,我是你永恒的颠覆者。”那么真正的内幕人和颠覆者又在哪里?他们需要颠覆什么样的秩序,需要自己如何去消灭经验与生活?是所谓的历史文明造就的中心?“我们不过是在离开时一路捡拾文明的遗物,权且当做纪念品。”那个伊斯兰教装束的老人也是向导,在火车的呼啸中讲述文明,讲述中心不断被边缘的历史和现实,而这一切是可以被颠覆的吗?或者说,大历史下的中心论是不是也是一个乌托邦,在自己的“被惊醒”的机遇面前,是必须被颠覆和解构的。“这个国家的真相”是关于文明的宏大叙事,但是杨典似乎并不想成为永远的凌山,在更多意义上,他只想成为那一只螳螂,走进梦的现实里并且成为那个体验者,成为那个内幕者,成为永恒的颠覆者。另一个向导是锦儿,《某美人肉体奥义书(残卷)》直接将国家叙事带进了身体叙事,而且杂夹着某些色情成分,就像那两只做爱的螳螂,在身体的极致高潮中达到解构的目的。所以“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将深邃,美好和罪恶浑然一体地融合于身,亦正亦邪,亦古亦今的女人”。而所有的努力则是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入身体的秘境,在“腿的交叉,手的交叉,命运的交叉”中抵达另一个中心,而其实所有美丑、善恶混杂在一起,在身体的极度体验中,却将现实的时间抽掉了,“她是半截爱人,不是前与后,上与下的半截,而是没有中间的半截。”半截所缺席的时间,是在过去和未来之外的今天,而肉体所书写的奥义书也是在一个“帝国首都最中心的贫民窟里”完成,帝国首都和贫民窟,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对比性,所以对于中心的颠覆也具有震撼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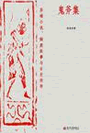 | 编号:C28·2121022·0924 |
美,和文明、宗教一样,都是掩盖了内幕的中心,是帝国的首都,是没有自我的地方,但其实,世界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世界是边缘的,是侧面的,甚至是没有今天的,所有人都可能成为那个颠覆者,在内内幕中发现自己,惊醒自己,“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痛的、酸的、麻的”,是不完整的,是没有中心的。所以在《不著撰人1449年亡国辞典及眉批》中,那个帝国在1449年的纪年中正在分奔离析:“1449年是中国很滑稽的一年,有人在打仗,有人在搞宗教,有人在玩瓷器,有人在读淫书,有人喝茶,有人写诗,有人习异术,有人弹古琴。”而在梁祝、孔明、蚩尤所组成的古代经典人物中,所有的一切也都在解构着传统,甚至在“但丁忽略的13世纪前中国异教徒之补遗”的《地狱篇注》中,异教徒是远离神学远离中心,“大多是贪婪的,浪费的”中国诗人。而所有的内幕者,或者这些颠覆者,却是带着身体之疾,这种不完整和不完美对于中心解构来说,具有双重的意义。瘦子、聋子、白痴追光者、白虎女子,“瘦是隐喻”,其实肉体也是隐喻,作为对中心的解构,一方面是在小说叙事中用那些不完整、不完善的自我,所谓“异端”,用他们的颓废和时间之外的“中古”组成内幕揭露者的队列,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消解中心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具震撼和寓意的就是死。
死是对于身体的消灭,也是对于叙事的终结,那个中心、历史、乌托邦、梦境,以及一切的场景都会消失。而死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他死,用他人这一武器来制造死亡事件,《菊瓣儿》就是“中古某刽子手秘密日记”,所杀的人形形色色:“有强盗、乞丐、娼妓、和尚、孩子、造反的土匪、酒鬼、市侩、写反诗的文人、丫鬟、浪子、媒婆、刺客、恶少、疯子、通奸犯、贪官污吏,政客、太监、甚至还有被抄家的宰相或前朝的皇帝。”他死就是一次对中心的颠覆,而更多的则是自死,自死所呈现的是不容现实,不容于秩序,黄鳝因“不肯受辱”,用一根筷子自顶咽喉而死。而罗小卿最后也是用瓷瓶碎片切脉而死。他死是对秩序的祭奠,而自死则是对自我的覆灭,但是在杨典的“异端文本”中,这些死都不干净,或者都有悬念,甚至就是他死和自死的混杂。《冷艳锯》里的那个“二十年前的一宗地方杀人案”,镇长先是“将自己一家上下十几口人杀得千干净净,然后又自杀身亡”,关羽的兵器从庙宇内消失,却进入了身体里,所谓“人发杀机,天地翻覆”也是一次颠覆,而成为无法解开的悬案。而更多的悬案则是分不清到底是他死还是自死,是死了还是活着。《冷弹》中的老人是不是被打死了?或者是我作为叙事者故意制造的悬案,“据后来人说,我们两人之间,有一个当时并没有死。”而《反梁祝》中的梁山与祝英在时间中死在文本中活,或者在叙事中死去在被叙事中活着,很多的死只是身体的一种托词,一种消灭文本消灭中心的实验而已,就像《丝人》中所说:“的确,没有人知道石公究竟是那一年死的。”
他死,自死,都只是在文本中听见“尖叫声”,对“痛的、酸的、麻的”世界的一种反应,或者正如杨典在《后记》中所说,要打破那种由来已久的沉默,沉默是不想说自己的话,沉默是默许别人的叙事,沉默是“我看不见我自己”,所有必须打破的沉默是要从阴影里“伏案疾书”,从阴影里惊醒,消灭中心,消灭传统,消灭那些病态的身体,“我用心灵的鬼斧,便足以砍开一切沉默。”是谓《鬼斧集》,而鬼斧当然不是一般的武器,是异端,是颓废,是中古,是那些烈士、情人、中世纪刽子手、音乐家、古代文人、诸葛亮、张岱、以及近代社会的二毛子、明教徒、女骗子、连环变态杀人犯、恋童癖者或某公司老板,不一而足。解构那些存在的文本,而创造新的文本,对于杨典来说,文本叙事的意义也就是反传统,反中心,以及反经验主义,“被自己的经验与生活消灭”的也一定是一个在边缘的剩余人。
“我就要向猪、花与云致敬。向疯长的山林植物与田野上星罗棋布的浮游微生物致。我就要向懒惰、颓废与虚无致敬。”而这些致敬的文本在杨典那里,变成了那本《秘笈》,反锁在粮仓里并不是最后的目的,“自己烧了粮仓,来成全自己”似乎也是另一个出口,其实尖叫也好,自死也好,或者梦境也罢,在反文本、反传统、反中心的同时,杨典又为自己的世界搭建了另一个文本,另一个中心,而鬼斧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他的小说人物几乎都来源于典籍和传说,而很少有自己完全虚构的人物,不管如何生活在贫民窟里,但总是在那个帝国首都,是“一部书的一个局部”,是“一卷腐朽笔记”,是“一张琵琶解剖图”,所有对“古代传奇的假释”似乎只在一种“惊醒”,一种对非自我梦境的体验,就像“时间再回到了2066年看到的那一幕:“在电影院里,梁山与祝英又感觉到以上的一切都发生在屏幕上,完全是一个幻觉。”
PS:题图为杨典画作局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