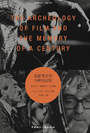2023-12-02《电影考古学与世纪记忆》:“与”看见了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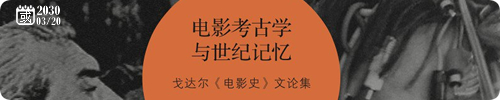
为何是8个章节?或更确切地说是4个章节,以A与B来表示,因为在一间屋子里有4面墙,就是这么简单不过的事情。
——《戈达尔与依沙布尔的对话》
从1A的《所有的历史》到1B的《单独的历史》,从2A的《单独的电影》到2B的《致命的美》,从3A《绝对的货币》到3B《新浪潮》,从4A的《控制宇宙》到4B的《我们中的符号》,“从……到……”构成了让-吕克·戈达尔《电影史》的带“s”的序列,而这种序列也在“从……到……”中变成了一个整体:从1到4的章节,从A到B的面向,组成了268分钟的文本,独立而完整的“一个”。当戈达尔在和依沙布尔的对话中将《电影史》的整体比喻成一个屋子,四面墙所形成的文本是一个多元性的存在?还是在四面墙的合围中变成了密不透风的封闭之所?
2018年观影了戈达尔的这部怪异的电影,五年之后阅读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这是从电影向书本的转换,但是这个独立的屋子还在,四面墙统摄的空间还在,面对电影或者文本,我们如何进入其中?以一种“说文解字”的方式拆解《电影考古学与世纪记忆》中的元素,不外乎是由电影、考古学、世纪记忆所组成,当然还有一个连接的“与”,拆解的四个元素就像是屋子里的四面墙,一面、另一面、再一面以及最后一面,真的能看清戈达尔的这个迷宫似的世界里存在着怎样电影诗学?戈达尔和依沙布尔的对话,标题就是本书的标题,在戈达尔简单谈及《电影史》的结构就像拥有四面墙的屋子之后,他又说到了“星丛”,八个星丛或者是“四乘二”,从外部到内部,并非是静态的呈现,而是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是星群在某一特定时刻形塑成了星丛,星丛的出现连接了现在和过去,并且使他们产生共鸣。
星丛的出现产生的共鸣,是连接之后的反映,过去和现在都指向历史的维度,而历史在戈达尔那里是“所有作品的的作品”,是《电影史》中那个带括号的(S)所显现的“星丛”:“历史,这是家庭的名字,有父母与孩子,还有文学、绘画、哲学、历史……我们这么说,是所有的整体。”艺术作品当然也属于历史,所以电影也是历史的作品,或者说电影自身构筑了“影像的历史”。但是不管是电影的历史性还是电影本身具有的影像历史意义,都是一种“历史的表演”,是“近乎活生生的历史”,它将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影像,在这种将历史唤醒的过程中,电影就具有了“历史记忆”。当然,依沙布尔在这里引用了福柯的学说谈及了“考古学”,他认为戈达尔的电影就是一种电影考古学,“从分散的时刻与遗迹开始——源自看来显得未定建构的考古学。”它涉及的事件未定建构的发展,阐明了一种本质关系。但是戈达尔似乎似乎对于这种“考古学”的提法采取了模糊性的表态,而他更侧重于对历史的思考,他认为电影叙说的历史是一个世界的影像,“它乃是世纪的隐喻。”这个隐喻在戈达尔的自我解说中,以两种维度展开,一是电影的理念来自19世纪,这是电影的一种历史性呈现,“反动思想家已经很快地说出20世纪是一个技术和技术的意识形态跃进的世纪,然而在19世纪时,技术就已经被发明了,所以在20世纪只有技术的运用却没有发明。”所以历史所具有的思想在20世纪来说,甚至变成了如字词一样是一种思想的命令;二是戈达尔将历史推向了未来,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一个不同的时代就会到来,这不是应该伤感的替换,“现在有一种新的电影,一个人们将在50年或100年后创造历史的不同艺术。”
一种是对命令的抵抗,一种是对时代的欢迎,戈达尔和伊沙布尔的对话其实阐述了最基本意义的“电影史”。但是从“电影史”这个总片名入手,可以拆解开来分析的维度也是两个:电影、历史,电影指向的是“电影是什么?”而历史指向的则是“历史是什么?”电影是什么和历史是什么,似乎都是关于本体的一种提问,编者孙松荣在《这座电影出没的城市》中就提到了电影的本体问题,他以“反身性”概括戈达尔电影拍摄的实践和思想,尤其在《电影史》中得到了体现,戈达尔在一直寻找电影是什么?电影能够创造什么以及电影如何创造的问题,以电影的实践来回答电影的本质,这就是一种“电影作为电影”的命题,就是直接陈述电影自身的物质性与策略性的“反身性”创作,简言之就是“电影论述电影”:从戈达尔加入维尔托夫小组,到《蔑视》中以展演电影自身的历史性形式现身/现声,再到《一切安好》中对电影制作法则的公然挑战,孙松荣认为,戈达尔的“反身性”策略是一种将电影的“存在性”从客观性转向主体性的建构,它在影像之间形成了环绕,指涉了影像材质的程序性、构成性和必然性,并在一种无法寻得出口的劫难中再现了创作的不可能性和无法再创作的可能构建的电影困境,这一困境更是指涉了电影对现实困境的投射,它是灾难世界,它是文化危机。
对电影本质的反思和主体性的构建,同样反映在迈克尔·维特的《“戈达尔,电影曾经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戈达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提及电影的死亡,到90年代则宣告了“电影已经彻底死亡”,他的电影死亡论就是基于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反思:“电影是什么?”或者可以说,“电影曾经是什么?”迈克尔·维特在这篇文章中只是很表象地认为,电影艺术在当下,是处在电视、数字时代的崛起时代,它的式微不可避免,所以电影被娱乐化是电影死亡论的现实背景,但是迈克尔·维特也指出,戈达尔所言电影死亡也指向历史的死亡,“当电影无力面对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时,就是电影开始消亡的确切时刻。”他认为,这是电影在“大写历史”中的失声,是“大写电影”的缺席,在《电影史》中,戈达尔研究了“大写电影”的几个历史节点,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电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电影,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经典好莱坞时代——“大写电影”的真正表达,在迈克尔·维特看来,是“电影装置在集体的意愿下发生了转变,以消解和追寻一个新的国族形象的轮廓,来应对国族身份的丧失与缺席。”
实际上,这里就出现了电影和历史的关系学,从电影是什么延伸出历史是什么,或者说从电影的死亡论唤醒的是电影的使命论。历史维度被展开,是历史和电影影像的重构关系,也是戈达尔之历史和戈达尔之影像的个体关系。迈克尔·维特的另两篇文章《<电影史>的史前史》和《变形者——作为多媒体装置艺术家的戈达尔》都是从戈达尔电影创作的过程来展开个体微观史:1969年开始戈达尔就开始研究电影史,他和让-皮埃尔·戈兰通过对图像、影像片段与书面文本的拼贴,勾勒出一部电影简史,后来作为被放弃的图书项目的一部分,成为了《电影万岁!》或《打倒电影!》;1970年代中期,戈达尔制作了一份20页的英文拼贴作品,这是关于《电影史》最为重要的早期档案,他在其中概述了自己与安娜-玛丽·米埃维尔以《电影与电视的历史》为名的关于“艺术、经济、技术和人的研究”的构想,“我想创造一部电影史,展示那个视觉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特定时刻,即绘画与影像更为重要的时刻。”戈达尔如是说——“史前史”直到90年代完成《电影史》才宣告结束。而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戈达尔又开始制作录像作品,他让影像进入到新媒体时代,迈克尔·维特认为,戈达尔并不拒斥录像作品,反而后期的录像作品是电影的2倍,这说明戈达尔开始尝试对“绝对主观项目”进行开发,尝试对早期电影的简单性和直接性进行再创造。这是戈达尔创作多元性的一种表现,而依沙布尔在《戈达尔,现代生活的电影艺术家——史实中的诗意》中则认为,戈达尔通过超越电影的方式,通过新技术的运用,既是一种反思和返回电影过去的方式,也是在对材料和创造的潜在性、实验的虚拟性中建立了史实性的诗意,它是“尚未”,它是“别样”,它是开放。
| 编号:Y23·2231004·2010 |
个体的创作和反思历史构成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史,而对于“历史”,戈达尔在《<电影史>——关于电影与历史》一文中也是以“个体”的方式发声,这是他于1995年9月17日获颁阿多诺奖时朗读的文稿,对于电影,他无比悲观地表示:“有一个曾经存在及相对独特的东西——电影。如同一般的独生子,电影却学坏了。”甚至他将电影银幕的白色画布看成是“导致尼古拉斯·德·斯塔埃尔自杀的准确反面”,它变成了裹尸布。所以这篇文章更可以看做是戈达尔对发表电影死亡论的“哀歌”和“悼词”,但是《电影史》是一种救赎,它是召唤事物的符号,“电影曾是一个人们从未见过、以物之名召唤物之身,一种看待立即流行的小事件与大事件、即刻地需要全世界的崭新方式。”戈达尔认为,电影的目的是思考,是治愈病患——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电影“揭露过这些集中营”,所以它失去了踪影,所以它要凝视这个世界。
从个体创作的历史到个体阐述电影的历史,这也是打开《电影史》的一扇门,从“电影是什么”和“历史是什么”这两个被拆解的问题,现在需要再揭露和凝视中重新连接起来:电影如何表现和反思历史?历史又如何变成电影的存在?安托万·德巴克的《戈达尔与对历史的时代批判》,其标题就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对历史的时代批判”,他认为戈达尔的电影史是一部“全体自传”的电影,不仅仅是一个人对电影的思考,更是从宏大的历史意义上进行反思:戈达尔在20至40岁的时候曾因自杀未遂或意外事故的原因,和死亡有过很多次擦肩而过的经验;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戈达尔的影片被戴高乐政权禁播,导致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改变;作为新浪潮的一员,戈达尔表现出了那一代面对历史时的惴惴不安。所以戈达尔的电影死亡论,更深刻的含义则指向了历史本身,它是一种从无所不在的“当下”向挥之不去的“过去”的猛然转向,电影即将死去,电影正在死去,因为历史迫使它不得不如此,所以电影之死在安托万·巴德克那里就被看成是“某种电影文明之死”,所以需要反思,需要凝视,需要批判,而戈达尔这个“正在消逝的电影的幸存者”被德巴克看成是伟大的历史学家,“通过这个让他得以去对历史时代做出批判的微妙立场,让-吕克·戈达尔最后就算没有成为一个非比寻常的历史学家,至少也已化作一个历史的书写对象。”
雅克·朗西埃在2001年的文章《无道德的寓言——戈达尔、电影、故事或历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戈达尔的“电影史”概括了并不相符的两种历史,一种是电影“可能的历史”,另一种则是电影百年发展的“既成历史”,历史和历史的不相符是因为电影误解了自身的历史,和德巴克对历史维度的反思不同,朗西埃更侧重于对影像本身的反思,他认为这种误解是源于电影本身,它屈从于脚本化的“故事”,而不再理解从绘画传统继承而来的“图像的力量”,而戈达尔正是从图像的力量中重新构建电影“可能的历史”。如何构建?朗西埃分析认为,这个步骤在戈达尔那里是两步,首先是将图像从电影故事中夺回,然后将图像重新编排进新的故事,看上去这两步在技术上可以简单实现,但是在戈达尔那里,则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它以电影背叛自身和背叛历史的方式证明运动影像艺术的“彻底纯真”。
通过《电影史》4A章节《世界的掌控》中“希区柯克的方法论”,朗西埃具体而微地分析了希区柯克电影和戈达尔重构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在让戈达尔自己声音进入图像的实践中,将图像转向了视觉单元,构建了特殊的关系,“这种完美的反操作将人物和他们的导演变成了真正从死亡之地浮现出的影子。”希区柯克的方法论也是戈达尔的方法论,世界的掌控也是戈达尔对于影像叙事的掌控,而这种重构在朗西埃看来,也是历史可提供的经验,“历史是这种共同经验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所有的经验都是平等的。任何一种经验的符号都能够表达其他经验。”按照诺瓦利斯的说法,“万物皆言说”,它是戈达尔的影像实践,也是历史经验的表达,由此,历史和影像,或者说“电影史”完成了两者的构建,“这一诗学使每一个句子和图像都成为可以与其他元素联结在一起的元素,由此,这些元素可以讲述百年历史和电影的真相,即使图像和句子改变了它们的性质和意义。”
历史性的延续变成了《电影史》的诗学,那么电影的创作也必将是对于历史的见证,而在《电影史》中,戈达尔的反思更进一步,“诗学又反过来指责电影背叛了它”,所以电影在更大意义上开始了建构——在朗西埃看来,戈达尔运用的正是一种叫“隐喻蒙太奇”的方法,“在隐喻层面上确实存在着100年的电影时代,用以见证电影在这100年存在中的缺席。”电影的缺席表现在1935-1945年历史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表现在好莱坞梦工厂和商业化“与魔鬼签订的盟约”,按照戈达尔的说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电影不在场,所以电影缺席了历史首先是电影背叛了自己,而戈达尔在《电影中》让电影再次见证:《德意志零年》的最后一幕,戈达尔将其变成了意大利电影摆脱“美国占领”而诞生的象征,“戈达尔在影片结尾处施加的极慢镜头,将那个俯身于死去兄弟身上的姐姐变成了一个复活的天使,向我们展示了影像从每一次死亡中重获新生的永恒力量。”因为戈达尔电影中“错误的人”的存在,所以它才能在展示了有罪的艺术纯真之后,证明自己的神圣使命。
从历史的缺席中见证,《电影史》是戈达尔的“隐喻蒙太奇”,按照戈达尔的说法,蒙太奇就是思想,这是一种连接,更是一种对话,这种连接和对话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德勒兹在《关于戈达尔的三个问题》中明确指出,戈达尔表达的是“没有正确的图像,只有图像”,这也就意味着戈达尔要建立的是“只有思想”的世界,而这个思想的建立,是一种“口吃”,“正是这种创造性口吃,这种孤独,让戈达尔成为一种力量。”口吃是问题的表达形式,是让答案沉默的言说,更是一种“当下-生成”,因为它在不断连接,“将语言分解为一种权力攫取,使其在声波中产生结巴,分解那些所有声称是‘正确’思想的思想,以提取‘正确’思想。”德勒兹认为,戈达尔的“思想口吃”就表现在那个并列连词“与”上:与是连接,是关系的生成,有多少与就有多少种关系;与让关系摇摆不定,它更让“是”变得动摇,“与……与……与……与”是一种创造性的口吃,和“是”具有的支配性用法形成了反例;与更代表着多样性,这是对同一性的破坏——而德勒兹更是将“与”和自己的“千高原”理论联系起来,“与”运转起来,它既不是此也不是∶,它在两者之间,它是边界,它是逃逸线或流动线,“正是在这条线上,事物在流过,生成在进行,革命在形成。”
“与”创造了新的边界,“与”发现了断裂线的新方向,“与”构建了思想的蒙太奇,“与”也成为“电影考古学”与“世纪记忆”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口吃,很有隐喻意义的是,在这本论文集里,大部分作者对《电影史》的革命性意义给予了肯定,但是收录其中的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文章却提出了一种质问,在这篇《<电影史>,就是我——“双刃剑”或矛盾的历史》的文章中,于贝尔曼也认为,戈达尔将自己、将电影置于历史的判决之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诗意的高度。但是当他举起巨斧对历史作出判决的时候,他无疑是被告也是原告,但他最重要的身份则是检察官,“检察官戈达尔将在这个意义上在历史的注目下,预审关于他自己的实践的案子。”对历史的指控实际上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无辜:在一个亲维希反犹太主义的家庭中成长的无辜,集中营电影缺失的无辜,所以他才会说:“从那一刻起,回想起来,我对自己说,作为一个电影人,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我在被占领的领土上,我是抵抗运动的一部分。”
因为无辜,因为历史的恶,所以于贝尔曼认为戈达尔的做法恰恰是让自己作为“抵抗运动的一部分”而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立场,《电影史》的第一部分,戈达尔喃喃自语:“导入/一个/真正的/电影/的/历史/一个/唯一的/一个/真实”,这就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立场。当戈达尔通过电影“重看”过去,为“没有看”的原始错误赎罪,那些巨大的引文形成了“引文蒙太奇”,而戈达尔又在回看、背诵、回溯、重新发现中“再蒙太奇”,从而与当下的现在碰撞。但是这个被依沙布尔命名为“电影考古学”的实践,于贝尔曼却区分了神话学和考古学的区别,在他看来,戈达尔如果以哀歌的方式对历史哀悼,他需要的就是考古学,而且考古学带来的是“一种不那么夸张的、更哀婉的、更抒情的方式来看待《电影史》”但是戈达尔却是以神学的方式复活了历史,当他带着开始对信仰和奇迹发出呼唤,无疑戈达尔把自己定位成了救世主和救赎者,这就造成了一种错位,当历史成为“所有时代、所有居民、所有战争的残酷和所有艺术的美丽混合在同一个图像的烟火中”最宽泛的共同体,它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最狭隘、最孤独的主体性”,于贝尔曼认为,当戈达尔将“整个历史”缩禁在“我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症状性的表达,“复杂的《电影史》是否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概括:这是一个戴眼镜的人的故事,他独自一人,非常认真地打字;我们听到他低沉的声音诉说着深刻的事情,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他写的、谈论的和想象的许多事物。”
或者历史被简化成“就是我”的断言?这种“最终之人”的姿态在于贝尔曼看来是一种担心:当戈达尔以一个粗暴命令的词,一个片面的定义或一个反打镜头,将富有争议的事物固定在一个“不容置疑的和确定的位置上”,不正是对多样性的封闭?《电影史》不管对电影、对历史还是对个体来说,都打开了一个多样性的世界,蒙太奇制造了叙事法,“与”看见了边界,图像的力量不断显现,但是于贝尔曼看见戈达尔在不容置疑的位置上制造了对多样性的封闭,这种论述也正是多样性的体现,或者当戈达尔用8个章节构筑起四面的墙,不管是开放的存在还是拒绝的封闭,都成为了戈达尔的《电影史》,“《电影史》,就是我”。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7164]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 1条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