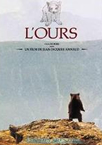2015-04-13 《子熊故事》:人化的“熊本主义”

冲突其实写在这雪山森林的每一个角落,母熊教着小熊吃食蜂蜜和蜜蜂,灰熊带着小熊捕杀奔走的梅花鹿,豹子虎视眈眈追逐孤立无援的小熊,这是动物意义上的生与死,这是物种之间的肉弱强食,但是当这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因为人类的闯入而被破坏的时候,冲突其实变成了野蛮和文明的冲突,变成了原始和现代的矛盾,那猎人举起的猎枪上分明刻着熊的图案,一颗带着人类征服的子弹打中了灰熊的左肩,却并非是人类的胜利,相反,却将那种学会射击学会生火并且说着语言的人类变成了动物的拯救对象,而当另一颗子弹朝天鸣放终止杀戮的时候,也完全成了动物感化下的救赎。
人类成了文明世界的配角,猎人成了第三人称,而熊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从原始野蛮的象征变成了现代文明的另一个隐喻,暴力和报复都已经不在,熊在自然和谐和文明延续的双重角色中完成了新的定义,这种定义看起来充满了人本主义的光辉,而其实,对熊的拟人化塑造更像是一个人类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双重角色其实带来的是双重矛盾,当作为动物的熊放弃自己的自然属性是不是意味着更大的死亡威胁?当熊被赋予人本意义完成对人类的救赎是不是可以消弭非物种的歧视?文明或者只是写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词汇,即使猎人们藏起子弹,即使他们离开森林,也只是闯入者的暂时退出,也只是熊世界的暂时安宁。
|
| 导演: 让-雅克·阿诺 |
 |
这是动物世界成长的第一步,他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下去,但是随之而来的种种困难构筑了他人生跌宕起伏的情节。在冰冷的母亲身边躺了两天两夜之后,小熊开始走进属于自己的森林,下山的时候他连滚带爬差点掉下悬崖,追逐青蛙的时候失足落水惊出一身冷汗,而在悬崖石壁上孤独入睡的时候,他的梦中全部是青蛙怪物,扑向他让他感觉到恐惧。无依无靠,孤独生存,对于小熊来说,这样的人生境遇其实已经带有了人化的影子,正是母亲的死,让他独立成长,也是母亲的死,让他感受到了缺失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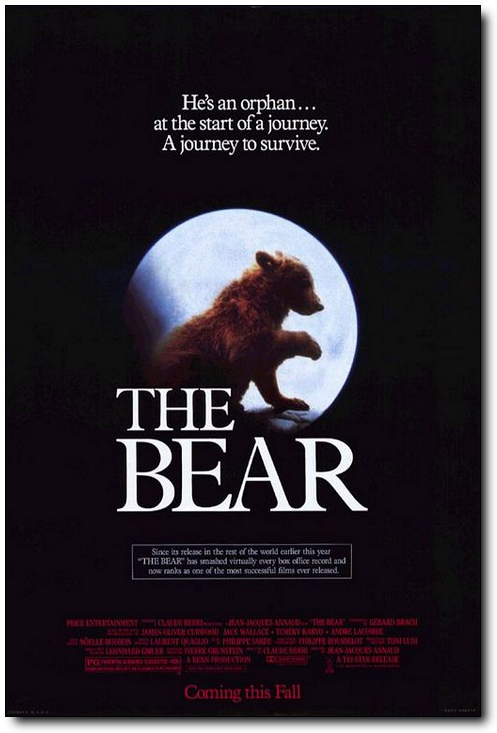 |
| 《子熊故事》英语海报 |
所以当那头受伤的灰熊闯入他的生活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同类流血的痛苦,这和母亲之死一样,慢慢成为他感知世界的宝贵经验,而他对于灰熊的跟踪和照顾,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弥补自己失去母亲的现实。灰熊的痛苦叫声,瘸拐的走路姿势,都让小熊紧追不放,即使前面有悬崖,有激流,他也奋不顾身地来到灰熊身边,而当他用嘴舔着灰熊伤口的时候,本来想要赶跑小熊的灰熊终于被他的行动感动,他像死去的母熊一样,和小熊亲昵,给小熊寻找食物——他用自己的那种爱回报小熊付出的爱。
用爱来感化,用爱来回报,看起来是动物世界同一物种之间的本性流露,但其实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人类的文明表达,或者说,不论在小熊身上,还是灰熊身上,都具有了人化的意义,当灰熊和小熊直立地站起来眺望远方,他们就像是一对偶遇之后的忘年交,充满了人性的关爱。而小熊更是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他在睡梦中出现的青蛙恐怖场景、母亲被石头砸死的闪回,以及后来因误食毒蘑菇而陷入迷幻状态,都直接造成了小熊人性化的视觉和心理表达,可以说,进入小熊的世界就是进入一种人类的幼儿状态,一切懵懂无知,一切又充满着人性的光辉。
而与这种动物的人性化场景相对应,是真正人类的物化,或者说是人类对于爱、和谐和人性的抛弃。猎人们进入森林,他们手中拿着刻有熊图案的猎枪,从脚印和大便的线索中寻找熊的踪迹,而他们手上已经获得了珍贵的熊皮,那些熊皮是他们破坏自然的战利品,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写照。在灰熊获取树上果子的时候,邪恶恐怖的枪声在这宁静的森林中响起,子弹射中了灰熊的左肩,受伤的灰熊疯狂逃离人类的视线,侥幸逃脱的灰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种下了复仇的种子,带着伤痛的身体,带着痛苦的狂吼,灰熊在这场人类和动物的冲突中几乎成了牺牲品。
但是不死的灰熊却被小熊感化,如果可以猜测的话,小熊不为灰熊舔伤口,灰熊在内心深处必然会向人类进行报复,猎人的那匹马被咬死足可见灰熊自卫的天性。而猎人的那匹马,其实是驯化的动物,在某种意义上早已经脱离了原始动物的属性,而打上了人类文明的烙印,它是猎人的工具,是闯入自然捕杀灰熊的工具,连同猎人后来带来的那些猎犬,也都成为人类文明的驯化物。脱离了自然物种的属性,所以灰熊咬死咬伤了马匹和猎犬,那那匹马死之前从眼角流出眼泪,似乎呈现了另一种拟人化的情感。
所以灰熊和马匹、猎犬之间的冲突是自然和人类文明的冲突,本来这样的冲突会慢慢延伸到灰熊和猎人之间,而当小熊被猎人抓住,这样的冲突似乎越来越趋向于必然性,但是人化的小熊似乎并没有成为猎人最终的牺牲品,虽然被吊住了绳子,但是猎人并没有杀死小熊,相反,反而将其视为一种可爱的动物,给他喂食,逗他玩乐。所以在一旁潜伏的灰熊似乎并未按照计划,用自己的野蛮力量和人类对抗,甚至,最后以一种出乎意料的解救方式还猎人生的权利。等待灰熊现身的猎人在寻找水源的过程中,突然遭遇到了凶猛的灰熊,张开大嘴的灰熊似乎要一下子将这个手无寸铁的猎人吞下肚子,猎人跪在石头上,当手中那小小自卫的石块掉落,当他喊出“不要杀我”的求饶声,灰熊巨掌刚要落下的一刹那,他转身离开,留下的是惊魂未定的猎人。离开是灰熊的宽恕,是动物的怜悯,是对人类的救赎,灰熊的左肩那伤口似乎还没有完全愈合,他却用超越动物思维的行动把猎人带回到安全地带。
这是人化的“熊本主义”,一切闪烁着人性光辉,而当灰熊离开,惊慌的猎人转身去拿枪,当他抬起刻有熊图案的猎枪,瞄准救下他生命的灰熊时,他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是愧疚,也是感动,这是救赎,也是自救,子弹从枪口射出,但是却朝向了天际。而另一个猎人赶来,同样用枪瞄准灰熊的时候,他也让他放下了枪,放下了征服的欲望,放下了人类的贪念和私利,放下了人类文明中的罪孽。灰熊没有咬死猎人,猎人没有打死灰熊,在动物和人类之间达成了友好的契约——猎人取消了猎杀计划,离开森林,回到属于自己的人类社会。
而当猎人们离开之际,那只小熊却赶来,站在山顶,直立起来,像一个朋友一样,挥动着熊掌,向猎人们告别。“上帝作证,顺其自然吧。看看谁是世界文明的象征。”猎人的这句话是宽恕自己,也是解救自己,是对熊的感恩,也是对于自然的一种敬畏。世界文明的象征是小熊和灰熊之间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爱?是灰熊不杀人类的恻隐之心?还是人类放弃对自然的征服?其实人类多少是尴尬的,他们自始至终都是这大自然的一个配角,他们闯入森林世界,虽然手中拿着武器,虽然有燃火驱赶寒冷和恐惧,但是这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不能带走的,为了欲望他们差点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从闯入者变成放弃者,从罪恶的人变成被救赎的人,他们被一头熊所主宰,这仿佛是对人类开的一个玩笑,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变成了物皆有之的高度,是那头被人类伤害的熊先有了恻隐之心,然后才让人恢复了恻隐之心。
所以说,熊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人类内心的野蛮本性,而使自己具有了人性,自然的熊变成了人化的熊,这是文明的一个寓言。而其实,在这不允许人类闯入的自然生态中,熊作为动物原始力量的象征符号,也不能超越物种属性,当那头饥饿的豹子猛扑向小熊的时候,动物间的肉弱强食依然在随时随刻在上演,生与死在自然界中似乎是永远的冲突,而小熊经过九生一死的遭遇,最后被灰熊解救的时候,整个自然也演化成一幕关于爱的主题戏剧,灰熊救下了小熊,他们像一对父子进入洞穴,开始了温馨的冬眠生活——外面雪花飞舞,而在里面他们相互依偎,此时,小熊的梦中一定没有那恐怖的青蛙,那诡异的蘑菇,那滚落是石头,以及凶恶的豹子,只有喜悦、快乐和爱。
The greatest thrill is not in killing, but in letting live.这是电影最后的字幕,“最震撼人心的不是捕杀,而是给予生存的权利。”熊世界里的故事是1885年的真实事件,是1917年的小说,是1988年的影片,当被赋予了人性意义,当消除了非物种的歧视,当生存的权力变成文明的最高标准,这只是一个“让上帝作证”的寓言。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277]
思前: 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