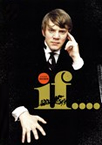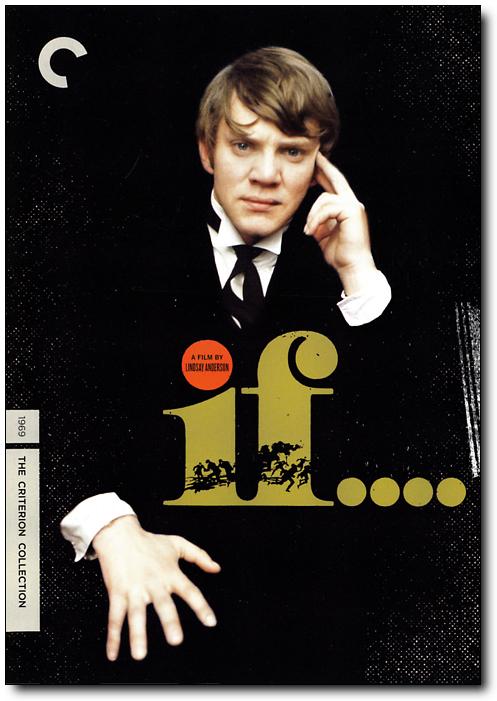2016-06-03 《如果》:自由是一种虚拟语态?

只是一个“if”,小写,以及省略号,在交战互射的激烈场面下,最后黑屏里的“if”却又把暴力的对射场面化成了一种虚拟状态,是幻想?是虚构?是传统世界里的一次对于反抗的意淫?是保守学校里一种对于自由的想象?房顶上的查维、华莱士、奈利、菲利普和那个性感的女人,他们举起枪对着底下的那些人射击,而起先混乱的人群也拿起了枪,对着上面的暴力学生还击,当校长大喊“挺火!理智点!”刚说完这句话,女人的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脑袋,血汩汩而出,随即倒下。
是对秩序的一种破坏,是对规则的一次僭越,上和下、内和外,组成的对立体系在暴力世界里变成了“if”后面省略的命运。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不是真死?理智在哪里,暴力从何而来?那在教堂里的是达官贵人,是陛下,是将军,是主教,他们维护着传统,他们认为“英国没那么容易改变”,他们高喊着纪律、服从、尊严和责任,他们倾听者上帝的教诲,但是当教堂底下冒出了浓烟的时候,将军还在台上作着演讲,似乎一种秩序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充满恐惧的烟火将教堂变成了危险的场地,而后是混乱,而后是逃生,而“让妇女先走”也是一种秩序而已。而当他们逃出象征威严、礼义和仪式的教堂,却面对着从屋顶上射下来的子弹,居高临下的是坏学生,是对秩序进行反抗的青年,而当他们以俯视的方式制造另一场混乱的时候,是对于秩序的颠覆,也是对于上帝的否定,本来处在秩序的最下层,却成为屋顶上的反抗者,而在这上下颠倒的关系里,他们喊出“王八蛋”,他们射出仇恨的子弹,他们制造一次事件,但是只是“if”,只是一种悬置在现实之外的状态,谁是新的上帝,谁是新的暴力者,谁是拔出枪却又难逃惩罚的新青年?
|
| 导演: 林赛·安德森 |
 |
快速、急切、毫不犹豫,朱特变成了“跑起来”的人,而他也终于在遭到自己的位置,放置了自己的物品,拿出了自己的水果之后,变成了这个秩序世界里的一员,规则似乎就一直存在的,他的到来只不过将自己纳入到一个充满专横和压迫的学校,一种不用怀疑的生活。听起来这里的生活是“我们要劳逸结合,别把两者搞混了,要互帮互助,就像一个新家庭,你帮助学校,学校也会帮助你。”看起来这里的而老师可以骑着自行车直奔教室,大谈欧洲的民主,课堂上讨论“查理三世为什么会成为“软体动物”但是,在这“互帮互助”的后面,在这自由讨论的学校,却处处有虚伪和偏见:低年级的学生应该为学监“暖马桶”;所有的学生都应该遵守纪律,离校者将被严惩;必须按时熄灯按时入睡;如果考试一个人记不住单词,那么全班就要跟着受罚……而学生和学生之间,也是一种等级,也是一种秩序:学监监督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又欺负低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也欺负同年级的同学。当查维、华莱士和奈利在宿舍里喝酒的时候,学监邓森便要求他们每人冲三分钟的冷水澡,在寒冷的冬季,在其他同学享受热水浴的时候,在邓森自己泡在浴缸里的时候,却让他们三个对着寒冷的水龙头,而即使三分钟十年已到,邓森一句“等我回来再离开”又将这种处罚变成了个人随意的命令。而同学之间的欺负,就是把没有朋友的同学剥掉了裤子,反倒帮助脚,然后把他的头按在马桶上,然后用马桶里的水给他冲洗头……
|
|
| 《如果》电影海报 |
不断有命令,不断有检查,不断申明纪律,而在寄宿制度里,还有对于禁欲的考验,新学期开学每个学生都要被检查身体,就在老师面前,学生们脱下裤子,接受检查,而那个女教师更是光明正大地用手电筒对准男生的下体,认真查看。他们没有隐私,甚至没有尊严,这种去欲望化的生活恰好就是寄宿制学校倡导的清教生活,但是,在这样一种禁欲生活里,学监们却要享受另一种特权,那个面目清秀的学生菲利普给他们烤松饼,而劳奇却认为在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把他作为“同性恋”的一个代表,以自我命令的方式把菲利普分给邓森,让他服务于邓森,每天叫他起床,给他刮胡子,甚至在处罚三名学生冲凉水澡的时候,也让菲利普给他端咖啡。
这便是等级制度,这便是教育秩序,而这种虚伪和偏见,专横和压迫,对于查维、华莱士和奈利来说,却是一种扼杀。他们的宿舍里贴满各种持枪引用人物的图片,他们总是藏着那些裸露女人的画册,他们一起喝酒,一起谈起女人,一起制造事端,他们喜欢暴力、革命,他们崇尚自由和快感,他们在“我的身体正在老化”的现实里高喊“先做爱然后死去。”可是这壁垒森严的学校,这秩序统治的学校,如何能呼吸到一点自由的空气?他们或者偷偷拿出酒来喝一口,或者欣赏画报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在击剑运动中高喊“暴君去死”的宣言,而那被同伴划伤的手里终于还是渗出了血——这样一种虚拟的现场,其实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反而会变成伤痛,带来流血的现实。
终于,他们出走,查维和奈利在举行橄榄球的间隙,偷偷溜出了学校。当他们走出学校,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也是打开了一扇通向自由世界的门。在街上他们虚拟这刚才击剑的动作,然后躺在马路上,以恶作剧的方式投身到这个自由社会;他们在摩托车店里抢得了一辆摩托车,然后开着它驰骋在乡野,对于他们来说,摩托车到来的速度给了他们一种自由的感觉;然后他们走进了咖啡店,在白咖啡还是黑咖啡的选择中,也开始了一种对女人的调戏和征服,查维看性感女人的屁股,在冲咖啡的时候强硬吻她,得到一个耳光之后却也以暴力方式完成了情欲释放。
实际上,当他们打开那扇通往自由世界的门,那个“if”就已经出现了,在黑白和彩色的场景交换中,在虚拟和现实的双重影像里,他们仿佛就走进了那个和学校完全不同的世界,if的大街,if的摩托车,if的咖啡店,if的女人,然后在咖啡店里展开的if世界里,女人走上前来对查维说:“我会杀了你,我喜欢老虎。”然后做出老虎扑食的样子,向着查维进攻,而查维一句“我也喜欢老虎”,又把这种攻击变成了两个人的游戏——翻滚在地上,赤身裸体。然后自由世界变成了彩色的影像,三个人骑着摩托车,以一种“罗曼史”的方式昭示着既有结构的解体。
if的世界开启了,而这if的后面却是“惩罚”,学监的理由是:“我们必须要体罚那些不安份子,他们不知廉耻,他们玩世不恭,他们已经成为学校的一大威胁。”三个人成为他们实施体罚的目标,查维在他们的淫威面前只说了一句话:“我最讨厌你,劳奇,希望我们都卑躬屈膝你才会满意。”这是一种反抗,可是这样的反抗最后还是被他们的鞭子镇压下去。三个人轮流进入健身房,关上门,里面是鞭子抽打的声音,是落在肉体上的沉闷声响,以及被体罚完了之后“谢谢劳奇”的规矩。华莱士进入,出来,奈利进去,出来,他们说只打了四下,似乎一幅无所谓的样子,可是脱下裤子,屁股却流出了血。等到查维进去,被要求放开手臂,身体靠在横梁上,然后撅起屁股,劳奇从后面冲上来,狠狠地用鞭子抽打在屁股上,一下,两下,三下和四下,查维以为和华莱士、奈利一下,惩罚已经完毕,可是劳奇让他不要起身,继续保持原样,然后再次冲过来,再次抽下去,五下、六下、七下……一直到十下。中关于完毕,忍者剧痛,查维走上前伸出手,对着劳奇说了一句:“谢谢,劳奇。”
受伤的肉体,疼痛的精神,对于查维他们来说,这又是一个将if的生活镇压的现实,他们在宿舍里开始体验死亡的感觉,用塑料袋套在头上,在密不透气的封闭世界里感受死亡一步步走近,他们设想诸多的死亡方式,想着那种死亡最残忍,鞭打之死,飞虫进入耳朵,或者癌症之死,查维却说:夜已经死了。在和死亡之夜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或者是恐怖,但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现实,而在寻找死亡、寻找恐怖的体验中,他们或者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死亡的制造者,“脑子被一枚钉子慢慢钉进去,死亡的痛苦只由钉子的速度决定。”钉子的速度,由慢而快,死亡,当然也由一种体验变成了恐怖,而在这个寄宿学校里,无非是在他们头上钉进去了那一枚钉子,而唯一改写钉子速度的办法就是反抗,甚至要将钉子钉在他们的脑袋上。
当学校获得体育圣杯大家在欢呼的时候,当校长说我们要团结一致的时候,查维和华莱士、奈利终于将酒瓶子里的最后一滴酒喝光,然后查理拿出了一把手枪,他先是用橡皮子弹射杀图片上的每一个人,然后用刮胡刀在三个人的手掌上割下一道血痕,三个人的手合在一起,每个人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让压迫者见鬼去吧”“自由”“反抗”,然后查维说:“用一颗子弹来改变世界。”他拿出了真正的子弹,然后交到每个人的手里,一场反抗运动开始了,一种自由的渴望形成了。子弹,是仇恨的子弹,是报复的子弹,是有着钉子的速度的子弹,那颗子弹在“不能离弃,不能背叛”的战争开始之后射出,它射进了伍兹主教的身体。
但是这所谓的战争也无非是if后面的虚拟语气,校长对他们的惩罚时,伍兹主教竟然从那个大抽屉里爬出来,然后和他们一一握手,而三个人的处罚竟然是整理地下室,地下室里有动物的样本,有畸形幼儿的标本,还有遗存在那里的大批枪支炮弹,这是一个if的地下室,在教堂之外,在学校之外,在压迫之外,是真实的枪支,是真实的子弹,是真实的炮弹,却也是他们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武器。if的世界里主教呆在那一只抽屉里,是所谓的宗教的工具化象征,而畸形怪胎,则是对社会制度的一种讽刺,而枪支炮弹,则变成了真正实现“钉子的速度”的最好表达。
查维、华莱士、奈利三个人是专横和压迫的牺牲品,是追求自由生活的象征,而20年后想成为律师的菲利普则是人性被压抑的象征,而性感的女人则是这个男人世界之外欲望的象征,他们五个人,聚在地下室,聚在if的世界里,然后拿起了枪,走向房顶,如上帝一样俯视这个虚伪的学校,俯视保守和伪装下的秩序世界。冒烟、扫射、死亡,是抵达了一种钉子的速度,但是在底下的反击中,甚至最后变成镇压的命运里,所谓的反抗其实在权力面前,依然面临着失败的危险,依然无法逃避死亡的恐惧。世界从来不是不安份子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换取自由,从来不是以暴力运动的形式获得胜利,也从来不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发现黑暗和武器,发现怪胎和畸形,if,是小写的if,是省略号前的if,是黑屏世界里的if。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45]
思前: 《独角兽》:负罪的灵魂无处可逃
顾后: 我去除了所有的隐喻